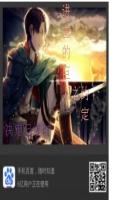汤氏作品的改编者沈璟、臧懋循、冯梦龙都是吴人。他们自以为得天独厚,是南戏以至传奇的嫡派正宗,所有“生不踏吴门”的作家都是旁门外道。王世贞《艺苑卮言》批评李开先的《宝剑记》、《登坛记》说:“公词之美更不待言,第使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字,妥,乃可传。”张琦《衡曲麈谭》指斥汤显祖“近日玉茗堂杜丽娘剧非不极美,但得吴中善按拍者调协一番,乃可入耳”。连口吻也很相似。他们和臧懋循一样都因为自己是吴人,而怀有强烈的地区优越感。
后来的研究者以讹传讹,把昆曲勃兴的时代大为提前,其实在汤显祖时代昆曲并未在三吴(即太湖周围地区)以外占有统治地位。《琵琶记》、《宝剑记》后来用昆曲演唱,使人得到一个假象,似乎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为昆曲而创作的,因而以昆曲的比较严谨的格律要求它们,发现它们不合要求时就横加非议。他们对《四梦》也有类似的指责,随着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改编。
请看事实。《金瓶梅》的现存最早版本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即汤显祖去世的第二年。小说写定时即嘉靖、隆庆之际,它所记载的大量戏曲演出情况比任何史料都要详尽。它多次提到杂剧,并未如同某些人想象那样在明代销声敛迹,而海盐腔风行南北,其中没有一个字说到昆曲。
汤显祖十岁时,徐渭作《南词叙录》,弋阳腔流行最广,北到京师,南到闽、广,其次为余姚腔、海盐腔。昆曲局限于当地,像一切事物初起时一样,还在受人排斥。“或者非之,以为妄作。”徐渭对此愤愤不平。稍后,松江何良俊《曲论》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南词叙录》写成四十多年后,据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昆山腔才取得对海盐腔的优势,然而在汤氏家乡盛行的仍是海盐腔。与此同时,沈璟晚年制订曲谱,虽然名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实际上他只为促进南曲中的一种即昆曲的繁荣而努力。他的目的“欲令(戏曲)作者引商刻羽,尽弃其学,而是谱之从”(李鸿序),这个意图正好说明在汤显祖、臧懋循、沈璟的时代,昆曲的统治地位还有待确立,或正在确立之中。从《金瓶梅》到沈璟,各家年代先后不同,忠实地反映了弋阳、海盐、昆山各腔依次代兴的情况。一个江西人在江西创作戏曲(只有《紫钗记》例外,它作于南京),是否以昆曲作为他的唱腔,至少是一个疑问。对此本文作者将另作讨论。
三、《元曲选》的编印
臧懋循对《玉茗堂四梦》的改编以失败告终,他的《元曲选》却取得一个选本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
臧懋循在六十三四岁时因幼孙的婚事而有河南之行,他绕道前往湖广麻城(今属湖北省)刘承禧家借到元人杂剧二三百种。刘承禧的父亲守有是汤显祖的友人,这批曲藏曾经汤氏鉴定。刘氏父子是前兵部尚书刘天和的孙子和曾孙,世袭锦衣卫官。刘承禧娶前首相徐阶的曾孙女为妻,而臧懋循的女儿嫁给徐阶的一个孙子。倚靠婚姻亲戚关系,臧氏才借到这些曲本。它们从宫廷御戏监的抄本过录。至于它和近人王季烈校编的《孤本元明杂剧》,即也是园旧藏脉望馆抄校内府本是否同出一源,却因资料不足难以断定。看来同一杂剧在内府也可能有不同系统的别本同时被收藏。臧懋循在《寄谢在杭书》中说:“然止二十余种稍佳。余甚鄙俚不足观,反不如坊间诸刻,皆其最工者也。”由此可以推知《元曲选》中录自刘氏藏本的,约为二十余种。以刘氏藏本作参校的则可能更多。
在编刊《元曲选》前未有别的刊本流传的杂剧40种,分四类情况:
(一)《元曲选》的孤本15种:《陈州粜米》、《争报恩》,《来生债》、《虎头牌》、《冻苏秦》、《秋胡戏妻》、《神奴儿》、《谢金吾》、《伍员吹箫》、《救孝子》、《昊天塔》、《灰阑记》、《东坡梦》、《抱妆盒》、《冯玉兰》;(二)无别本流传的3种:《隔江斗智》、《李逵负荆》、《张生煮海》;(三)只有元刊本而版本差异较大的6种:《薛仁贵》、《老生儿》、《铁拐李》、《竹叶舟》、《气英布》、《赵氏孤儿》;(四)只有抄本、未见刻本的16种:《赚蒯通》、《杀狗劝夫》、《张天师》、《燕青博鱼》、《朱砂担》、《小尉迟》、《黑旋风》、《马陵道》、《举案齐眉》、《桃花女》、《冤家债主》、《盆儿鬼》、《百花亭》、《货郎旦》,《合汗衫》、《楚昭公》(后二种又有元刊本而差异较大)。这40种在《元曲选》前是否已有刊本而后来失传,现在无可查证。如果不是这样,它们有可能来自刘氏藏本,或臧氏的原有曲藏。
另一重要来源是上引臧氏书信中提及的“坊间诸刻”,包括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16种;《古名家杂剧》八集,收元明杂剧40种,其中《女状元》脉望馆校本有万历十六年牌记;《新续古名家杂剧》五集,收元明杂剧20种;息机子万历二十六年序《杂剧选》30种,万历三十七年尊生馆主人黄正位刻本《阳春奏》收元明杂剧39种。以上各集现在都已不全。此外,校勘证明臧氏还广泛地利用当时流行而现已失传的某些版本。
从现有版本对比看来,《古名家杂剧》、《新续古名家杂剧》和《元曲选》重复的那些作品,有两种情况,如《金钱记》、《玉镜台》、《窦娥冤》、《还牢末》等两者差异较大,可能来源不同;如《酷寒亭》、《红梨花》、《竹坞听琴》、《扬州梦》等,虽然前三剧依次略去八、三、四曲,可能它们同一系统的本子曾被臧氏用作重要的校本,甚或作为底本。
《杂剧选》即《古今杂剧》,一称息机子本,它和《元曲选》重复的那些作品也有两种情况,如《渔樵记》主角姓名,臧选为朱买臣,《杂剧选》本为王鼎臣,其他如《踿范叔》、《度柳翠》、《望江亭》、《碧桃花》、《合同文字》等差异较大,可能来源不同,如《玉壶春》、《陈抟高卧》、《两世姻缘》等,它们同一系统的本子可能被臧氏用作重要的校本,甚或作为底本。
《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重复的13种,除《陈抟高卧》、《任风子》外,彼此差异极大。这里说的不是指《元曲选》科白齐全,而元刊本只保留科白的梗概,甚或完全不印科白。这里指的是两者都存在的可资比较的部分而言。
元刊本之所以可贵,一因为它最接近于原本,二因为它提供了14种前所未见的孤本,另外16种也可供《元曲选》和王季烈编《孤本元明杂剧》的复本作校勘之用。它们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如果片面地认为唯有元刊本最接近原本,而《元曲选》和其他明刊本又和它差异硕大,臧懋循甚至坦率地承认他的编选是“戏取诸杂剧为删抹芜繁。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寄谢在杭书》),如果因此而贬低《元曲选》的价值那就错了。
一般看来比《元曲选》迟,但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
问题是复杂的。
元刊本只是简单地保留科白的梗概,甚或全部删除,这一点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如同王国维在《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叙录》所说“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或者如同臧氏在《元曲选序》引用别人的说法:“其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这些话是否正确值得怀疑,诚然,科白容易遭受窜改,它不像曲文那样受到格律的限制,不是任何人所能随意加以增删。曲文一向比科白更受文人的重视,这也是事实。但是创作杂剧而又不撰写科白完全不符合当时实际:身为书会才人的大多数剧作家是为舞台演出而服务的。许多杂剧如果脱离科白,它们就不可理解。从杂剧创作的实际情况看来,角色的行动、情节的发展和进行几乎都由科白而不由曲文加以表述。把现存杂剧如《争报恩》、《东堂老》、《冤家债主》、《盆儿鬼》、《老生儿》、《渔樵记》中的大段科白归之于演员的即兴之作,人人得以自由增减,不是一时失言就是正统文学观点在作祟。像《老生儿》、《渔樵记》中对话的生动逼真、机智泼辣,理合和全部元代杂剧中那些最精彩的曲句一样受到同等的重视。即此一点而论,元刊本就不及《元曲选》接近原着的真面目。
就选录和校刻的粗劣而言,很少有别的书曾达到《元刊古今杂剧》那样糟的地步。如《范张鸡黍》一本而留下两大段空白。《任风子》既有大段空白,第四折又只剩下两支曲子,而上下两页的页码是相连的,可见不是装订时的偶然缺页,而是刻板时的遗漏,印制时始终没有发现。同一折又不见(尾)曲。《元曲选》的《赵氏孤儿》有五折,元刊本却只有前四折。剧本题名为《冤报冤赵氏孤儿》,虽然没有一本五折的先例,但“冤报冤”如箭在弦,势在必发,难以半途而废。
元刊本的若干失误可说完全置曲律于不顾。如《合汗衫》第三折(小梁州)和它的(幺篇),元刊本未标明(幺篇),两曲变成一曲。《铁拐李》第四折,元刊本把(快活三)并入后曲(鲍老催),而只标后者的曲牌名。同剧第三折(川拨棹)、(七弟兄)、(梅花酒)三曲联用,元刊本和《元曲选》文字大体相同,前者却将(川拨棹)的最后五句划入(七弟兄),又将(梅花酒)的首句作为(七弟兄)的结句。《元曲选》(七弟兄)以二、二、三字的短柱体曲句“一七二七哭啼啼”(衬字不录)开始,和曲律相符。元刊本却把它搞乱了。有迹象表明臧氏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元刊本,所有的差异并不出于他的有意修订。两者的优劣表明,在许多场合下《元曲选》反而比元刊本更接近元代杂剧的真面目。
元刊本错字之多也是少见的。它常以“ 〇”或“一”或“人”代替缺字符号(□),但如同对待明显的脱页一样并不认真加以改正。错别字如“多粘带”误作“无年伐”,“年”“粘”、“代”、“带”同音,而“代”又误为“伐”(《铁拐李》第四折(普天乐),“垒高冢卧麒麟”(《范张鸡黍》第四折(醉春风)误作“垒一家卧其人”。如果没有别本对照,那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元刊本也有胜过《元曲选》的一些字句和片段。如《元曲选》的《合汗衫》第二折主角张孝友离家远行时,看见城中失火,他居然说:“俺趁着船快走,快走”,显得对留城的父母妻子毫不关心。元刊本处理为张孝友的父母送儿子回到城里后,才发觉前面失火,这样就合理得多了。
应该指出元刊本和《元曲选》的差异,除了不是前者的明显讹误外,大多数异文并无优劣之分。与其说是有意删改,不如说是版本来源不同。
从有优劣之差的异文看来,《元曲选》不及元刊本的情况比较少,而《元曲选》比元刊本好的情况比较多。这些异文也和上面说的一样,多数情况都难以指为有意删改的结果。
下面再举《老生儿》元刊本所独有而为《元曲选》和别的明刻本所失载的一段曲文为例。
(倘秀才)钱呵,为你一(搬)得人(穷)汉为贼落草,般(搬)的人幼女私期暗约。可知把良吏清一(官)困罢了,般(搬)的亲兄弟分的另住,好相知恶的绝交,把平人陷□。
(衮秀求(滚绣球)钱呵,有你的不读书便□ □,没你的不违法就下的(疑缺牢字)。你般(搬)的世间事都颠倒,将我这不雇(顾)后的呆汉般(搬)调。有你的不唱喏便唱一(喏),没你的不(此字疑衍)高傲便(疑缺不字)高傲。人(?此下未加整理)是你鸦青神道,有你的没你的我便人着使脱你的眼脱便十分怕揣着你的胸脯增五寸高,天地差错分毫。
宾白不全,曲文难懂,即使经过细心整理,元刊本也难以作为文学作品为一般读者所接受。
一句话,元刊本不失为珍贵的研究资料。由于时代最早,它最接近元代杂剧的真面目,同时由于它在编校刻板时极其粗劣疏忽,在某些方面,它反而比《元曲选》及其他明刻本更有失元代杂剧的真面目。作为文学读本,它远不及《元曲选》。它和《元曲选》的差异不能片面地归咎于臧懋循的窜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倒是要归功于臧懋循《元曲选》的存真复原。
除元刊本外,以李开先在嘉靖年间出版的《改定元贤传奇》16种为最早。现存6种,南京图书馆藏。从何仲子(煌)在脉望馆校本《王粲登楼》的题记看来,这个本子和元刊本最为接近,但也经过“改定”。它比《元曲选》少得多。
和《元曲选》同时而略早的金元杂剧选本有陈与郊《古名家杂剧》正续编、继志斋《元明杂剧》、息机子《杂剧选》和黄正位《阳春奏》。
孟称舜《酹江集》和《柳枝集》年代较迟,受到《元曲选》的影响不小,暂且不论。王骥德序《古杂剧》可能也是同样情况。
《古名家杂剧》正续编60种,现存27种,除去和也是园藏本重复的18种、明代作品1种,实得8种,也是园藏《古名家杂剧》残本元明杂剧55种,除去明代作品22种,实得33种。两者合计41种。不到《元曲选》所收剧目的一半。其中34种和《元曲选》重复,可以互相校订。
继志斋《元明杂剧》可以和《元曲选》对照的金元作品三种。
《杂剧选》包括脉望馆所收12种,共22种,其中和《元曲选》重出的19种,可以互相校订。
《阳春奏》现存金元杂剧三种,其中和《元曲选》重出的两种,可以互相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