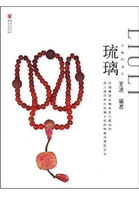第四折《收江南》:“哥哥是心直口快射粮军。”严敦易《元剧斟疑》以为张国宝当作张国宾。张已有《合汗衫》一剧,因两剧都在相国寺团圆,遂误以为张作,作者应为无名氏,可从。
二十、高文秀《遇上皇》
第二折把赵元的身份定为射粮军,但具体描写与此不相适应,编剧者对此身份似乎缺乏理解。
上面所列举的杂剧作者的年代以及在地名、官制和其他人事中所显示的金代印记,表明以上二十本杂剧中至少有一些是金代杂剧的遗留,虽然在流传中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异文。可见王国维所说:“宋金戏剧之结构,虽略如上,而其本则无一存”,并不符合事实。杂剧如同时代相近的古代小说一样,它们原来出于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之手,经过世代流传,在流传中经过许多人手的增订删润才最后写定,有的写定较早如石子章、李直夫,有的较迟,如上举贾仲名已是元代末年人;有的写定者曾作出可贵的增订和删削,可说是名实相符的再创作,有的则很少有润色。种种情况,不一而足。
众所周知,杂剧作者多半是失意文人。他们时乖运蹇,后来又因民族歧视和科举停开,仕进的道路断绝了。他们落魄潦倒,却难以改变长期养成的浪子习性,于是昔日光临勾栏的风流狎客,一变而为仰给于勾栏的食客,身份介于主客之间。他们“会围棋,会蹴踘,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各种伎艺,无所不精。编写杂剧使他们在勾栏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
他们不用掏钱,得以继续享受迷花醉酒的生活。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地方政府的吏员,他们以杂剧创作作为俯仰由人的官场生活的调剂,得以不无安慰地仍然以文人自居。书会才人并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既有业余的行家。也有以此为业的戾家。以各种伎艺,出入勾栏,这就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从作为百戏的杂剧到具有一本四折固定戏曲体制的杂剧的演变,比有文献可供查证的年代要早得多。金(宋)元时代,北方各城市勾栏演出久已存在着一大批传统剧目,它们在书会才人的笔下得以改编和写定。
无名氏《蓝采和》第一折,伶人对看官说:“爱看什么杂剧,随您占选(甚杂剧请恩官望着心爱的选)。”看官说他夸口(因下一句唱词要协韵,改用“自专”),伶人回答:“俺路歧们(专业演员)怎敢自专,这的是才人书会錓新编。”“錓新编”,既是因袭,又有创新。从照搬、移植、必要的润色和删改,直至富有创造性的不下于创作的种种改编,各本杂剧之间加工程度大不一样,但它们的改编者都被看作是杂剧作者。勾栏和艺人都以上演新作吸引观众,更促使同一题材、同一作品的不同改本先后产生。谁都可以把传统剧目,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根据演出时的具体需要,甚至按照演员的实际情况加以改编。《西厢记》五本要在较短的时间演出,那就有郑光祖的《梅香》。董秀英的爱情故事,南戏《玉环记》第六出和孙季昌《正宫端正好·集杂剧名咏情》(见《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都有记载,本来有它自己固有的故事情节,但改编者却把它改得同《西厢记》十分接近,简直成为它的缩本。颇为知名的杂剧《酷寒亭》,第一二折郑孔目的同事赵用唱,第三折酒店主人张保唱,第四折草泽英雄宋彬唱。按照剧情,郑孔目是主角,但他没有一句唱词。因此,它的改编本《还牢末》,虽然草率之至,却也有它的立足之地,四折戏全由主角一人唱到底,而同它相对照,又有《还牢旦》。编剧是为了演出,既不为出版,也不为传之后世,因此不存在作者的署名和版权问题。一个戏班可以采用别一戏班的剧本,随意加以改编。
别的戏班对这一戏班的剧本也一样。正因为如此,天一阁本《录鬼簿》明白注明次本、二本即复本的就有李文蔚《东山高卧》,赵子祥《害夫人》、《石守信》,李好古《张生煮海》,李取进《受禅台》,郑光祖《倩女离魂》和金志甫《东窗事犯》。单就同书所记,内容相同的复本远不止此数,如关汉卿、王实甫都有《破窑记》,关汉卿、郑光祖都有《伊尹扶汤》,石君宝《曲江池》和高文秀《打瓦罐》本事相同,杨显之、花李郎都有《酷寒亭》,而赵文宝《教女兵》注明有旦本,可见另外一定有末本。就是同一本杂剧,尽管流传的版本并不太多,有时出入也相当惊人。如以元刊本和《元曲选》相重的十三种而论,除《任风子》、《陈抟高卧》外,其他各剧差异很大。从《元曲选》和《古名家杂剧》、《新续古名家杂剧》重出的《金钱记》、《玉镜台》、《窦娥冤》、《还牢末》的差异看来,两者应出于不同系统。《元曲选》本《赵氏孤儿》有五折,而元刊本只有四折;《窦娥冤》第二本《斗虾輶》的名句曾为王国维所激赏,而《脉望馆古名家》本的相应段落却配不上这样的评价。
题目正名相当于最简明扼要的剧情提要,它竟然同杂剧内容不符合,这样的杂剧并不少见。关汉卿《窦娥冤》(《古名家杂剧》本)题目正名第一句说“后嫁婆婆太心偏”,剧中窦婆被迫接纳张父来家同住,还不能说已经改嫁。说她心偏,无论她对谁都不能这样说。
郑廷玉的《金凤钗》正名为:“杨太尉屈勘银匙箸,宋上皇御断金凤钗。”按剧本的具体描写,杨戬自报家门:“官封衙内之职。”衙内当是宋代衙内都指挥、都虞候等禁军军官的省称,比太尉官阶低得多,审判官谏议大夫张商英也不是大官。张商英断案,奏请皇帝批准,并没有“御断”的情节。高文秀另有杂剧《好酒赵元遇上皇》,它和《金凤钗》一样,写的都是当时在位的皇帝,不是太上皇。元刊本张国宾《合汗衫》的题目正名的第一句:“马行街姑侄初结义。”此本无介白,内容不详,臧本却只说:“嗨,俺婆婆亦姓赵,五百年前安知不是一家。”
因此救济他十两银子,没有认亲的情节。关汉卿《王闰香夜闹四春园,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剧本只偶然一提这个园名,钱大尹按照梦中鬼神的指示破案,说不上什么“智勘”。同一作家《救风尘》,官员为宋引章和周舍的争讼下断说:“只为老虔婆爱贿贪钱。”剧本写明宋引章受欺是由于她本人轻信甜言蜜语而受骗上当,鸨母倒想劝阻她:“不是我百般板障,只怕你久后自家受苦。”从上述情况看来,人们可以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证明某剧不是通常所说某作家的作品;或某作家虽有这样题名的作品,今传某剧则由于内容与题目正名脱节,当是另一作家所写。这种方法行之于个人创作无疑是有效的,但对金元杂剧则不然。本文认为当时传统剧目有的可能只有口口相传的简单梗概,或几支主要曲牌,然后由各书会才人写定全剧的曲白。它们受到优胜劣败的筛选,有的情节或唱段被推广,有的被淘汰,有的杂剧除了原有水平较高,又吸收别一本子的优点,改掉自己的不足之处,逐渐形成固定的一二种定本。其中有一些破绽依然存在,或虽然已经有人加以纠正,但留传下来的只是较好的、而不是最佳的本子。
除上述名实不符的情况外,金元杂剧中的破绽不一而足。关汉卿把鲁斋郎(见同名杂剧)作为人的姓名看待,而斋郎是学官名,不会是名字。
费唐臣《苏子瞻风雪贬黄州》,第一折说白:“臣今辞了天颜,这一去摈斥海岛,葬江鱼之腹,再不能见陛下矣。”唱词:“则今日伤心游海岛。”贬官黄州同远谪海南缠夹在一起。如果说这是出于没有或很少文化知识的人的窜改,他怎么又知道苏轼贬官海南?孔文卿《东窗事犯》,据《录鬼簿》说,他采用的是“西湖旧本”,竟把杭州说成“钱塘镇”。《介子推》把晋献公和他的世子说作天子和太子,违反普通常识。无名氏《鸳鸯被》,女主角李玉英十八岁(《楔子》),过了一年,成为“二十一二”岁(第一折)。她从来没有哥哥,张瑞卿冒充她的哥哥,她竟信以为真,没有一点怀疑。无名氏《刘弘嫁婢》,裴兰孙明明说:“俺父亲在襄阳为理(州府一级的司法官员),不幸被歹人连累身亡。”同一折《三煞》却说:“他祖宗是官宦家,他父亲为宰相职。”职位高低,前后悬殊。关汉卿《裴度还带》一会儿说是在洛阳,一会儿说是在开封,并让剧中人自白:“老僧汴梁白马寺长老是也。”洛阳白马寺并不是僻典。无名氏《碧桃花》也一样,第一折男主角说:“俺父亲曾为潮阳县县丞,三年任满回来,东京闲住。”东京即开封,第二折女主角的父亲却说:“致仕闲居,如今在洛阳城外庄上居住。”萨真人所在的丹霞山原在江西南城麻姑山之西,号为道家第十福地,也被移到洛阳城外。无名氏《货郎旦》,张玉娥、李彦和自报家门都说是长安人氏,而张玉娥和人私奔却约定在洛河边相会。第四折张三姑回忆当时“四口儿出的城门,望着东南上慌忙而走须臾之间,云开雨住,只见那晴光万里云西去,洛河一派水东流”。洛河在洛阳东南,可见他们的家乡在洛阳,同剧中另一人物张撇古的家乡河南府是同一城市。北宋以洛阳为西京,由西京而讹为长安,这是本剧流传久远的证明之一。这些情况难以用个人创作或个人创作被窜改加以说明,只有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角度才可以作出解释。
无名氏《合同文字》杂剧,刘天瑞夫妇带了三岁孩儿安住外出逃荒,死在外乡。十五年后,安住送父母骨殖回乡安葬,带了当年的合同文字即证明他亡父并未同伯父分家析产的文书。第一折刘天瑞唱词说:“则为那家私生受了二十年”(《油葫芦》),意即为了保全家乡的祖产,在外漂泊了二十年。同折《混江龙》描写他在外乡的生活:“俺则为人离乡贱,强经营生出这病根源。拙妇人女工勤谨,小生呵农业当先。拙妇人趁着灯火邻家宵绩纺,小生呵冒着风霜天气晓耕田。”这些描写同杂剧所云逃荒后不久就病死的情况不一致。可见《油葫芦》、《混江龙》是同一杂剧另一传本的遗留,情节同《杂剧选》本、《元曲选》本很不一样。《清平山堂话本》卷一的《合同文字记》是第三种传本,可能以它为最早。刘天(添)瑞投奔的不是陌生人,而是姨父张学究,把刘安住头打破的不是刘天祥的继妻,而是他本人。智赚合同文字的关目,那时还没有。《合同文字》的三个传本可以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典型代表。
金元杂剧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它同个人创作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它不忌讳雷同和因袭。从曲白的词句、情节和关目,一折以至整本都有存在。词句如“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一书生”——至少见于《玉镜台》第四折、《冻苏秦》第三折、《小尉迟》第二折、《荐福碑》第一折、《王粲登楼》第一折、《金风钗》第一折、《破窑记》第四折、《醉写赤壁赋》第一折、《射柳捶丸记》第一折。情节和关目,如文人受亲故冷落,被迫出走,等到功名得意重逢时,正要进行报复,别人点明原来以前是亲故好意激励自己,暗中却叫人给以路费送行,恍然大悟之后,一边说:“则被你瞒杀我也。”另一边说:“则被你傲杀我也。”严酷的社会现实化作一场喜剧性的误会,这是书会才人给予失意者的自我安慰,对剧作家同样适合。见《冻苏秦》、《王粲登楼》、《渔樵记》、《举案齐眉》、《裴度还带》、《破窑记》,都是第四折,《红梨花》采用一半;《梅香》、《谢天香》可用而不用,显得别行新意,《踿范叔》可说是它的一个变种。一折或整本的雷同或因袭,如《梧桐叶》之于《拜月亭》、《还牢末》之于《酷寒亭》、《东墙记》之于《西厢记》、《竹坞听琴》之于《红梨花》、《勘头巾》之于《魔合罗》、《抱妆盒》之于《赵氏孤儿》,另外如《薛仁贵》和《飞刀对箭》则各取同一传说的不同段落作为自己的题材,互有异同,正好互为补充。
如上所说,金元杂剧并不忌讳雷同和因袭,这不等于它和中国古代其他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忽视艺术的独创性,或者把它置于次要地位。它的雷同和因袭多半限于题材以及艺术上的粗略之处。在相近题材和相近的艺术手法上往往比在不同题材的不同技法中更不容易见出自己的独创性,因此它在艺术上对作者的要求不是更低,而是更高更严格。同是对《西厢记》的改编,照样画葫芦的《东墙记》,不管它是否白朴的作品,引不起人的兴趣,而郑光祖的《梅香》别出心裁地以梅香(相当于红娘)为主角,以它作为驭繁就简的要领。白敏中与小蛮(相当于张生与崔莺莺)正要幽会而被老夫人撞见,白敏中被老夫人羞辱一通而打发走了。最后白敏中状元及第而奉旨成婚时,想起以前受气,竟装作不情不愿,而女方一家见他以“牙笏半遮其面”,还不知道新郎是谁。《西厢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严肃主题变成了轻松活泼的真正的喜剧。改编者并不认为他有义务忠于原作,这在个人创作中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