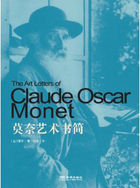不管《录鬼簿》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它将书会才人和名公加以区分却显得目光犀利,意义重大。《录鬼簿》在列举44位“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之后说:“右前辈公卿大夫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用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昔之所学,而舞曲辞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者也。”“列诸首”的董解元实际上不在名公之列。用一个词来概括,这44位“名公”都可以说是文人士大夫。《南史》卷三六记载了一个生动的故事:齐武帝的宠臣中书舍人纪僧真因为不是高门出身,他请求武帝让他做一个士大夫。武帝说此事他作不得主,要他去找江敩。纪僧真在江家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退出。当然,元朝在南朝之后已经隔了八个世纪,森严的门阀制度早就不存在。但士大夫拥有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则没有变化,即使没有官位也一样。上列名公中只有杜仁杰善夫是“散人”,没有官位,但他托儿子的福,赠翰林承旨、资善大夫,死了之后,朝廷还赏给他一个好听的谥号文穆。其他人不是学士、平章,就是将军,至少也得是一个知县(州)或照磨、省掾,这已经是极其少见的例子了。
书会才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低得多。如同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套曲所自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錋錋一粒铜豌豆。”说穿了无非是不怕人欺侮的一个老江湖艺人而已。
当然事物是复杂的,不少人似乎处于两者之间,但是名公就是名公,可以称之为文人士大夫;书会才人可说是文人,但称不上士大夫。
书会才人中白朴也许是相当独特的例子。他的《天籁集》同文人士大夫的集子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他是金朝入元的降将张弘范和史天泽家的门客,同时也是宋朝入元的降将吕文焕家的门客。在当时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不必以气节对他们强作要求为宜。但是看他的仙吕《醉中天·佳人脸上黑痣》、中吕《阳春曲·题情》“则被你个肯字儿,拖逗我许多时”,把他列为书会才人是恰当的。
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和般涉调《哨遍·张玉岩草书》都是典型的士大夫情调,但是他的大石调《青杏子·姻缘·憨郭郎》:“当垆心既有,题柱志须酬。莫向风尘内,久淹留。”这只能是“风尘内久淹留”的招状。
上面是书会才人中带有较重的士大夫情调的两个例子。名公中,如贯云石的正宫《塞鸿秋·代人作》:“这些时陡恁的恩情俭,推道是板障柳青严,统镘姨夫欠,只被这俏苏卿抛闪穷双渐”;中吕《醉高歌过喜春来·题情》:“恰便似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能够折人手,空教人风雨替花羞。”骂情打俏,可说与书会才人没有区别,但他毕竟是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制知诰、同修国史。官位使他列入名公之内。
说到底,有没有官位或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名公和才人的决定性区别所在。我想把才人也称为文人士大夫那是太滥了,它抹去了士大夫和非士大夫即平民的界线。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用力甚勤,而结果则一半可信,一半可疑。可疑的如《虎头牌》作者李直夫。据孙氏考查所得,李直夫官做到行省的肃政廉访使,而《录鬼簿》记书会才人,即使做过小官和吏员的也一一载明职衔。《录鬼簿》记李直夫说“即蒲察李五”,语气轻忽,此书从未这样对待官员。不能因为他仅仅同杂剧作家姓名相同而看作同一个人。《考略》据《滋溪文稿》卷二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查出“《元史》卷一七八的传主、名臣王结之”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也以同样理由不能认为他是《西厢记》的作者。我想,如果充分注意到《录鬼簿》对名公和才人的区别,这样的误会就可以避免。按照《录鬼簿》名公的前例,“奥殷周侍御”、“班恕斋知县(州)”,《滋溪文稿》所写的王德信实甫可以列入名公而绰绰有余。论者以为《北宫词纪》三、《词林白雪》六和《雍熙乐府》一四的王氏商调《集贤宾·退隐》“百年期六分甘到手”,与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元故资政大夫中书左丞知经筵事王公行状》所说的“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相吻合,他们没有注意到《集贤宾·退隐》第一曲“抱孙孙儿我愿足,引甥甥女嫁心休”,《北宫词纪》三和《词林白雪》六都作“免饥寒桑麻愿足,毕婚嫁儿女心休”。两种文本无论哪一种同《滋溪文稿》所说的“贵子”王结的情况都可说是前言不对后语,而《雍熙乐府》十四则没有标明它是王实甫的作品。
顾名思义,书会最早应是说话人的行会。不少人对说话艺术的望文生义地理解,如冯沅君教授就在《古剧说汇》中有一节专门论证《水浒中白秀英所演奏的是诸宫调》,《水浒传》第五十一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的原文是“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着写定者的身份 33章城双渐赶苏卿》”。下接以“但见”开始的对演员的赞词,也即对她说唱的具体描写:“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应该说《水浒》的原文比任何研究者的大着都要可靠,白纸黑字写定的“话本”决不可能听凭一两个人的主张改成“诸宫调”。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说:“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藏蕴满怀风与月,吐谈万卷曲和诗。”可见名为说话,却是说与唱,说与舞同时进行。发展到后来,有的偏重说话,有的偏重唱戏曲,可以一身二任而有所偏重。书会才人可以同时是演员,也可以以编写为主,不一定上场演出。尽管《醉翁谈录》对编写小说的才人提出很高的要求,事实上编写戏曲的才人必须满足更高的业务要求。至少在书面知识上是如此。戏曲有严格的格律包括四声和协韵。因此书会才人同时也是文人,但由于社会地位低落,算不上士大夫。《录鬼簿》之所以将名公和才人加以区别,其意义就在这里。
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十分密切,不知其二,要知其一,简直不可能。原因即在于两者本是同根所生的事实。
书会才人在宋金时代实际上已经产生,虽然还没有找到同他们真实身份相符的记载。上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可以为此作证。入元以后由于科举试停开时间长,即在照常举行时名额大为减少,出路也变得差得多,因此文人大批地沦落为书会才人,喧宾夺主地将原来文学修养不那么高的书林中人挤到一旁,使自己成为它的主流。明代初年洪武永乐时代,尽管文人经常受到政治迫害,但作为社会的一个等级,文人(包括书会才人)的地位有所改观,他们又恢复了原来的身份。现在所能找到的“书会”的最后记录是朱有炖杂剧《刘盼春守志香囊怨》第一折的说白:“这《玉盒记》正可我心,又是新近老书会先生做的。”据梅鼎祚《青泥莲花记》的记载,它根据宣德七年(1432)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写成。
后来,书会就再也不见记载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重校《金印记》第一出云:“闲将六国传,书会好安排。”这是明代文献提到书会的最后一次,可惜年代未能考查清楚。)大多数明代小说和传奇(戏曲)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写定者就由社会地位或低或略高的文人接手了。其实像梁辰鱼(1519-1591)为一扬州盐商取悦妓女杨小环作的南吕《宜春令》,得到“百金为寿”(据《野获编》卷二五《词曲·南北散套》)以及以他的“巧喉倩辅”
“自奏其制”以博取主人和他的伎妾的欢心(《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已经同元代的书会才人很少有区别。但梁辰鱼是文人士大夫,地位已不是书会才人可比,虽然他的表叔王世贞在提到他时还不好意思说他们是表亲。
最后要指出,《录鬼簿》李时中名下所说“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萧德祥名下所说的“武林书会”以及《永乐大典》本《小孙屠》所署的“古杭书会”、《张协状元》所署的“九山书会”应解释为元贞年间杭州或温州(九山)的书会为宜,是普通名词,不是专有名词。正如《张协状元》卷首《水调歌头》所提到“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的“诸宫调”不是专名一样。这里说的“诸宫调”是指南戏中一出为同一宫调的曲子。南戏有好多出,所以就套曲的组织而言是诸(若干)宫调。以现代人的观点去硬套古代的“书会”,是不恰当的。古代的书会是很松散的“组织”,可能没有任何确定的“组织”形式。这有点涉及题外了。
(《浙江学刊》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