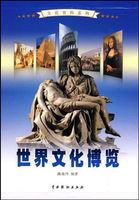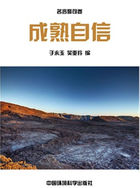切锯:大的玉璞需要切锯,这是琢玉工艺的第一步。良渚人是采用何种方法分离玉料并使其基本成型的呢?从出土器物观察,玉器上留下的工具切锯痕迹大致有三类:直线痕、抛物线痕、圆弧线痕。直线痕相对简单,大概是以高硬度石片等片状硬性物件在玉料上加砂蘸水作往复的直线运动而留下的切割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说的大概就是这层意思。抛物线痕是良渚玉器上所留较多的切锯痕,如张陵山所出的玉蛙和玉环背面的切锯痕便是典型实例。它应是将麻纤维等韧性较大的线状物结成弓锯的弓弦,在玉料上往复拉锯,并不断添砂加水而留下的切锯痕迹。用弓锯来切锯玉料的方法,在古代乃至近代都有广泛的运用。汉代的“马氂截玉”、清代至中华民国时代的“钢丝绞成的弓锯”开锯玉料,用的都是类似的切锯方法。圆弧线痕在玉器上也有体现。如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大玉璧上,一面留有6条直径为21.8厘米的同心圆弧线切锯痕。
寺墩所出12节玉琮和13节玉琮上所留切锯痕,似乎也是同心圆弧线,直径分别为24厘米和12厘米。这是用何种工具或何种加工方法所留下的痕迹呢?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遂忽划断。”当代陈廉贞在《苏州琢玉工艺》有这样的描述:“玉璞安放在架上,不时需要蘸水抹砂,并由两人慢慢拉动钢丝绞成的弓锯,把玉解成小块或片子。如欲琢成一定的形体,那就需用黑线在玉璞上划上轮廓,用附有利刃的圆铁锯装在辘轳的轴端,玉上蘸抹了砂浆,用脚踏动辘轳,依着黑线,慢慢磋切。至于轮廓曲折凸凹复杂的形体,就需用精粗不同的圆锯来修琢。”从已知的切锯玉器方法逆推,良渚文化玉器上所留圆弧线痕或许就是一种类似后代砣即轮锯切锯时留下的痕迹。不过这仅是一种推测而言,良渚文化玉器制作中是否已经用砣或类似器具尚有待更多的证据来佐证。
不管采用哪种方法,只有辅以解玉砂才能达到目的。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已发现有当时使用的解玉砂遗存。如江苏武进寺墩1号墓地的一块玉璧上铺有一层砂粒,经鉴定为花岗岩风化壳粗砂粒,主要成分有钾长石、钠长石、石英和黑云母等,其中石英硬度为摩氏硬度7度,高于制琮、璧的玉料。从草鞋山玉璧上纵横交错的细密的磨纹看,用作解玉砂的砂粒很小,可能是事先已经过筛选。
钻孔:良渚文化玉器大多有大小不一的穿孔,那么这些孔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据推测玉器上的孔大概是用木棒、竹管、细石器加砂粒蘸水不断在玉料上旋转磋碾而成的。良渚时期实心钻多用于小孔的钻琢,通常是手执钻具直接蘸砂碾磨。小件玉器的小孔,用燧石制成的细石器(石钻、尖状器)加细砂蘸水两面对钻而成。有些先以燧石钻对钻出圆孔,再以线锯穿入孔内切割而成。玉器的大孔用竹管从两头对钻而成。竹管在旋转磋碾中容易磨损,从而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圆锥形孔壁。两面对钻避免了一面钻穿通时的崩裂,但常因两头对得不准而造成错缝,在孔内壁留下台阶和钻槽。
打磨:用形状和大小不同的砺石把玉器上的锯切痕或钻孔的痕迹打磨掉,也是琢玉工艺的一个环节。打磨时同样加入了颗粒均匀的砂粒,先粗后细,循序渐进。
从技术分析看,当时可能已采用了轮盘研磨技术。这种研磨技术显然是受到轮制陶器的启发,从而运用一种圆盘状可做圆周运动的简单研磨装置来研磨玉器。反山20号墓出土玉环上的同心圆旋纹,或许就是当时已使用简单轮磨机械的证据。
玉器研磨技术与其他琢制工艺一样,是逐渐进步的,这一点在良渚玉璧器形的演变上得到了较好反映。良渚文化早期和中期的玉璧往往厚薄不均,器表大多留有切割痕迹。到中晚期,则出现了厚薄均匀、器表光滑平整的玉璧。
琢纹:精湛的琢纹技术又是良渚玉器的一绝。良渚玉器的琢纹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浅浮雕结合阴线刻画,这是最盛行的方法;二是纯粹的阴线刻画,线条纤细而浅显;三是透雕结合阴线刻画的镂雕。浅浮雕可通过利用中介砂研磨减地的手段获得,透雕是琢孔结合线切割完成的。那么,刻画阴线的工具是什么呢?良渚玉器上的阴刻线往往细如毫发,有的甚至达到了微雕的程度。如汇观山2号墓出土的一件琮式镯,在宽仅3.5毫米的凸棱上镌刻了14条细密的凹弦纹,不借助高倍放大镜似乎不可能分辨出界限。又如反山出土的“琮王”上的神人的羽冠,以及手、胸和神兽的头部与前肢都刻画得生动逼真,线条细如发丝,甚至能在1毫米宽度内精刻出4、5条细线。有人认为只有天然钻石才能在高硬度的玉器上琢出这样的纹线,良渚先民远征遥远的苏北新沂花厅就是为了取得钻石,因为再向北数10公里的鲁南临沂一带就是古代的钻石产地。江苏丹徒磨盘墩遗址和新沂花厅遗址先后出土过一些石英质料的小工具,器端尖锐,硬度超过摩氏7度。有学者认为,这类高硬度燧石工具,应当就是良渚人的琢纹工具。也有学者认为,鲨鱼牙齿是玉器琢纹的工具,因为在福泉山、反山、瑶山等墓地中出土过鲨鱼牙齿。不管运用哪种雕刻方式,当时很有可能采用了复合式工具,如将燧石钻头、鲨鱼牙齿都装上把柄成为复合工具而使用。
抛光:抛光是玉雕工艺的最后一个环节。抛光的具体方法,可能是把玉器放在木片、竹片或兽皮上,用旋转的木圆轮(或再在其外套上兽皮)“砣床”来摩擦玉器。
脂肪和竹沥皆呈酸性,在玉器上来回摩擦即可取得细腻滋润,平滑光亮的抛光效果。根据民族学材料,云南腾冲曾保留有一种较原始的抛光方法是:将粗竹剖为两半,一半覆盖于地,将玉器在竹皮上反复摩擦,直至出现光泽。
以上表明,良渚人所显示出的制玉水平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程度,也标志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玉技术发展到顶峰阶段。它为之后青铜时代玉雕工艺打下了坚实基础,开拓了辉煌前景。
三、神人兽面纹解读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上,反复出现各种神人兽面纹图案。这种图案有的刻画得十分精细繁复,有的则较为简略抽象,其中最为典型,并且经常被提到的是以下两件精品:
一件是余杭反山墓地1986年出土的玉琮。这个玉琮重达6.5千克,所以又被称为“琮王”,出土时平正地放置在头骨的左下方,为矮方柱体,其表面十分精细地刻着8个神人兽面复合像的纹饰。发掘简报称:神人的脸面作倒梯形。重圈为眼,两侧有短线象征眼角。宽鼻,以弧线勾画鼻翼。阔嘴,内以横长线再加直短线分割,表示牙齿。头上所戴,外层是高耸宽大的冠,冠上刻10余组单线和双线组合的放射状羽毛,可称为羽冠;内层为帽,刻10余组紧密的卷云纹。脸面和冠帽均是微凸的浅浮雕。上肢形态为耸肩、平臂、弯肘、五指平张叉向腰部。下肢作蹲踞状,脚为三爪的鸟足。四肢均是阴纹线刻,肢体上密布卷云纹、短直线和弧线,关节部位均有小尖角外伸。在神人的胸腹部以浅浮雕突出威严的兽面纹。重圈为眼,外围如蛋形,表示眼眶和眼睑,刻满卷云纹和长短弧线。眼眶之间有短桥相连,也刻卷云纹和短直线。宽鼻,鼻翼外张。阔嘴,嘴中间以小三角表示牙齿,两侧外伸两对獠牙,里侧獠牙向上,外侧獠牙向下。鼻、嘴范围内均以卷云纹和弧线、直线填满空档。整个纹饰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肉眼极难看清楚所有细部。发掘简报称它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
另一件是余杭瑶山祭坛1987年出土的三叉形玉器。发掘简报称:这次发现的是一座位于山顶的祭坛,建坛后又成为墓地,因此认为这里埋葬的就是巫觋。这里出土的一些玉琮上也有神人兽面纹,与反山的相仿。而在两件三叉形器上所表现出来的神人兽面纹饰则别具一格。其中10号墓出土的在三叉各饰3组羽状纹,下部用浅浮雕琢出兽面,嘴有4枚獠牙。7号墓出土的左右叉各刻侧面相向的神人头像。神人头戴羽冠,方形脸庞,单圈眼,嘴中用阴线刻出上下两列平齐的牙齿。
中叉上端饰5组直向羽状纹,象征正视的神人像;下端以阴线刻兽面图案,是神人和兽面的另一种组合图形。
除此之外,在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类玉琮上,较多的则是只刻大眼兽面纹或是小眼人面纹,或是两者的组合。用眼来代表整个神像,是一种抽象的艺术表现,一般认为这种抽象图案所表现的内容仍然是前面介绍的神人兽面纹。
上述神人兽面纹在良渚玉器上反复出现,自然也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张光直认为,琮兼圆方,正象征天地的贯串。中孔所穿的棍子就是天地柱。而对琮上的纹饰,他解释为是巫师与其动物助理的形貌。动物可以协助巫师通过天地柱来沟通天地。这里所谓的动物助理就是《抱朴子》中提到的,古代有法术的人骑着“”就可以腾云驾雾,周游天下。所以他认为琮是中国古代宇宙观与通天行为的很好的象征物。林已奈夫则认为琮就是用玉做成的“主”。“主”又称“宗”,是宗庙中祭祀时请神明祖先的灵降临凭依之物,俗称“牌位”。周代天子以木为“主”,称“木主”。士人以成束的茅穗为“主”,称“苴”。而周以前则多以玉为“主”,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玉琮。据此,林已奈夫主张玉琮是祖先崇拜的象征物。邓淑苹则认为玉琮是神只、祖先、神灵动物的“三位一体”。在神人兽面纹中除了神、人、兽3种概念外,还有鸟爪和羽冠所代表的“鸟”。而其中的“人”则应指死去的祖先。在先民的意念中,祖先和自然神有时是糅杂不分的。这些雕琢了特殊花纹的玉器,可能被视为通神的礼器,人们要借助它与神只祖先打交道,以求得福祉。
这只是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此外还有种种说法。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人、兽像属崇拜对象,甚至是偶像神;另一类观点认为图像和巫师作法有关。毕竟年代久远,今人各种观点目前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虽然,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在其他玉器上也有表现,但主要集中在玉琮上,且自始至终体现神人兽面纹及其发展的也只有玉琮。因此,破译玉琮在良渚时期的实际用途,是解读神人兽面纹的关键之所在。而了解玉琮在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实际状况,则是最基本的前提。那么,良渚文化玉琮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第一,玉琮出现在等级较高的墓葬中,但并不是所有高等级的墓葬都有玉琮;玉琮在墓葬中出土位置并不固定,有位于墓主的头部、臂部、腰腹部、脚端等不同部位;在较早的玉器组合中,琮和璧不存在固定的共出关系,而在稍晚的玉器组合中,琮、璧、钺的共出关系比较固定;玉琮通常不与纺轮同出,但玉琮随葬与墓主的性别之间还无法证实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第二,玉琮具有独特的造型,不过内圆外方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早期玉琮的四边、四角并未显示出外方的形态,直至中晚期外方才成形,而早期的内圆发展到晚期,有些已变成不规则的环形。早期玉琮的个体较矮,节数不超过4节。4节以上、个体较高的琮主要出现在晚期。但晚期也有少量个体较矮琮的存在,甚至出现了多节琮改为个体较矮的现象,如福泉山40号墓出土的玉琮。
第三,玉琮装饰纹样繁简不一,且早、中、晚期的纹样有所变化。中期的玉琮纹样形式最为丰富,基本涵盖了晚期的纹样形式,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包括兽面纹、人面(神人)和兽面的组合纹样以及人面(神人)纹;晚期纹样以人面(神人)纹为主,但纹样结构由复杂趋于简单。早期和中期纹样不存在一统的局面,到晚期的人面(神人)纹简化纹样才出现趋同的现象。
第四,根据经过矿物学鉴定的标本来看,良渚文化玉琮一般属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的软玉,也有少量其他石材的,比如福泉山第40号墓出土的两件玉琮属滑石质。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其他材质(如陶、骨、角、木等)的琮及琮类器。可见,制作琮的材质的选择具有比较固定的目标性。有些墓葬中玉器在玉质、玉色上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则十分相近,如反山墓地。
由此看来,玉琮可能是一种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结合体,但就目前考古资料所显示的现象而言,其具体的功用尚不明朗。因此,良渚“神徽”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还需要在更多的考古资料作支撑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节 中国史前玉文化
距今6000-4000年,除良渚文化外,中国境内的其他数个区系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也已显露出文明的曙光。在这些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大多发现了城址、大型宗教活动中心、大型墓葬、图像性文字、铜器等文明因素。也有不少考古文化遗址与良渚文化遗址一样,出土了众多的精美玉制品。发达的制玉业、成组的玉礼器和“唯玉为葬”的显贵墓葬似乎都在表明一点,那就是玉器已成为文明前夜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达的史前玉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礼仪制度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