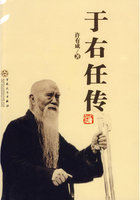孩子去世后,萧红急于出院,她对白朗说,这里除了一个值班护士,只有她一个人住,她害怕。这让白朗很是为难,江津本地风俗忌讳儿媳以外的女人在家里坐月子,房东说:“在家中坐月子晦气,必须红毡铺地才准进门。”
白朗是女人,也是做了妈妈的女人,深知生产是女人的一大关口,产后更需精心护理,好好将养。然而在逃难中条件艰难,白朗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得将刚刚生产过后没几天的朋友送回重庆。
11月的江津,天气已然十分阴冷,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白朗的衣物所剩无多,但见到萧红无衣御寒,她还是尽其所能为“月子”里的朋友准备了几件衣物。萧红独自前来又独自离去,与白朗握别时,凄然地说:“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江上的风呼呼地吹着她单薄的话音,白朗强忍着心酸,安慰道:“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不想萧红却惊问:“我吗?”
她苦笑道:“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1940年春天,白朗收到了萧红从香港寄来的信,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白朗盼望着再次见到萧红,但她的盼望落了空。到了这年冬天,萧红并没有回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白朗和罗烽先后去了延安,从此便与萧红断绝了书信。白朗时时安慰着自己:“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
然而,又一个冬天过去了,又一个春天来临了,他们等到的不是密友的佳音,不是望眼欲穿的归期,却是萧红的死讯,永远的别离……
惊闻噩耗的那一天白朗想起,曾经在江津岸边分别时,萧红幽凄的话音:“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那时的萧红,似乎已然预见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可是白朗依旧不愿相信,那个美丽、聪慧的萧红,何以在不到31岁的青春年华,就离她而去呢?
1938年冬天,萧红从江津返回后,经朋友们帮助,和端木一起住进了歌乐山云顶寺一个名叫“乡村建设所”的招待所里。这里环境清幽,入秋之后游人甚少,有食堂可以吃饭,有莲花池可以玩赏,半山腰有一所抗战期间远近著名的歌乐山保育院,适于写作、静养。产后极其虚弱的萧红,在这里慢慢恢复了身体。尽管孩子的夭亡让她心痛,但也摆脱了此前的困扰和焦虑,了却了与萧军的恩恩怨怨,获得了一份难得的轻松。
萧红乘船离开武汉以后,战局每况愈下。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至此,抗日战争正式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12月,日本反战人士池田幸子和绿川英子先后来到重庆。池田的丈夫鹿地亘在外地忙于反战反日同盟的宣传工作,有孕在身的池田只身前来,住在米花街小胡同。听说萧红也在重庆,欣喜地邀请她来这里同住。
一时找不到住处的刘仁、绿川英子夫妇,也接受了池田的邀请,住进了终日不见阳光的米花街小胡同。于是,三个年轻而不凡的女性一起生活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快乐而悠闲的日子。
绿川英子第一次见到萧红是在1937年,那时她初来上海,“八一三”的炮火迫使她在法租界辗转躲避。其间,她曾偶然地和萧红做了一月余同屋的房客。为了避人耳目,她没敢去拜访这位女作家,只是在灶批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偶尔碰见她。令绿川英子印象最深刻的,是萧红的大眼睛和响亮的声音。
上海沦陷后,绿川跟随丈夫刘仁流亡香港,1938年返回武汉,在郭沫若的推荐下,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中央电台,担任日语广播员。不久,日军特务机关查出其真实姓名,1938年11月1日,在东京的《都新闻》上登出其照片,称其为“娇声卖国贼”,并给其父去信,要求他“引咎自杀”。
绿川再次见到萧红,是1938年12月在重庆街头。那时晨雾未收,照射着湿气的电灯光下,萧红和一年前一样,依旧闪烁着两只大眼睛,然而在绿川看来,却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她并不知道,尽管只是过去了一年,萧红却已然经历了分手、新婚、生子、丧子,还有许许多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
绿川对萧红说:“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也漂亮,而你本人更漂亮啦!”
萧红报以娴静的微笑,以之代替初次和异国同性见面时的酬答。
绿川一直以为,萧红不过和社会上通常的所谓“女作家”一样,过着浪漫的生活,写着优雅的文章,以女色显现于文坛,随着女色的消逝,她们的名字也在文坛上慢慢消失。
直到在池田幸子的邀请下,绿川和萧红同住进米花街小胡同中,她对这位“女作家”的成见才得以修正。在这段短暂的安闲时光中,她们白天尽情享受战时陪都的荣华,夜晚则尽情畅聊与战争毫不相关的话题。萧红善于谈天和唱歌。池田的预产期渐近,不便自由外出,萧红便为她煮自己拿手的红烧牛肉,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她。
令绿川不能释怀的是,相伴不久,萧红便离开了米花街小胡同,去和端木过“新生活”了。不久,他们就自囚在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小世界中;又过了不久,又谜一样地飞往了香港。山遥水远路几千,竟然连一封信也没有寄来。—— 一别便成了永诀……
绿川回忆起萧红的后半生,悲愤地写道:
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
不给人知道,悄悄地走了的她,不给人知道,悄悄地死了。
在这篇题为《忆萧红》的文章中,绿川英子对端木蕻良的怨责随处可见。她不明白,为什么萧红要跟随这样一个男人,过她并不喜欢的生活。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萧红要被端木所支配,甚至一天天加强对他的从属。她更不明白,结婚、生产、苦恼、贫困、疾病等,这些封建时代的女人所踏过的荆棘之路,为什么进步作家萧红也会背负着十字架重蹈覆辙。在绿川看来,萧红后半生的不幸,皆是由婚姻的不幸导致的。她为这位杰出的朋友感到深深的惋惜:在民族自由与妇女解放斗争的行程上,她没有披沐胜利的曙光,带着伤痕死去了,那作家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完成。
令人感慨的是,这位高呼着“妇女解放”,为萧红打抱不平的绿川英子,在萧红去世5年后,亦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上天无情地捉弄了一把这个女权主义者——她死于人工流产手术,享年35岁。
萧红在与这两位日籍女友共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回到了歌乐山,与端木一起生活。
1939年春天,池田幸子生下了一个女儿,夫妇二人都视之为掌上明珠,十分宝贵,为了照顾孩子,生活上不愿受到一点干扰。这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都已是国民政府官员,早已不再是上海滩流亡时的落难夫妇了,而萧红依然很相信过去的关系,常常带着端木前去打扰。这让池田很不快,她向胡风和梅志抱怨道:“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胡风夫妇不好回答,也觉得不便向萧红说。不久,萧红似乎感受到了池田对自己态度的变化,也就不再去池田家了。
她很少从歌乐山上下来,除了买菜等琐事外,也极少和周围的人交往。在简单、宁静的生活中,她与端木一起潜心于创作,完成了丰富的散文、小说作品。在歌乐山期间创作的散文,与之后所写的《放火者》一起,收入《萧红散文》,1940年6月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而在重庆创作的小说,连带在武汉完成的《黄河》,结集为《旷野的呼喊》,1940年3月由上海杂志公司初版。
不过,这一时期萧红的创作产量虽大,却并没有展现出她应有的文字水平,这或许是生活状态过于封闭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