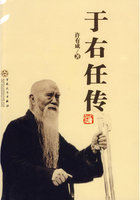萧红和端木重回武汉,也重新住进了武昌小金龙巷21号——半年前萧红、萧军与端木三人大被同眠的地方。
安顿妥当后,端木便计划着要与萧红举行婚礼。在他看来,婚礼不仅是一项仪式或庆典,它更是一项公示,一份夫妻双方所共同信守的承诺。此前,萧红之所以会被汪恩甲抛弃,之所以会被萧军背叛,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他们与萧红之间没有这项契约,因而也就不受正式名分的约束。
端木的提议让萧红感动不已,27岁的她,虽已有过两段实质上的家庭生活,却从没有穿过嫁衣,从没有当过新娘。她可以体会到,端木想给她一个婚礼,是对她人格权利的尊重。
端木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他的三哥,三哥起初非常反对,不理解条件这么好的弟弟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年龄比他大,两度和别人同居,眼下还怀着别人的孩子的女人,这样的儿媳,母亲一定不会接受。而端木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说结婚是他和萧红自己的事,没必要征得母亲的同意。三哥见无论如何拗不过弟弟,只好听之任之,临走前留下一笔钱,供端木安排结婚之用。
1938年5月下旬,端木蕻良与萧红在汉口大同酒家举办了一个简朴却温情的婚礼。这天,端木身着一套浅驼色西装,打着红领带;萧红身着红纱底金绒花旗袍,内配黑色纺绸衬裙,尽管因为有身孕显得有些腰身粗大,但依然与端木组成了文雅又漂亮的一对。
参加婚礼的只有端木家在武汉的亲戚,以及萧红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由端木三嫂的父亲主婚,胡风担任司仪。池田幸子亲自送来一块上好的衣料作为贺礼。萧红把当年鲁迅和许广平送给自己的四颗南国相思红豆,转送给端木作为定情信物。
席间,为了活跃气氛,胡风提议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的经过。萧红感慨道:“剖肝掏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浪漫蒂克式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接着,她真诚地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萧红对端木发自肺腑的感激。争吵、打闹、不忠、讥笑,这些与萧军在一起时受过的伤害让她身心俱疲,她不敢再奢望爱情,而只希求一份平平淡淡的生活。这也是她最看重端木的地方,她知道端木在很多方面不如萧军,但至少,端木不会搅扰她,不会强迫她,更不会伤害她。而今她憔悴如斯,还怀着萧军的孩子,端木却肯为了这样一个她放弃掉自己优裕的生活,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在酒店二楼的头等包房里,萧红与端木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第二天,他们搬回小金龙巷的家,开始了一段平静而平凡的居家岁月。端木的生活能力差,万事皆不过问,萧红并不在意,她怀着一颗愉悦的心,辛勤地安排打理自己和端木的生活,将这个临时的小家收拾得井然有序,甜美温馨。
令萧红不曾想到的是,因为与端木的结合,曾经一些无话不谈的朋友与她日渐疏远。萧红与萧军传奇式的邂逅,萧军“英雄救美”的故事早已在文艺界传为美谈,人们下意识地视端木为“第三者”,认为是他的闯入破坏了二萧般配而美满的良缘。再加上端木个性上的胆怯、自私,为人处世上的孤傲和小资派头,都让朋友们很看不起,他们不明白,端木到底是什么地方吸引了萧红,竟至于让她如此狂热、如此草率地托付终身。
胡风就曾劝萧红说:“作为一个女人,你在精神上受了屈辱,你有权这样做,这是你坚强的表现。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
由于萧军的位置被并无好感的端木取代,朋友们渐渐不愿来萧红家。而他们为萧红抱屈,不满她的决定,自然也伤害了端木的自尊,于是慢慢地,来往也就越来越少了。
回武汉以后,萧红一直在想方设法找人帮忙联系医生,想把腹中的胎儿打下来。可是这时,她已怀孕5个月,胎儿太大,这样的人工流产手术太危险,没有人敢应承。
将近端午,梅志发现自己也怀孕了,她和胡风也认为眼下时局混乱,不宜要这个孩子,于是托房主的夫人带着到医院找熟人堕胎,萧红也跟着一起去咨询。到医院一问才知,人流手术的费用是140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巨款。
萧红也意识到,自己怀孕已6个月,不可能再做人流手术了,何况她也实在拿不出这笔高昂的手术费,只有听天由命,把孩子生下来。
就这样,在与端木蕻良一起安静的写作与生活中,萧红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沉重,行动也一天比一天迟缓。在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时,战争也渐渐靠近了武汉。
1938年六、七月间,日军兵分五路钳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了“保卫大武汉”的战时动员,然而这一口号喊得越响,人心越是惶惶不安。
7月26日,九江失守,日军大规模集结作战部队,积极推进向武汉的进攻。
达官要员、工厂企业、学校、政府机关纷纷迁往战时首都重庆,之前从各地会聚到武汉的各界人士,也都纷纷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长江航道水泄不通,入川的客轮一票难求。
当时,入川没有铁路与公路,只能走长江水路,而长江在宜昌以上进入三峡后,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有些地方甚至仅容一船通过。因此,所有来自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大船,均不能直达重庆,而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方能继续溯江入川。战局的紧张,逃难人群的庞大,更加剧了入川航道的混乱。
萧红和端木也准备迁往重庆。8月初,萧红托罗烽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船票,端木坚持要走两人一起走,让萧红把船票转卖出去,再等机会。萧红则认为船票来之不易,不如两个人暂时分开,端木先走,她有机会再和朋友结伴去重庆,与他会合。
萧红主张让端木先走,原是有自己的打算的。一来她身怀六甲,初到重庆人生地不熟,无人照料,而在武汉至少还有一些朋友可以帮扶她,等一段时间后再结伴入川亦可;二来端木先去,可以在人满为患、住房紧张的山城找个落脚的地方,等一切安顿好后她再过去,也更方便;三来她也担心,若是留端木一个人在武汉,他可能会走不成。
端木见萧红确实想得比自己周全,只得同意了这一方案。临行前,萧红将家里的大部分存款交给端木,仅留下少量的钱供自己零用。端木并未拒绝,在家庭生活中他从不过问钱财之事,自己的收入也一向都是交给萧红安排,这一次,萧红给他“安排”了这些钱,他并不知道萧红只给自己留了那么少,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收下了。
在先行入川这件事情上,端木蕻良在日后的几十年中常常受到诟病,人们或指责他胆小无用、不负责任,或抨击他自私自利、不近人情。其实,若是我们把自己放入当时的情境里,仔细想之,会发现端木的行为也并非不能理解。
萧红诀别萧军,嫁给端木,所实现的不仅是人生的转折,更是家庭角色的彻底翻转。和萧军在一起时,她被视为一个“孩子”,萧军保护她,也轻视她;而嫁给端木后,她俨然变成了一个“家长”,家里一切大小事务都由她来管理,她自然也要“强势”地要求端木服从她的意志。
在二人关系中,一人扮演“孩子”的角色,另一人扮演“家长”的角色,这样是比较好相处的。一旦前者由“孩子”上升为“家长”,与后者的关系转变为两个“家长”的关系,矛盾就会由是产生。萧红与萧军最终走向决裂,除了因为萧军的出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萧红“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也有了不弱于萧军的能力,而萧军却依然用对待“孩子”的方式对待她,以绝对的保护者自居,完全不顾及她的尊严和感受。
反观萧红与端木现在的状态,正是“家长”与“孩子”的和谐状态。端木的“听话”,正是出于对萧红“家长”权威的尊重,让这个“家长”放心、安心。也正因为此,萧红与端木的相处才会比与萧军的相处更和睦、更愉悦。作为局外人,我们没有理由去谴责端木的做法,因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会懂得。
端木走后不久,日军加紧了对武汉的攻势。萧红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小金龙巷,在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她带着行李和铺盖,来到汉口三教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所在地,告诉蒋锡金,她要在这里住下来。当天从武昌搬来避难的还有冯乃超的夫人李声韵,她同样也在等待去重庆的船票。
没有足够的床铺,萧红就在走廊楼梯口的地板上打了个地铺。身怀重孕的她身子越来越沉,行动越来越不便,每天大多数时候都只好躺在冰凉的地板上。
然而,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里,她依然没有放弃写作。8月6日,她完成了一篇近八千字的短篇小说《黄河》,半个月后,又写下了约三千字的短篇小说《汾河的圆月》。今天,当我们读着这些简洁洗练的文字时,我们怎能想象,它们竟是一个怀有近八个月身孕的女人,在空袭频仍的不眠之夜里,卧在冰凉的地铺上写成的……
一天,萧红突然对朋友们说:“我提议,我们到重庆后,要开一间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她接着说:“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座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到最能休息的地方。”
沉默了片刻,忽而又若有所感地轻声说道:“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长久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让她太累了,或许只有借助幻想,才能安抚那一颗疲惫又惶恐的心。在幻想中,她可以构建一个宁静、美好的未来;然而在现实里,她短暂的一生似乎永远漂泊在路上。
难得的是,世界无论怎样丑陋,生活无论怎样贫困,她始终是那个天真纯洁烂漫爱幻想的萧红,这一点,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