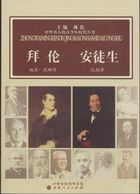香消散·情艰
最艰难的日子,总有最幸福的相随。爱,不是只为了在最美好的时光相守,能在苦难的日子厮守才最幸福。
从山西深山的桃花源中返回俗世,徽因和思成还没从喜悦中回过神,就听闻了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噩耗。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世界的崩溃与惊惶,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国难当头。那是怎样的一个黑暗时期啊,军队从城中走过,每天都能听见门外士兵的喧哗和挖堑壕的号子,孩子的啼哭偶尔一两声,就被惶恐的保姆捂住嘴变成了压抑的哽咽。
可是徽因和思成最担心的,并不是全家老少的安危,而是营造学社几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深思熟虑后,他们将这些资料放到了他们认为——在当时看来也确实如此——最安全的地方,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保险库的地下室。
为这资料做好了万全的考虑,可是他们并没马上离开。梁从诫回忆道:“战争对于父母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也许想得不很具体,但对于需要作出的牺牲,他们是有所准备的。这点,在母亲1937年8月回到北平后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8岁的姐姐写的一封信里(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表达得十分明确。母亲教育姐姐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他们在北平教授致政府的呼吁书上签了名,请求政府抗日,以实际行动支持宋哲元。
可是当时政府的所作所为,伤透了这群知识分子的心。很快,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飘满了日本的太阳旗——日军占领了北平。日本人进驻后,最着急的就是笼络能人为他们做事,没多久,他们夫妇就收到了来自“东亚共荣协会”的邀请函。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起了他们的主意,不走不行了。
徽因和思成并不怕旅行,那么多考察的时光给他们带来了太多行路的经验。可是,这样因为外国人的侵略,背井离乡地流亡,却使他们身心俱疲。思成这时候被诊断出脊椎软组织硬化症,不得不时刻穿着一个支撑脊柱的铁背心,而徽因的肺部空洞更需要注意,稍有不慎就会演化成更大的后果。
他们的第一站是梁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房子,在当时来看这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可是并没能停留很久。根据慰梅的回忆,那时他们还抱有战争能够很快结束的希望和天真:“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总之我们都是好好的,一个星期之前我们到达天津,将要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得少。到那时候战争就打赢了,对我们来说永远结束了。”
可是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扶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长途跋涉后,他们终于抵达了长沙这个他们认为暂时安全的地方。
可是长沙并非他们想象中的乐土——头顶上每天都有飞机隆隆飞过,造成的低气压使人连气都喘不上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沙依然越来越拥挤,街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飞机的警报和人们的哭号每天萦绕在城中,久久不能散去。
徽因他们并没被这样的现实所击倒,清华和北大的一些教授和文化界的朋友们也陆续到了长沙。他们经常晚上聚在一起,到徽因他们的临时住所相聚。“太太客厅”变成了家徒四壁的简陋房间,舒适的沙发换成了小小的板凳和马扎,咖啡和香茗变成了小炉子上的简餐……可是女主人还是那个女主人,睿智、自信、乐观、向上,客人们仿佛回到了北平那些个暖洋洋的星期六下午,回到了和平的旧时。徽因给慰梅的信中说:“一到晚上,你会遇到一些从前在北京每星期六聚会的朋友们在这儿那儿闲逛,到妇孺们来此地共赴‘国难’的家宅里寻找一丝家庭的温暖……在这三间房子里,我们实际上做着以前在整个北总布胡同三号做的一切事情。对于过去有许多笑话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很高。”可是乐观的心情并不能改变战况的不乐观,她说:“我们从山西回北平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一个多星期了,我们亲眼看到那一带的防御能力几乎等于‘鸡蛋’。我就不相信一抗战就能有怎样了不起的防御抗击能力,阎老西的军队根本就不堪一击。天气已经开始冷了,3个月前,我们在那边已穿过棉衣。看看街上那些过路的士兵,他们穿的是什么?真不敢想,他们在怎样的情形下活着或死去!”
空袭很快来到长沙,这使得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小小乐趣。徽因的住宅在第一次空袭中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徽因和思成一人抱着一个孩子跑到屋外时,眼睁睁地看着刚刚还温馨的家毁于一旦。另一架轰炸机擦着楼顶飞过,他们再也逃无可逃,只好留在原地抱在一起——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可是奇迹发生了,掉落在他们身边的炸弹竟然没有炸响,嘈杂声中他们安慰着惊呆了的一双儿女……
大难不死,他们不得不在废墟中翻找家里的东西。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掘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而他找积木。
为了活下去——此时此刻,已经没有比这个要求更高级的需求了。他们全家决定离开长沙,前往云南。这些受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本应作为政府的宝贵财富被保护起来,提供给他们更好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在政府自顾不暇的危急关头,徽因他们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保障。她的情绪难免因此而沮丧:“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干吗不躲得远远地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面对那样没有一线光明的黑暗,面对那样一眼望不到头的绝望,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国难的现实仿佛一面巨大的照妖镜,各种素日里高喊爱国的魑魅魍魉在镜下原形毕露,而各路刚正不阿的正人君子也都在这时体现了风骨。
而这时,徽因却为被剥夺了在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而陷入苦恼和愤怒,更让她心碎的是,那些旧友已经分散到祖国各个地方,“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能得到他们的一点点消息都让他们觉得欢欣鼓舞,可是却求之不得。“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且相互间不通消息。”在经历了苦苦挣扎后,徽因和思成踏上了前往昆明的大客车。
在他们以为已经不会有更糟的情况时,上帝又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在湖南临近贵州附近的小县城里,所有的大车都被征用,他们不得不停留在这个小镇,而徽因的肺病终于不堪重负,复发了。漫天的风雪扑打在徽因高烧到40多度的额头上,化作冰冷的雪水沾湿了衣襟。天无绝人之路,他们终于在一个小旅馆找到了住的地方——那是八个年轻的空军学员将自己的房间让出一间给他们住的。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两周,两周时间,不仅缓和了徽因的病情,也使思成和徽因同那八个年轻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几个小伙子都是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父母、亲人都在沦陷区,但是他们把梁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思成和徽因当成了长兄长嫂,他们的联系一直保持到到达昆明后,他们甚至亲自感受到了这些大男孩由学员成长为飞行员、为国家战斗的整个过程。
经过这样曲折的旅行,他们终于抵达了昆明。即使徽因身体孱弱,病魔缠身,仍然不能阻止她活跃的心。一见到美好的景色就像一个贪杯的人看到美酒。她给慰梅写信说到这些,带着一种喜悦和惋惜:“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昆明的春天,是属于花的海洋,阳光半明半暗、澄明温顺地照在这片大地上,也给予了这群逃难者温暖。在昆明的几年是徽因身体维持健康的最后几年,也是他们遭受更大苦难的一个缓冲。思成的身体越发不好了,徽因不得不担起家务的重担。
她如月光般恬静光洁的面庞被这样的困苦生活刻上了一道道皱纹,她在香山众人呵护下养好的身体被繁重的家务折磨得难以挺直脊梁,她盈盈秋水的眉眼间多了“国破山河在”的忧国忧民,她纤细的身形变得愈加形销骨立,她写出优美诗句的纤纤素手不得不拿起锅铲和抹布……
任何事情都不会一直走向不好的方向,他们在这极大的苦难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乐趣,仿佛前方就是否极泰来的转折。这时,他们借住在翠湖巡律街前市长的宅院里,不久,老金同西南联大的沈从文、朱自清等老友们也赶到昆明了,徽因疼爱的弟弟林恒到达了昆明航校,那几个认识的空军学员小伙子也常常来梁家玩,思成夫妇甚至以家长的身份出席了他们的空军学院结业典礼。
简陋的家里重新热闹起来,“太太客厅”仿佛从北平搬到了昆明。这些朋友都将思念、希望和焦虑压在心底,交换给彼此的都是生活琐事中的细碎快乐。在这样的条件下,思成依然极力奔走,希望恢复营造学社的运转;老金还在忧心联大的校址问题,希望保持中国的大学高等教育;徽因在家务和孩子中间忙得团团转,还抽空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这些家务和工作却没有使她失去审美的眼睛和心。
她在小诗《茶铺》里,描绘了看到的劳动人民的一切。这样温柔恬静的笔触,并不像一个在逃难中的主妇所作,反而像是未经历磨难,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的少女。她说:
……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
白天,谁有工夫闲着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翘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
为了躲避市区不知何时落下的炸弹,他们搬到了市郊并在那里盖了三间小房子——这是这对建筑师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的房子——老金就住在他们后院,他们在这里度过了短暂的美好时光。“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黄家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宝宝常常带着一副女孩子的娴静的笑,长得越来越漂亮,而小弟是结实而又调皮,长着一对睁得大大的眼睛,他正好是我所期望的男孩子。他真是一个艺术家,能精心地画出一些飞机、高射炮、战车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军事发明。”
快乐只能麻痹一时的神经,现实毕竟是有着诸多苦难的。这个贵族千金这时候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他们盖房子的钱甚至都是慰梅从美国寄过来的,老金怜惜而又无计可施地表示:“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可是即使这样的快乐,对于他们都是奢侈的昙花一现。
1940年12月,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联大搬迁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对他们来说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同济大学和营造学社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都迁移至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