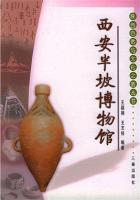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他和她都进入了老年,她退休了,他也离休了。他们一起去了老年大学,他学书法,她学国画。她在宣纸上画花鸟鱼虫,画好了他就在画的空白处题上一首诗,或写一句话,之后盖上两人的印章,一幅作品就完成了。陶陶然,悠悠哉!引得子女们羡慕不已。或者他们一起去打门球、练剑术。出门前,他帮她围好围巾,她帮他扣好扣子,就一起出发了。她经常叨叨他,冷了不知道多穿衣服,出门不知道戴帽子,他只是憨笑着,不作声。他总是顺从着她。他曾跟孙女悄悄说:“只要你奶奶高兴,我就很快乐。”
有一段时间,上小学的孙女和他们一起住,每天晚上,他给她端来洗脚水,放在她脚前。她洗完后又给小孙女端一盆洗脚水,孙女洗完后又给爷爷端来一盆水。机灵的孙女给爷爷奶奶讲了天堂的故事:天堂和地狱的人们都在吃饭,每人都拿一个长把勺子。地狱的人只顾自己吃,但勺子把太长,谁也吃不到嘴里。天堂的人都互相喂着吃,大家都吃得很饱。这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孙女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天堂里,都互相为别人服务,我们生活得很幸福。”祖孙三人幸福地笑了。
20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进入了体弱多病的年纪。两人不是你生病就是他住院。子女们的照顾已经很周到,但是他们还是要亲自到医院去看护对方,他们是不习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生活。有一次她住院了,女儿把他接到了自己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每天早晨,他早早地起来,悄悄地走出家门,来到医院给她服侍洗漱,然后就一整天陪着她。孩子们叫他回家休息,他怎么也不肯回。他说,“我不累。”孩子们只好一日三餐把两人的饭都送到医院。实在太累了,他就坐在椅子上打个盹。那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啊!他不是不累,他是不想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老伴啊。
有一次,八十多岁的他病了,住院了,脑子已经有点不清楚。半夜,从床上摔下来,半个脸都摔青了。他爬起来以后就向门外走去。护士和子女们扶住他,问他干什么去,他对孩子们说:“你妈住院了,我得去看她,她在哪儿?我要去照顾她。”孩子们听得都心酸地掉下了眼泪,安慰他说,妈妈在家没有生病,叫他安心养病,他这才放下心来。他已经病得很重,但脑子里想的还是她,没有想自己。
21世纪,他们迎来了钻石婚纪念日。在子孙们的搀扶下,他们坐在了首席上。蹒跚学步的重孙抱着一大捧鲜花向他们走来,她心疼地把重孙搂在怀里。子女、孙辈、重孙,在舞台底下排成队向他们祝福,深情地为他们唱起了“最美不过夕阳红”。唱得大家都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他和她风风雨雨地走过了六十年,从他们身上,我深深地理解了四个字:相濡以沫。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的女儿曾向我说过:能像姥爷和姥姥那样相伴一生,此生还有何求?
(作者系哈密地区第二中学退休教师)
黑暗中有一盏明灯
陈国栋
北京医院住院部的小窗口前,站着一位中年男子,他拿着一张住院通知单。“大姐,我们是从新疆来的呀!在乌鲁木齐耽搁了三天,病人右眼的视力由1.5下降到0.9,现在只剩下0.3了。您费费心吧,大姐。”中年男子苦苦地向住院部·护士哀求。
“实在没有床位啊!”
“大姐,病人还年轻哪。左眼已经失明,如果右眼再……再保不住,那……”“同志,你的事办完了没有?”
中年男子身后的病人彬彬有礼地问。他回过头看看身后的长蛇阵,侧身让到窗口一旁,让别人上前。等啊等,一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他又凑上前去。
“大姐,俺是抱着满腔希望到首都来的呀!我家里扔下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大姐,你就可怜可怜孩子吧。大姐,孩子是需要妈妈的呀!大姐,你们都是女同志……”
不管小窗口里面回话如何,他没吃没喝,整整站了七个小时,身后来一个人,他便闪在窗口一旁,等人家走后,他又凑上去恳求“大姐”。
“同志,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看!”护士随手递出一大摞排号等床位的住院单,“有什么办法呢?”
“大姐,您就给想想办法吧。”
“同志,你也一天没吃饭啦,先去吃点饭,明天我到病房给你联系一下。”“我不饿,大姐。请您现在就联系吧。”护士从窗口探出头来,对中年男子上下打量一番,她为这位丈夫的痴情深深感动。“那好,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
在护士的恳求之下,病房答应加一个临时床位。顿时,中年男子的热泪泉涌般地流淌下来。他双手捧着住院单,泪水滴到那位大姐伸出的手臂上。
“大姐,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您!”
中年男子名叫祖本元。专程从新疆哈密三道岭来北京给妻子张淑芬治眼睛。
张淑芬原是哈密矿务局二矿的绞车司机。1976年3月,不幸因公负伤,左眼视力消失大半。可她病情稍有好转后,立即返回工作岗位。凭着一只健康的眼睛,又创连续七百二十天无事故的好成绩。然而由于长期用眼过度,右眼受到感染,视力从1.5下降到0.9又到0.3……
祖本元搀着张淑芬走进医院。经过诊断,医生告诉祖本元:“你们来晚了。病人两只眼睛的视网膜脱离,完全丧失视力,仅右眼保留一点光感。手术效果难以设想,有可能恢复部分视力,也许连目前这点光感都保不住。”
祖本元如泣如诉地说:“医生,你们是全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了,我信得过你们……”
“是本元吗?”祖本元尚未迈进病房,张淑芬立即分辨出熟悉的脚步声。“是我。”
“医生说我的眼睛能治好吗?”“能……能治好。”
“那可就好了!可别瞎了,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祖本元的泪水扑簌簌流淌下来。他领着眼睛仅仅保留一点光感的妻子走出北京医院,住进椿树旅社。看着妻子的眼睛要这样瞎掉,他不甘心。他向全国各大医院发信,寻求再一次治疗的机会,有时一天就写三封信。
“淑芬,你想吃点啥?”刚到北京时,淑芬想吃素馅水饺,祖本元跑了几十家饭店,往返数十里总算在一家小饭店里买到素馅水饺。从此,淑芬再也不向丈夫提出自己想吃什么了,祖本元一问,她总是说:“吃点啥都行。”
祖本元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为妻子洗脸梳头、煎服中药,早饭之后,便跑遍北京城为妻子买来猪肝、羊肝、鸡肝、素饺等食品,让妻子吃好。
在北京的日子里,祖本元夫妇受到医护人员、旅馆服务人员的热情关怀,几千里外的单位领导、同志们也时时把他们挂在心上。哈密矿务局去北京开会、学习的干部、群众,接二连三地到医院、旅社看望他们,局工会还派人慰问他们。
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接到张淑芬的病历后,认为她的视网膜尚有修复的可能,愿意接纳治疗。矿务局当即给祖本元夫妇邮来九百元钱。祖本元高兴地说:“淑芬,你的光明在广州!”
谁料到,到达广州当天,积劳成疾的祖本元就卧床难起了。经医生检查,他患的是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如不及时治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窒息,甚至死亡。
出租汽车来了,张淑芬抱起丈夫完全失去知觉的双腿,轻轻安放到汽车座位上。
“淑芬,没顾上给你治眼,我就成了这样!你不能着急,更不能上火,千万不要哭,那样对眼睛不利。”祖本元对妻子说。
“本元,你放心。你看这招待所的领导、服务员对咱这么好,照顾得这么周到,您一定要安心治病。”张淑芬想笑一笑安慰一下丈夫,可是,泪珠却滚了下来……
经过三天的抢救之后,祖本元便请求出院。医生说:“你刚刚脱离危重期,不能中断治疗,尤其要加强下肢功能锻炼。”
可是,本元惦念着那个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妻子,他苦苦哀求医生,硬是出了院。
张淑芬向丈夫说:“本元,医生说让你加强下肢功能的锻炼,那我当你的拐棍,你当我的灯,咱俩一道走!”
黎明,丈夫攀在妻子的肩膀上,妻子按照丈夫“向左”“向右”的口令,两人艰难地行进在林间小路上。朝阳向着他们微笑,鸟儿为他们伴唱。走啊,走,一直走到大汗淋漓……
中山医学院附属眼科医院给张淑芬施行视网膜黏合术的努力失败,愈后不好不坏。医生从术后检查中发现视网膜有个疵洞必须修复,它是再度引起积液的祸根。这就是说,还要进行第五次手术。
第五次手术的过程中,张淑芬不叫喊一声,三天不吃不嚷饿,脏了不说洗,脊背上的痱疮溃疡了,可她连身都不愿翻。希望的风筝,断线了,她绝望了!
祖本元亲切地对妻子说:“淑芬,你千万不能想三想四。不管怎么说,有你活着,咱们的孩子放学回家能喊声‘妈’,一家人心里也踏实啊!”
淑芬说:“我不能再拖累你,你年纪轻轻的,应该再找一个。”“你胡说些什么?!”
“你刚三十多岁,我们要是活到六十岁,还有二三十年,照这样,你太苦了啊!”
“淑芬,再等三五年吧。”
“再等三五年,你都成四十岁的人了,谁还要你?”
“看你说到哪去了。”祖本元向妻子说,“医生说,再等三五年,说不定我国就可以移植眼球了。到时候,我的两只眼睛给你一只!”
丈夫的话,犹如一道闪电、一抹霞光、一轮红日,顿时,张淑芬面前的黑夜里,万物生辉。他和她都哭了。
张淑芬从左眼受伤引起双目失明已经整整五年了。祖本元为了让妻子生活得舒适,在室内布置方面,真可谓用心良苦。他家各道房门都悬挂着软布绣花短帘,一触即知,不必担心碰到门板上。妻子想听收音机,仅需拉动一下延长了的开关拉线,就可以了。卧室里的床体和沙发、座椅,全部采用圆滑软结构,不怕磕碰着人。为了避免房角带来不便,室内东北角放一个大衣柜,东南角放一张圆桌。
他们有时也不断争吵,产生的原因就是丈夫埋怨妻子不该干诸如点炉火倒开水之类的危险活儿。丈夫一上班,妻子就摸着发面、洗餐具、擦门窗、扫地,有时还摸着洗衣服、缝被子呢!
妻子同下班归来的丈夫,放学回家的子女,有说有笑,茶余饭后,祖本元领着妻子到邻居家看电视。画面上的情节,由丈夫边看边讲,不看电视时,祖本元便给妻子读书报,讲故事。笑语欢声之中,妻子乐趣无穷。她的黑夜里,始终亮着一盏闪闪发光的明灯。
(作者系原哈密矿务局宣传部干部,此文曾发表于《新疆青年》,1984·年2·月号)
由下棋到老年大学
达忠书
我退休后一有闲时间就和老伴下跳棋,消遣娱乐,大有裨益。
起初,老伴不大会走,三下五除二就败将下来,可是老伴不服,总要继续再战。她屡战屡败,有时也说点泄气话,我安慰她,胜败乃兵家常事。稍事休息,她又要拉开阵势,结果还是输,她说:“我难道就这么笨吗?”我鼓励她:“你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
老伴下棋有点百折不挠的精神,她那全神贯注的神态真有点可爱。有时电话铃响了,她一点也听不到。我逗她:“我接过两次了,这次该你了。”她竟然说:“我走过了(指下棋),该你走。”我哭笑不得,只好去接电话。她还说:“你的尿真多,憋一会儿不行吗?”到了做饭时间,她还在琢磨如何走好棋,说:“要不怕耽误老头子吃饭,我非走赢这盘棋不可。”两三年过来,她的棋术有了很大的长进,我却成了她的手下败将,她也用同样的话安慰、鼓励我,我们便心领神会地对笑起来。后来我有意当靶子,让她经常练,并动员她去参加比赛,她不以为然地说:“和你下棋是为了娱乐,陶冶情操,对健康有益。参加比赛又有压力,又不自在,何苦呢!”
两岁的外孙女,也常来参与。起初,她看着我俩四只眼睛盯着六角棋盘,两只手四个指头拨弄棋子,好一阵才挪动一个棋子,觉得很没意思,就要我们和她玩别的,我俩当然不肯,外孙女就让我们玩不成,往往把棋子搞得一塌糊涂,有时一把把棋子拨落满地,我俩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实在想玩,只得在她专心玩别的玩具时,背着她悄悄进行。她发现了这个秘密,也想出对付我们的办法:就偷偷溜来猛然把棋子拨到地上,弹跳滚动,噼里啪啦,她却天真地得意地笑着跑开。这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双休日,孙子们也来助战,有的给奶奶当参谋,有的帮爷爷走棋子,这个说奶奶的棋术高,那个说爷爷的棋也不赖,指指点点,比比画画,进退攻守,各持己见,叽叽喳喳,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