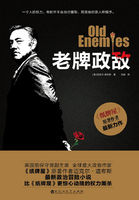1
亚兰前脚走,周明后脚也出了门。
亚兰去的是杭州,周明去的是广州。
头天晚上亚兰才在枕边对周明说,我想还是去吧。去哪儿?周明有些纳闷。去杭州呀!亚兰支起胳膊肘侧身望着周明。就是外语出版社举办的全国大学英语师资研讨班。前年就没去了,今年是最后一次,系里就剩我和丁洁、老黄没去,其他人都去过了。我到现在都不会做课件,别人都学会了,不去怎么也学不会,反正又不花自己的钱。
亚兰怕周明不高兴,反反复复解释。前后就五天,很快就回来了。其实我也不想去,但是没办法。前年就没去了,今年是最后一次,系里就剩我和丁洁、老黄没去,其他人都去过了。我到现在都不会做课件,别人都学会了,不去怎么也学不会,反正又不花自己的钱。亚兰看周明没吭声,以为周明真生气了,又说了一遍。
周明盯着天花板看,目不转睛,神情呆滞。
你到底怎么了?不是说好的吗,谁出差都只能等到头一天再告诉对方的吗,你生什么气呢?(的确,为了不使留守的一方提前感受到不安,两人定了一条规矩,谁出差都必须到头一天晚上才通知对方。)这回是亚兰不高兴了。撤下手肘,背过身去不理周明。
你刚才说什么,去杭州?明天?几点的飞机?
亚兰不理他。
嘿,我问你是几点的飞机呢!
这回轮到周明去扳亚兰的身子。
亚兰还是不理睬。
周明也就没再努力,自己退回身子平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道,我干脆找领导说说,明天我就去广州,用不着推迟了。
你说什么,你也出差?亚兰一听马上转过身子来。
是啊。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亚兰说完就感到无聊了。说好出差的头天晚上才通知对方的嘛。
说实话,本来领导是安排我月底去广州的,我考虑刚从重庆回来就又走你会……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调到明天,我前脚走,你后脚就又开溜了,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省得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亚兰温柔地侧贴到周明的身上。
周明伸手从亚兰的后脖颈下穿过去搂着亚兰,另一只手顺势攀上她胸前的一座山包。亚兰的胸不大,但坚挺,很有质感,结婚十年了依然饱满圆润。她自己也为此时不时骄傲一下。今天出去,回头率特高!有个人走过去了还回头一直看着我,冷不丁一下撞到垃圾箱上,蹭了一身,把我给笑的。亚兰时不时这样说一段插曲。边说边自豪地朝穿衣镜挺起她的前胸。你看你老婆怎么样?光着身子的亚兰自顾自地对镜子说。每当这个时候,周明都会从书房高声说道,那还用说!眼神依旧匀速扫过书页上的文字。
周明加速攀上山包,登上后停留了片刻,围着山尖转悠一阵。
然后迅速下山又攀上邻近的另一座山包,照例停留一阵。在山峰附近像探险者一样动手插红旗。还没插牢,亚兰就发出了浓重的鼾声。周明也就自动停止了工作,平躺着身子,支起屁股颠了颠,感到找到了舒适,就固定了姿势。不一会儿,也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亚兰拎起一个简易的旅行包便出了门。周明朦胧中好像听见耳边有蚊子般的问候声,侧头看见亚兰已经走到了厅里,接着是撞击大门的声音。周明艰难地撑开眼帘,时针正好指向六点零三分。还早!周明对自己说,扭头又睡了过去。再醒来时,周明憋了一泡尿。周明很不情愿地起床,拖拖沓沓挨到洗手间,一口气放掉了膀胱里的水,感觉也顿时轻松起来。回到卧室,发觉时针指向了九点。周明在床沿呆坐了几分钟,抬眼看看梳妆台上含蓄而笑的亚兰,然后动作麻利地洗漱完毕,到书房拎起可以肩挎的皮箱(上次出差用的日用品还原封不动在里面),鸽子似的飞出了公寓。
2
你几点的飞机?亚兰打来电话时,周明正准备登机。我正登机呢。周明说。你还顺利吧?
挺顺利的,我们住在西湖酒店,就在西湖边上,我现在正倚着窗欣赏湖光山色呢。亚兰的声音听起来像从海绵里挤出来似的。
那好吧,多小心呀!不要去洗桑拿,记住哦,别……
我听不清楚。周明说。我要挂机了,我听不清楚。
那好吧,一定不要去洗……后面的两个字没出口就被周明麻利地关死在手机里了。
就是这样。周明和亚兰分头开始了快乐的公务之旅。两年前,基本情况是周明出差多。亚兰,你知道作为一个大学教师,除非去招生,要么去参加学术会议之类,平常哪有出差的机会。碰到寒暑假,更是留守族。除非学校组织去旅游或者参加什么培训。但这种机会并不多,有限的出差都早被系领导当作笼络自己势力的机会私下里瓜分了。总之两年前,亚兰几乎是很少出差,而周明因为在报社工作的关系老出差。亚兰在家待着,周明觉得挺放心,所以出差总是挺踏实的,有时一出门就十天半月,直到报社领导追踪而至,通知他赶快回来发稿,周明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当地,回到北京的家和单位。而且,每次回到北京,他都有一种起腻的感觉。与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各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北京再怎么加紧改造,总激发不起什么新鲜劲。
可是后来,亚兰说不行,这样不行,你总是把我扔家里,自己一个人在外头潇洒,太不公平了。你知道吗,你出差时,我自己一个人在家什么事都不想干。一天亚兰认真地对周明说。
是吗?周明突然理解了为什么每次他出差回来,屋里像乾坤大挪移,原来在厨房的切菜刀都能放在盥洗室熟视无睹,甚至周明出差前做的一锅饭,回来时还滞留在锅里,而且长起蓬蓬勃勃的绿毛。
周明就说,你也出差吧。
我往哪儿出啊。
找呗。
大约从一年前开始,亚兰的差一下多了起来。她跟她在教务处的一个东北老乡,两人结伴,千方百计找招生、培训的机会出差。实在没有,就出门旅游。有次,半个月出门两次,每次一周,你算算,几乎是头天刚回家,第二天就又走,有意让周明尝尝一个人留守时的滋味。周明呢,虽然不会让菜刀躺在马桶上,但一个人也的确懒得做饭烧菜,不是找朋友玩,就是在饭馆将就。所以,绿毛还是到处长,只不过长的物件以及位置不同罢了。
周明就想,得找一个解决的办法。都不出差是不可能的。至少周明不可能。一则职业使然,二则多年养成了习惯,超过一个半月连续待在北京,他会被空气和情绪合谋窒息而死。
亚兰呢,一旦跨出了这个家门,也同样不可能让她不再出门。
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一起出门,你走我也走,分头出差。
3
周明下午到的广州,马上就投入了采访。晚上由采访单位的一把手请吃饭。吃完饭送周明回宾馆大约九点。今天你辛苦了,就早点休息吧。一把手礼貌地说。明天一早周明要采访他,他需要回家梳理和准备一下,所以他无意安排周明去什么地方娱乐一下。这多少让周明有些失望。
周明倒头躺到床上,觉得房间有些冷清。他打开电视,检索了一遍,除了女性胸罩的电视购物节目外,没有一点生动有趣的镜头。
周明颇感无聊,起身到写字台前细细翻服务指南。在娱乐一项,逐一审视。美容美发,电话2228;保健按摩,电话2216;桑拿,电话2457。周明想了想,拨通了2216分机。马上,周明的耳膜里飘进一个女子兴奋且饱满的嗓音:保健按摩,需要服务吗?周明一听就有些内惧、心虚,像被一个性欲十足的女人强暴了一下,他赶忙放下了电话。
重又躺在床上,觉得不安一个劲往上翻涌。四壁透出的好像医院里来苏水的味,让人无法多待一刻。
两分钟后,周明站在了楼下。也没看方向,顺着右手的马路就往前走。几辆出租车很快跟了上来。“要车吗?”几辆车抢生意地轮番问了几次,周明没搭理,三辆车悻悻地撵其他客源去了,只有一辆不死心,尾随着周明。周明想了想,折回身钻进了车里。随便开,满七元就停下来。广州的出租车起步价是七元。司机诧异地扭头看了周明一眼。觉得周明怪怪的,但又不敢吱声。几分钟后,司机说快跳表了,还走不走?周明说停,就停这儿吧。说完给了钱下了车。
夜风明显有些凉,周明下意识耸了耸肩,开始朝来时的路往回走。走了一段,发现后脑勺有块铅似的,回头往后一看,竟是刚才送他来的那辆出租。周明能感觉到司机穿过玻璃窗的眼神,充满了询问和好奇。周明停下步,想等出租车跟上来给他说句放心话。可他这一停下步,出租车司机反倒不好意思了,也停了下来。周明朝他挑了挑眉,相视一笑,就又自顾自往回走去。
走过两段五百米的主路,又走了一段五百米的辅路,右手边一条巷口灯火通明,热闹非常。这是一处大排档,五六家食铺连在一起,五六十张白色小圆桌,二百来张白色小圈椅,大约围住了百来个的身躯,可以想象那是什么阵势。周明走近前,马上有五六个伙计上来揽客。周明今晚吃得不错,胃口还沉浸在上好的鱼翅燕窝汤里,自然涌不起吃河粉和田螺的欲望。又往前走了几十米,左手的一条巷子闪烁着一排发廊的旋转灯箱,给人一股强烈的飘柔和花露水的气息。周明的心里涌起一点奇妙的冲动,身不由己地踏上了小巷的石板路。
十几家发廊左右排过去,周明左右转动眼球,快速扫描过每一家店面,眼角的余光里飞速地闪进各色打扮妖冶的女子。或坐或倚,或招手或蹙眉。的确有些让人口渴。周明不紧不慢走到路尽头,想想又反身折回,重又左右转动眼球,重点把刚才印象不错的脸面重新扫射了一遍。这时开始有女子大方地向周明招手,弄得周明浑身发热,不知不觉又走到了路口大排档的地方。五六个伙计重又一起拥上来拉生意。这回他们已认识了周明,嘴角仿佛在说,瞧,就是刚才进了小巷的那个人。周明脸上这时像蒙了一层地膜,脸上热得湿漉漉的,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似的,三步并两步走出巷子,来到大街上。
往前走就到了海印桥,再往前走一点,就到了宾馆。周明进了大堂,上电梯,进房间。漱口,洗澡,洗袜子,洗毛巾,洗今天路上穿过的背心,直到没什么可洗的了,才躺到枕头上。
躺了大约有二三十分钟吧,还是睡不着。屋里静得只听见空调轻微的嘶嘶声。周明左右辗转,屁股颠了几次,也没有找到舒适的感觉。
突然手机就响了。
你睡了吗?是亚兰。
几点了,你还没睡吗?
我睡不着,正站在窗前看西湖的夜景呢。
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呢。
我睡不着。你呢?
还行吧。你今天起个大早,还是早点睡吧。
你也一样,早点睡吧。
两人说完话,周明关了机。看看表,已是十二点十分。周明又左右翻了一遍身,颠了几次屁股,都没有迈过欲睡和入睡之间的那道门槛。头反而是涨涨的。
周明动了一下去楼下按摩的念头。
说去就去。周明重新穿戴整齐,循指南中的提示,径直来到二楼。
吧台小姐非常热情,引导周明循长廊东拐西拐。就这里。她打开一扇侧门,屋里摆了一张手术台似的床。
吧台小姐让周明在屋里等等。工夫不大,进来一个中等个头、胖乎乎的女子。走近前,周明才看清她的脸抹了一层厚厚的粉。没说一句话,她就动手脱裙子。
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周明连忙制止。
你不做吗?她显得迷惑不解。
做什么?
做这个啊。边说边探手伸向周明的胯间。
周明立马涌起了被强暴的感觉。莫非那个电话真是她接的。
周明抑制不住地浑身起鸡皮疙瘩,慌忙逃也似的出了前台。吧台小姐不知何故,一个劲跟在屁股后头打圆场。
一分钟后周明站在宾馆的大厅前。一辆出租车主动从停车位上开了上来。
周明看也没看,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往右手这条路开,满七元就停下。
出租车二话不说,快速驶上主路。不一会儿,过了那条有一排大排档的巷口,到了刚才打车停车的地方。周明掏出钱转身递给司机时,不禁愕住了。是你!原来竟又是刚才送他的那辆车。司机也乐了,不过并没说什么,接过钱,对周明笑一笑算是回答,也算告别吧。
周明下了车,顺来时的路往回走。
那辆车默默跟在后面,大约有三十米开外的距离。
周明明明知道他跟在后头,却也无所谓了,自顾自往前走。夜风凉飕飕的,让人清醒。周明习惯性地伸手掐了掐太阳穴,甩开大步往前走去,好像是参加一场竞走比赛。那辆车依旧默默地跟在后头。
周明走到那条小巷口,大排档依旧灯火通明。周明出宾馆时,心底里确是想去那小巷看看没准某家发廊没关门,就去做一个按摩的。可是,临走到了巷口,他却改变了主意,外表果决地走了过去。
周明在路灯的护送下,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拐过一段旧街,来到了珠江边。此时珠江的夜景说不上美丽,也不让人迷醉,但倚着江堤,从灯影与夜幕之间,目测建筑与建筑的间距,丈量人与人之间的三围,别有一番心境。周明盯住一朵浪花,看它翻卷起来,沉没,再翻卷出来,再沉没,又翻卷,直到辨别不出是哪一朵。周明就想,水的生命力,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存在而辉煌而执着的,哪怕只有一滴水珠,如果不能结成浪花,它就渗入地下,或者干脆蒸发。周明接着想人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到这一点呢,非要结个伴,成个对。
其实并没有物理的意义,只有心理的聊以自慰罢了。
想完这些,周明觉得自己再无法深刻下去了,于是继续往前走。
走了大约有一公里吧,觉得脚板又硬又胀,于是抛出目光盯住前方路边二十米开外的一张石凳,费劲地走近前,屁股一沉落在上面。
待了大约十分钟,一辆出租突然堵在眼前,司机侧身探过头对周明说,要不坐车回去?
居然还是刚才的那辆出租,他一直就尾随着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