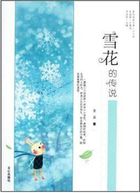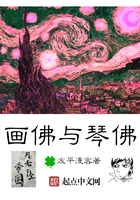师姐穿着睡衣开了门,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一脸诧异。他一把推开师姐,奔到床前,被子一掀,空的。又蹲下来,看床底下,除了个大箱子,几双鞋盒,废纸,厚厚的一层灰,塑料袋,掉的一个卫生巾,小半卷卫生纸外,什么都没有。
师姐这才反应过来,又好气又好笑,问他:“找到没有?”
诗人问:“把人藏到哪里去了?”火气已经消了一半。
师姐火道:“你神经病啊!”
诗人说:“那你怎么不敢接电话呢?”
师姐说:“我手机开的是静音,写论文,再说,我接不接电话那是我的自由。”
诗人又火了:“你牛逼什么?”说着就把师姐扑倒在床上,去扯她的衣服,说,“这就是你不接老子电话的后果。”
师姐边挣扎边打他,憋着嗓门喊道:“你真是个畜生,门还开着呢!”
诗人扑哧笑了,松开她道:“我说你是个婊子你不信,真正的良家妇女在这个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门开着还是关着,而是怎样不被强暴。”
一说笑话,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变得滑稽起来。
师姐从床上爬起来,整理好头发,说:“没见过你这样赖皮的。”
师姐报复诗人这个骚货,估摸着诗人正在家吃饭,故意给他打电话。诗人当着老婆孩子的面接她打来的电话,那声音就极其庄严,先是你好,继而在“你”后面处处加上“们”字,表复数。
据说诗人那傻儿子贼精,能从诗人接电话的语气中判断出男女关系,能从他父亲出门时的穿着判断是否去约会。
有一次诗人自以为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出门前一本正经地叮嘱儿子别看动画片,认真做作业,他办完事马上回来,没想到小家伙一脸坏笑地把父亲从头打量到脚,然后问:“老爸,你玩了多少个女人?你老实交代,我就不告诉妈妈。”
诗人绷着脸把儿子厉害了一通,一出门就笑得不行。
师姐听诗人在电话里一本正经的样子,也故意在电话里逗他,结果是两个人在电话里各说各的,诗人完全答非所问。
诗人在电话里“你们”长“你们”短的,师姐便故意说笑话逗他笑。诗人有时一个人演戏演不下去了,师姐老在电话这头调侃破坏他的庄严情绪,他绷不住失声笑出来,老婆就过来要抢他的电话。
过后见了面,诗人就要扑过来打师姐,说老婆在旁边说是他相好打来的电话,也破坏了他在孩子心目中作为一个父亲的崇高形象。
师姐讽刺他说:“你还顾及你的形象啊,我以为你不在乎。你看你发起疯来,都不像个人。”
诗人说:“不像就不像。”说着就故意要动手动脚,直到师姐暴怒起来才罢手。
有一次诗人赌气,有一周没理师姐,连一个短信也没发,师姐纳闷了,这家伙什么时候这么有涵养起来了?以前他跟她赌气都超不过一天,最后总是他又厚颜无耻地找上门来,也不顾分手时话说得如何地决绝。
师姐已习惯了诗人的骚扰,没有诗人骚扰,生活太沉寂了。师姐心神不定,看书没有效率,这个发现很是让师姐震惊,继而警惕起来。
在和诗人的交往中,她尽量不让自己动情,理智告诉她,诗人这条毒蛇是沾不得的。但还是不知不觉中了诗人的毒,这毒还一时半会儿解不了。
师姐心神不定地等诗人的电话,那是诗人最酷的一次,酷得让师姐油然而生敬意。
两个人谁都不给对方打电话,都在考验对方的耐性,比拼内力,看谁坚持得久。
在电脑前待了一整天,晚上师姐在阳台上透气,一眼就瞅见了那棵桃树下有个熟悉的身影,正鬼头鬼脑地朝她这个方向偷窥。除了诗人,还会有谁呢?师姐心中一阵狂喜,愈发感觉诗人可爱了,这个快四十的老男人,可爱得像个小孩子,对他的怨气也全消了。
师姐拿起电话呼他,响了很久诗人才接起电话,电话里持重得很,一本正经地请问她有何贵干。
师姐调侃说:“我看到一个乌龟头在我阳台外一伸一缩的。”
诗人那个黑影赶快退到墙根处躲起来了。
师姐故意关了手机,回屋关灯睡了。
诗人回去后坐立不安,又悄悄溜到师姐宿舍前,看师姐寝室的灯都黑了,手机也关了,心想师姐竟然睡得着,有些恼羞成怒,便拼命地打师姐寝室的座机,直到把师姐寝室的灯给打亮了,手机给打开了,师姐一身睡袍出现在阳台上,两个人在黑夜里对着手机说话。
诗人赌气这段时间,每天至少来师姐宿舍外侦察三趟,今天中午来了一趟,本想上来打破沉默的,还是忍住了。诗人说:“以后我再也不这么傻乎乎地逞能,硬撑着,这一周过得很难过,不过,倒看了好多书,要是这几年都像这样学习的话,我会成为一个大家。”
有了这次赌气的心理经验,师姐对自己就有些警惕了,害怕对诗人动情,那样事情就失控了。那天两人约好一起上自习,快下自习了诗人都还没出现,师姐沉不住气了,给诗人发了个消息问他在哪儿,诗人竟破天荒地没回。
师姐感觉不对头,多半跟他哪个小情人幽会去了。师姐偶尔在诗人的手机上发现一些可疑的短信,还有不敢当她面接的电话。师姐越想醋劲越大,根本就看不进书。
过了好一会儿,诗人才回了个短信,说在帮他亲戚办事。师姐强迫自己看了一会儿书,刚好有个同学来找座位,师姐就把诗人的座位让给那同学,那同学不知内情,跟师姐说:“我刚才看见诗人了,他肯定不会来了,旁边跟着一个好漂亮好时髦的小姑娘,两人在情人湖边儿散步呢!诗人跟小姑娘谈笑风生,还装作没看见我。”
师姐听得心里酸酸的,强作笑容地开了两句玩笑。下自习的铃声响了,师姐收拾书本起身要走,诗人才匆匆跑来了。
师姐不动声色,强压怒火,装作若无其事地关心诗人事办得怎么样,诗人还没来得及编排谎言,那多嘴的同学就笑嘻嘻地跟诗人开起了玩笑,说:“刚才那个美眉好漂亮耶!”一句话把诗人的谎言堵在了半路上。
诗人没想到被人戳穿,强行抵赖说:“你看错了吧!”边给那同学使眼色。没想到那同学还不识趣,硬说没错。
诗人观察师姐的表情,挂着淡然的微笑,好像并没生气,这才稍稍放宽了心。
下自习后,师姐和那同学有说有笑地走了,诗人约师姐去跑步她也没理,诗人才感觉到问题严重了。
那天下自习回去后,师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诗人面前的全部骄傲被那个不知名的肯定比她青春漂亮的美眉击垮了。唯一能打败师姐的就是师姐不再拥有的青春。
师姐开始检视自己的内心,和诗人交往以来,师姐还从没这么受伤过,难道她一向认为没怎么让自己上心的诗人也不知不觉地具有了伤害自己的能力?
师姐有些后怕,为今晚自己那莫名的伤痛。师姐不想让自己心痛,师姐原以为没人能伤害到她了,一方面是自以为内心修炼到了一定的火候,另一方面师姐也相信她再也遇不到能伤害她的男人了。
那一晚师姐带着心痛入睡,又在心痛中醒来,感受到自己受了说不出口的隐蔽的内伤。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师姐两天没答理诗人,诗人急得面色憔悴,每天可怜巴巴地守在师姐必经的路上,师姐见了他客气地跟他打声招呼,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不管他笑得多妩媚,装得多可怜。
上英语课时,师姐看到诗人头发凌乱,脸色蜡黄,动了恻隐之心。师姐意识到,她越是不理诗人,就说明她自己心里还是在乎他的。这样一想,师姐就又释然了。
下自习后,诗人又可怜巴巴地跟在师姐身后,快到宿舍门口时,师姐猛地站住了,回身看着诗人,问他:“我们去河边走走?”
诗人受宠若惊,小心翼翼地问师姐:“你不生气啦?”
师姐反问:“我生气过吗?”
师姐坐在诗人的电瓶车后座,叫诗人骑稳点,她靠在诗人后背上很享受地闭上眼,吹着河风。诗人完全弄不懂这个喜怒无常的女人,不过也不需要弄懂,云开雾散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