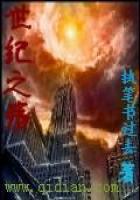师姐停下来,被一幅景象吸引住了——浩瀚的蓝色星空,一弯新月恬静地倒影在护城河中,在夜气馨香中,一衣带水的杨柳婉约婆娑如一幅剪影。
诗人从后面偷袭师姐,恶作剧地把她摔倒在草丛中。他本来没有其他想法,然而,师姐倒地后的惊慌使他起了冲动,他本来是要拉她起来,反倒一翻身把她压在了身下,封堵了她的嘴。
师姐在他身下拼命踢打,越挣扎被他钳制得越紧,他那会儿真有点儿疯了。当诗人放开她的时候,她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朦胧的星月下,师姐长发披散,清秀莹白的脸庞上,一双眼睛黑亮亮地怒视着他。
他把她扶起来,把她的头发捋顺,送她回宿舍,一路无语。
过后诗人为他那天的圣洁而自鸣得意,说他那天其实子弹都上膛了,结果硬是高尚了一把,没抠动扳机,否则就是一百个师姐也难逃他的魔爪。
师姐抗议说:“你不是说要做柏拉图的嘛!”
诗人说:“至今为止,我们还算是半个柏拉图啊,我不是没动你嘛!”
诗人和师姐关系暧昧,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诗人在班里按年龄排行老二,男生们跟诗人开玩笑,私下里把师姐叫做他们的二嫂子。因为诗人是有正房夫人的,因此,这个二嫂子还有另外一个隐讳的含义,那就是地下情人,俗称二奶。
诗人故意把“二嫂子”的事讲给师姐听,师姐开玩笑说,比叫二奶好听点。也不忌讳以二嫂子的身份跟他一起出席各种聚会,对大家含沙射影的玩笑话,也只是笑纳,没有通常女人在这种场面上的假正经。
他看不惯那些假装正经的女人,其实心里想得要命,脸上却绷着,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
师姐不装,似乎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是在乎的。诗人以为师姐对他们的关系是默认了,当诗人想得寸进尺,在言语挑逗中加上点小动作试探师姐时,师姐就认真起来了,打开他的手,正言道:“我再嫁不出去,也不会跟你这样的男人有什么瓜葛的。”
诗人还在嬉皮笑脸说:“我这样的男人怎么啦,我这么多情,又有才华。”
师姐一反常态,以厌恶的表情吐出一个字:“脏!”
诗人很震惊,他没想到他在师姐面前的真诚和赤裸换来的是一个“脏”字,后悔不该什么都告诉这个蛮有心计的女人,看她表面上无动于衷,调侃打趣,原来她是在乎的。
师姐大概也觉得自己言语有些过分,想缓和一下,说:“我爱的男人,我要是他的唯一,我不会跟别人分享。”
诗人跟师姐表白说:“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花心,我之所以花心,原因不在于我的心本来是花的,而是没遇上像您这样兼情人、老婆、朋友、知己为一身的多功能型女人。”
师姐说:“少把这些在别的女人面前说过的俗气话跟我说。”
其实诗人说这话是真心的,尽管这话的确在别的女人面前也说过一两回,但诗人觉得她们都没有师姐更配听这句赞美诗。诗人说:“有了你我谁都不想,我保证以后对别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
师姐凌厉地逼问:“你保证得了吗?这是你做得了主的吗?”
诗人也恼羞成怒,恶狠狠地回道:“那你等吧,你就等着一辈子守活寡吧,看来老女人嫁不出去有嫁不出去的道理!”
诗人蔫了,想想还是家里的黄脸婆幸福,虽然她从来没有单独享有过自己的丈夫,但她是幸福的,她懂得享受,享受美食而不必思考哪些是对身体有害的,享受自己的男人而不必费心伤神是否被别的女人偷食。
诗人不喜欢强势的女人,也许所有男人都不喜欢女强人,但他的红颜知己偏偏个个都是强人。
诗人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一个让师姐臣服的机会。在诗人的理念里,一个女人,只要征服她的身体,她也就臣服了,男人一旦占有女人的身体,再高傲的女人也得放下架子了。反过来,占有身体后,也就失去了兴趣。占有的目的,已经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为了说服自己,学历高的女人也不过如此,Just so so,她的身体和别的女人都一样,甚至不如,不值得想念。
女人诱惑他,但最终是要被他打败的。
诗人邪恶地看着师姐,心想:哪天我把她上了,看她还居高临下不?
诗人邪恶的眼神扫了一下师姐饱满的胸部,就这么一个眼神,师姐这个女巫似乎立即就察觉到了,朝他背过身去。
师姐恰恰不满足于诗人仅仅把她当女人一样的喜欢,师姐相信自己的丰富和特别,可惜诗人并不懂得。她不想和诗人发展成固定的情人关系,她感觉到什么事情一固定下来就不好玩了,就失去了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余地,就成了一盘死棋。
师姐把这个道理也讲给诗人听,诗人不理解,说:“怎么你们女人会有这样的思想,这不明摆着是想多角恋嘛!”
诗人没想到遇到了一个比自己还花心的女人。
在师姐面前,诗人就变成了一个爱吃醋的小性子女人,而师姐则成了个拈花惹草的男人。诗人还没吃过女人的醋,都是女人吃他的醋。
诗人不时蹲伏在师姐的宿舍楼前候着,有次直到宿舍关门前才见师姐被几个人高马大的男生护送回来,谈笑风生的。要不是掂量了一下,自己身单力薄打不过那几个小子,诗人就冲上去了,疯狂的诗人还是保留了一点清醒。
师姐远远地就看到了树影里的诗人,知道他是在等她,跟同行的道再见后,朝他走过来。看他一脸的委屈,知道他要发难,就先发制人,骂他道:“你等我干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疯呢,都奔四的人了,你以为你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啊!我不就是跟几个老乡出去吃个饭唱个歌什么的,你犯得着这么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催逼吗?你自己是有家室的人,我还单身呢,我就不能跟别的同学交往吗?我也不是你老婆,真不知你老婆怎么活?你也太自私了。”
诗人本想跟师姐耍泼,见师姐很生气,也不敢放肆,缓和下来说:“我不是爱你嘛,我爱你才吃你的醋,哪像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师姐说:“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男人吗?怎么不把那兰花指也使出来,难怪人家说你娘娘腔。”
为了监管师姐,怕师姐这个骚货去勾引那些男人,诗人好几天都没有去幼儿园接儿子了,回家后儿子早睡了。
有一次儿子破例还没睡,在等他,扑过来吊住他,两条小腿缠在他的腿上,亲热极了。
儿子说:“老爸(儿子在学校刚学会了老爸这个称呼,立即在他面前显摆),你上哪里去了?你这么多天都没有吃饭,你不饿呀?”
这个傻儿子,以为他没在家吃饭就是没有吃饭。诗人母性大发,把儿子搂在胸前狠狠地亲了两口,说:“傻儿子,老爸在学校吃了的。”
送儿子上幼儿园,送到学校门口,跟儿子再见,儿子快走到教室门口又回头喊他。他问:“宝贝,什么事?”
儿子说:“老爸,晚上你来接我吗?”
诗人说好的。
儿子说:“老爸,你这次不要走远了啊!”
诗人鼻子发酸,都是这个女人害的,他恨师姐,又恨又爱。他想,去她的吧,这么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谁稀罕谁要去!
他暗暗发誓,不给师姐打电话,也不去找她。可是没到一天他就憋不住了,他知道师姐是个犟驴,绝对不会主动跟他求和的。
黄昏时分,他又心烦意乱起来,从幼儿园把儿子接回来的路上,儿子兴奋地讲学校里的事情,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半路上就给师姐打了个电话。师姐没接,又拨,还是没接,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想象力空前活跃起来,师姐身边肯定有个男人,说不定还是她导师,说不定两人此时正在苟且。
诗人嫌儿子走得慢,背起儿子就跑,一口气上了楼,放在家里,跟老婆说导师找他有急事,转身就走。赶到师姐楼前,跟看门的阿姨打了个招呼,一蹿就上了四楼,拍门。他要把奸夫淫妇堵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