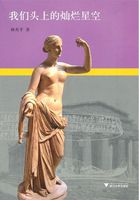斗转星移,时间在紫帽山下静悄悄地流逝,山川寂寥,村落井然,同处在晋江大地上的古闽人与古越人相安无事。不知道又过了多少个日出日落,这两个风俗习惯迥异的族群,纷纷走出各自的屋舍,聚在一起谈笑,一起生活,一起劳作,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闽越族。要是遇到节日或开心事,这个以蛇为图腾的民族,头戴用草扎成蛇形的草圈,赤着双足,裸露上身,围着熊熊的烈火,跳起古老又奇怪的舞步——拍胸舞。
C
栖身于云遮雾绕的山间,暮鼓晨钟,饮山泉,听鸟鸣,是晋江闽越族真实的生活写照。
子玄是土生土长的闽越人,鼻子扁平,个子矮小,须发少,手臂刺青蛇。子玄是无坊裔孙,与其他闽越族一样埋头甜美地生活在晋江境内。他从小听爷爷说,闽地山势险要,山路崎岖陡峭,先祖们筚路蓝缕,拓殖不息,蛮荒之地渐成富庶之郡。
一天,子玄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打听到一件奇事:在千里之外的闽北,有一个强大的闽越国,住着一群幸福的闽越族。这个远房亲戚来自闽越国,是个建筑师,曾参与建造闽越王城。这个亲戚告诉子玄,闽越国是越王勾践的后人无诸建立的,他的诞生洋溢着神奇和豪壮的色彩。公元前202年,勾践裔孙无诸,帮助刘邦战胜了项羽,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同年,无诸修建起了闽越王城。
提及闽越国,这个见多识广的远房亲戚神采飞扬,言语间充满了兴奋和自豪。他说:一到宗教节日,人们聚集到王国的都邑里,平民百姓与商人在这里交易买卖,有肩挑的,有背驮的,有手提的,有走路的,有骑马的,有坐轿的,还时常有穿着不同服饰的“外国人”穿行其间,他们是远方来的使节,向伟大的闽越王进贡。在亲戚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子玄不禁感叹连连:这个富饶的闽越国神秘,美丽,令人向往。
公元前110年的一个宁静清晨,子玄背起行囊,准备前往闽越国探亲,才刚刚走出家门,突然传来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那个强大的闽越国,被汉武帝刘彻包围了;汉武帝还诏令大军将闽越举国迁往江淮内地安置,并焚毁闽越国的城池宫殿。
这一天,是子玄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定居晋江的闽越族近百年的平静被打破了。这一天,黑云压境,晋江四周布满了汉兵,刀光剑影,烈火燃烧,浓烟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血流成河,尸骨横野。这一天,这群快乐的古闽越人突然消失,像蒸发了一样。
在汉军的枪口和刺刀下,子玄与老乡们忍气吞声,拖儿带女,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土,只有少数躲在山上树林中的人才得以幸免。直到多年之后,子玄才弄明白这场人口大迁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闽越王无诸死后,其子孙内讧迭起,频频挑起战争,周边的刘姓诸国不得不纷纷以财物珍宝讨好闽越国。无诸的后代东越王余善,外表看起来臣服于朝廷,内心却一直雄心勃勃。他私刻“武帝”玺,自立为帝,并发兵反汉。为了彻底消除后患,汉武帝诏令大军将闽越国民迁往江淮地区。
这一场大迁徙不但断送了闽越国,也让晋江大片土地的历史改轨,更让闽越族的青铜文明葬身于烟销雾锁中成为历史上的谜团。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在问:闽越的老百姓到哪里去了?他们是留在当地,被同化了,还是离开了福建,流散到他处?这一直是个谜。
2007年,复旦大学博士李辉试图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解开这个古老的谜团。他通过对现代福建和其他闽语人群的分子人类学研究,结果并没有看到闽越的结构。他给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的闽越族在福建地区基本上已经消失,现代闽语支人群并不是闽越人的后代,而主要是北方汉人后代;出海逃亡是闽越族最本能的一种逃生方式,所以南澳岛、澎湖列岛和台湾岛都很可能是闽越族的避难所。
三、一群南逃的人与一条东去的江
A
一身褒衣博带装束的司马放,站在晋安郡(西晋时期,晋江地属晋安郡)的一个江边山顶,抬眼远眺,山峦起伏,满眼葱荣。风起时林涛阵阵,山雀儿高一声低一声,让他神清气爽,数月来的路途颠簸与身心疲惫一扫而过。司马放驻足流连,望向对面的山,又低头移至山下的江,口中喃喃自语:这山、这江与故乡的洛阳是何等相似,何不把此当成归宿之地?
面朝大江,迎风而立的司马放,从兜里掏出一个红的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后,又露出一层白手绢,再慢慢打开,露出了几抔黄土。他抓起一把黄土,撒向江面,眼角处,泪光闪闪。他仿佛陷入了沉思,内心充满了无尽惆怅和忧伤,暗暗思忖:千里之外的洛阳城恐怕是今世再也回不去了。经过数月的艰难跋涉,他与几十个族人来到了重峦叠嶂的晋安郡,决定在这条与洛水相仿的江边安顿下来。
司马放是西晋王朝的一个没落士人,他永远也忘不掉自己与族人在战火中背井离乡的身影。这些痛楚的记忆,就像钉在木板上的铁钉子,即使是多年过后,钉子已经拔出,但刺痛的洞口还是留下了。
时间回到公元304年,西晋国都洛阳城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又一场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肃杀的秋天,一个叫张方的河间王司马颙部将,领着上千骑兵,冲进洛阳城大开杀戒,大城内外血流成河,哀鸿遍野。那时的洛阳人,就像鏊子上的煎饼,绝望而被动地忍受着痛苦。司马放已经记不清脚下这片黄土地历经过多少回战乱,只知道城中13岁以上的男子一律被迫服役,米贵到万钱一石,无数百姓被活活饿死。
伴随着一片片悲伤的哀嚎声和慌乱的脚步声,一支拉着大量金银细软的逃亡队伍向南迁徙。那时,司马放也夹在汹涌如潮的南逃人群中。回望悠悠洛水,神情忧伤的司马放,流下了屈辱的泪水,久久徘徊,不忍离去。
路过昔日最繁华的洛阳城铜驼街,他看到了道路两旁残破的屋舍突然涌出一群饿得皮包骨的饥民,冲过来准备把他们当做晚餐。他被吓得不轻,跳下马车,赶紧往墙角躲。在墙角,他分明感觉到脚底踩着坚硬的东西,低头一看,遍地是吃剩的人的骨架!扔下一些笨重的家当,司马放一挥鞭子,马车便箭似的飞奔起来。就这样他与族人开始沿着长江中下游南下逃亡。
司马放依稀记得他们离开洛阳城的那个月夜,一群把寒光闪闪的大刀举在头顶的匈奴骑兵,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急中生智的司马放,停下脚步,放声长啸,声音激昂悲壮。匈奴骑兵听到了司马放的长啸,个个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们高高举起的战刀又放下,静静地趴在马背上,目送这群晋人渐渐离去。
南逃路上,司马放自己本来就吃不饱,还把粮食分给其他人吃。他让老人和病人坐在自家的马车上,有人病倒了,他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一样照顾。遇有劫匪,他总是亲率家丁打退他们。日子久了,族人们都把他当成大哥,什么事都愿意听他的。
或许是留恋故土的缘故,司马放与这群饱受战乱之苦的西晋汉人起初并没走太远,而是渡过长江,进入了江左。不过,这里的有些地方,似乎并不太欢迎他们的到来。有的干脆把城门一关,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为了给自己找活路,他们只能继续踏上南迁之路。
几个月后,他们辗转来到了晋安郡的一条江边。面对着滔滔江水和莽莽青山,司马放伫立在江边,陷入了沉思。司马放知道,在西晋王朝看来,遥远的闽地是个穷荒之区,朝廷用以处置流放人口;自从孙权于公元257年最后一次用兵闽地,至西晋末年,这里长达半个世纪无战事。他告诉族人,这里是个理想的避难乐土,太平安定,地广人稀,犹如世外桃源。他以前读过《三国志》,上面记载了一件事:260年,景帝孙休以废黜的会稽王孙亮为侯官侯,遣发他往封地,孙亮不愿前往,自杀于途中。
B
又到一年中秋月圆之时,司马放与族人围坐一团,看见一轮圆月从江面上升起,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漫上了心头。遥望着高高挂在墨蓝色天空中的月亮,遥望着那隔了万重青山的故园,司马放用晋人喜欢的胡笳吹起了感伤的曲调。伴随着幽幽的乐声和山中的狼嚎,有人唱起西晋民歌。这怀旧的歌声,在山林中久久回荡,勾起了这群远方游子对家乡的无比怀念,大家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一晚,大家聊起了许多有关家乡的往事。突然,有人说:“月亮下的江水好安静,不知家乡的洛水是否像今夜这般美丽。”又有一人接过话茬说:“这条江真美丽,不如给她取个名字,也叫她洛水,如何?”司马放沉吟片刻之后,徐缓道:“还是叫她晋江吧。”众人大惑不解,司马放却从容一笑,目光中满是憧憬:“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南渡的晋人,沿江而居,以便让子孙后代记住我们是晋人,我们对晋国故土有多么思念。”从此,这条古老的江,有了自己的名字:晋江。
身为一个没落王朝的士族,司马放骨子里透着浪漫主义情怀。在晋江流域站稳了脚之后,他与族人开始泛舟游弋于晋江流域,顺流而下,探究晋江的秘密。在深沪湾,司马放偶遇了一户以船为家的疍民。见到陌生人走近,疍民连忙拨着桨,船缓缓地移向海中央。这时的司马放,一种莫名的酸楚涌上心头,泪眼朦胧。司马放知道,疍民一定是误会他了,以为身着宽袍大衣的他是官府派来的。他听一同南迁的族人说,穿行于晋江海域夹缝中的疍民大多是古闽越族遗民,他们在汉武帝的追杀下,逃入江海避难,过起水上生活。有的官府甚至与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凝视着疍民远去的背影,司马放内心生出无限感慨:和疍民一样,他们漂泊、迁徙、避世;不同的是,他们躲进深山老林,而疍民却隐身于汪洋大海。几百年过去了,疍民们结庐海湾,随时迁徙,如同漂浮于盐水之上的鸡蛋。只有遇到台风天,疍民才在港湾滩涂兴建木屋,短暂定居下来。
这一天,司马放又与族人沿着晋江下流,向西岸追寻这片土地的秘密。这是一片蛮荒之地,树冠浓密,藤萝纠结,虎象巨兽出没其间,毒瘴厉气弥漫山谷。在八仙山的一个向阳山坡上,翠绿的油松和落叶松掩映着一间木屋。轻叩木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探出身来。发现来者是一个身穿粗麻布的汉人,老人的脸上写满了不安和讶异。司马放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说明来意,大体是说:“早闻有些中原人被流放这里,初来此地的我们过来探探路,看看有没老乡。”听到久违的乡音,老人放下戒备之心,跟他攀谈起来。话未说完,老人泪眼婆娑。原来老人的祖父,犯了事,被朝廷抄了家不说,还把他们一家遣送到这里流放。他不仅要向土生土长的土豪租地服役,战时还要替豪强上战场打仗。听了老人这般话,司马放惊出了一身冷汗,想想有些后怕。不过,他转念一想,还好他们是举族迁居这里,有四五十号人马,谅土著豪强也不敢拿他们怎样。
一次次的穿越丛林山谷,一次次的趟过山涧溪谷,司马放在晋江流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除了疍民和山民之外,还有汉末留守的军人和避难入闽的北方汉人。这些北方汉人,跟司马放一样,都是为躲避战乱举家举族而来。
C
箭矢的飕飕声顿时惊醒了清晨的建安郡,一片片喊杀声和惨叫声顿时响彻了山城的上空。身穿粗布衣的起义军,个个手执毛竹制成的长筅和四面带刺的竹刺笼。他们扼守南北城门,用竹刺笼把官军前进、后退的道路完全截断,廊道两侧则是长筅齐出,穿透了一排排惊慌失措的官军身体,几十个官军应声倒地。其余的士兵也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无人再敢轻举妄动。在凌乱散落一地的断肢残骸中,人群中有人认出了建安郡太守傅湛的尸体。拖起这具冰冷的身躯,众人消失在丛林深处。
这是小武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祖父是这起发生在晋太元四年(379年)闽人反抗东晋王朝起义的亲历者。这起刺杀风波消息传到东晋国都后,朝野震惊,后来浓缩成了《晋书.孝武帝》上的一段文字:“晋太元四年……九月,盗杀建安太守傅湛。”
生活在灵源山下的小武,是土生土长的山民。与迁居此地的汉人待久了,他也跟着说中原话,也写方块的汉字。尽管如此,他总觉得族人与朝廷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隔阂,就像是横在心上的一块巨石,沉闷而痛楚。小时候,小武常听祖父亲口讲述村中的一些秘事。祖父告诉他,在一个世纪前的东吴时期,“孙权”绝对是一个敏感词,这个中国兵法家孙武之裔孙,五次用兵闽地,每次都是冲他们而来。原来孙权一直想要把闽地的山民收编到自己的军队中去,然后将他们带到江南作战。可是这里的山民,偏偏不买账,如此一来,战争一触即发。
任凭时光流逝,终究无法消弭山民与朝廷之间的纠葛。恰恰相反,历史积淀下的仇恨,让这隔阂渐深。与祖辈一样,小武身上流着愤怒的血液,他不理解朝廷为何把他们列入最低等级,为什么他们总是遭受江南大族的白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