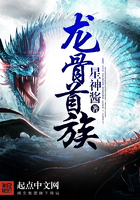中国古代顶尖的大诗人,也就是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白居易(772-846)在他们当中是比较罕见的。所谓“罕见”,不是讲他诗歌的思想艺术境界格外出众,而是指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其他诗人所不具有或不完全具有的一些鲜明而突出的特点。
“唯歌生民病。”深切地关心人民疾苦,多方面地揭示他那个时代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是白居易诗最可贵之处。白居易生活在中唐时期,盛唐的繁荣富庶已趋耗竭,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政治动荡,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加剧,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白居易在政治漩涡中心的官场,目击丑恶现象,愤而作诗。他的《杜陵叟——伤农夫之困》,题目就揭示哀伤农民的困苦。诗里说长安近郊杜陵的一个老农种些许薄田,三月无雨,麦苗黄死;九月早寒,禾穗青干。这样颗粒无收的荒年,地方官明知,而仍然“急征暴敛求考课”(用超额搜刮赋税的“政绩”来求得考核升官),弄得农民“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白居易痛斥残民以逞的官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统治者对农民超经济的剥削,花样繁多。地方官为了讨好皇帝,“正税”之外再加私敛,进贡皇帝“私库”,还美其名曰“羡余”(盈余)。《重赋》一诗,抨击“羡余”的残酷:“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鲜明地揭示了官吏为自身前途,敲骨吸髓地搜刮劳动人民的生活所资,损不足以奉有余,供皇家糟蹋。
还有“宫市”,皇家所需物品在市场上强买,实际上是公开的掠夺。唐德宗时用宦官专管其事,设“白望”几百人在市场上寻找所需货物,宣称“奉旨”采购,随便给一点钱就算是买的。白居易的《卖炭翁——苦宫市也》,专写“宫市”虐民。两鬓苍苍的卖炭翁,千辛万苦烧得一车木炭,为了卖个好价钱,盼着大雪寒天,身穿单衣,腹中饥饿,赶着牛车……却遭“宫市”之劫:“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指望卖炭,换取“身上衣裳口中食”的老翁最后的生存条件被剥夺了。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每年都要向皇帝进贡土特产。地方官为了讨好,挖空心思把产品加工得精益求精而全不顾劳民伤财。《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揭露宣城太守向皇帝吹嘘当地能织出比太原毯、蜀都褥更加温厚华美的红线毯,宫女踏在上面跳舞,越发翩翩多姿,皇帝十分欣赏,年年派使者索取。白居易愤而指责:“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的命运,也受到了白居易的关注。《上阳白发人》一诗,揭示最高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淫欲和供他们役使,常强选大量民间女子入宫,不让她们婚配,老死深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原本应当享受青春幸福的民女,就这样在深宫空房凄风苦雨中了此残身,是何等的惨无人道!
《新丰折臂翁》一诗,白居易沉痛控诉了不义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史载,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哥哥、宰相杨国忠好大喜功,发动扩边战争,七万人全军覆灭。新丰折臂翁诉说他幸存的经历,用巨石敲断右臂,逃避兵役。“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塚上哭呦呦。”诗歌艺术地反映了生活真实,描摹了一出骇人听闻的惨剧。
由于白居易所处的现实社会太黑暗了,诗人情不自禁地把抨击的烈火烧向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他憎恨和诅咒种种不合理的制度,以及极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揭露权贵的荒淫,同情人民的不幸,为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而呐喊。他无愧为那个时代的精神界的战士。从这个角度看,白居易的创作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罕见的。
难得的是,诗人在关心穷人疾苦的同时,常常把自己“摆进去”。每当想到自己当官、安享纳税人上交的俸禄,而穷人却啼饥号寒,受苦受难,愧疚之心便由衷而生。如《村居苦寒》:“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观刈麦》中写一位贫苦农妇抱着孩子在田间拣麦穗:“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白居易怀着“达则济天下,岂独善一身”的良知,希望普天下的穷苦人都能温饱。他在《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诗中说:“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这种愿望,同杜甫所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出一辙,也只能是聊以自慰的空想。
贫富悬殊,贵贱对立,社会不公,是封建体制的痼疾。白居易对这种现象,怀有强烈的憎恨,并且撷取为诗作的重要题材。例如《轻肥》,一边是“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的宦官们的穷奢极欲;一边是惨不忍睹的社会悲剧——“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一边是“朱紫尽公侯”,“日中为一乐,夜半不能休”的享乐“天堂”;一边是人间地狱——“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白居易继承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精神,烛照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从而给人以更加强烈的心灵震撼。
古代诗人的创作思想倾向,多从他们的诗歌中自然流露。唯独白居易自觉地用理论形态比较系统地阐发了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和审美理念。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旗帜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观点,诗歌的作用在“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强调诗歌创作要考察政治得失,表达人民愿望。在这封信中,白居易还申述了对诗歌的审美理念:“诗者,根情苗声,华言实义。”用花木来比喻诗的思想内容(“根情”、“实义”)是根本,是诗歌的灵魂;艺术技巧(“苗声”、“华言”)是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进而批评了六朝诗歌“嘲风月,弄花草”的形式主义唯美倾向。正是在上述创作思想指导下,白居易写了大量的揭露政治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是白居易全部创作中最有批判力量和战斗意义的精华。白居易说,他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的一些诗,戳到了权贵们的痛处,他们读了之后,有“众口藉藉,已谓非宜者矣”、“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执政柄者扼腕矣”、“握军要者切齿矣”。强烈的反响,也印证了白居易自觉的创作思想对于他的创作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
白居易诗歌创作,追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的文风。前人笔记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曰解,即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这虽然只是传说,但宋朝诗人曾看过白居易诗手稿:“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说明白诗的流畅动人,是经过了认真的艺术锤炼的,因此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不无自豪地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仆诗者。”元稹也肯定这个事实,并加以补充:“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上到宫廷,下到旅店,上到王公士大夫,下到市井小民、仆役妇女,到处都题写、吟咏白居易的诗,而且有人精心缮写拿到市场交易或用来充当酒钱茶资的。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一些邻近的国家和民族中,也曾得到相当普遍的流传。日本嵯峨天皇就曾抄写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哦。宋代契丹国王也亲自翻译白居易的诗诏群臣诵读。一个古代诗人的作品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读者,确是罕见的现象。
上面所说的白居易诗歌的罕见可贵之处,是他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诗人也有不少消极之作,特别是他上书言事、写诗讽刺,得罪权贵,遭到贬谪之后,早先的“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的锐气消失了。他明哲保身,不敢再过问政治了。“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曾经的精神界的无畏战士,蜕变为乐天知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庸人,白居易的诗作由此失去了战斗的光芒。这是令人惋惜和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