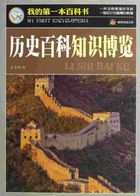而当时真正有能力有才干的人,都是出身低微而且被当时的道德伦理所不容的,比如张汤、赵禹、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等人。因而,这个时代不是不需要贤人,而是太需要贤人了。但是,如果真的有了贤人,又不能保证不受公卿权贵的排挤迫害,所以他们只好一个个扮成放荡不羁的样子来掩饰自己的光彩。
这一点,是东方朔在回答博士儒生们的时候没有说的,因为不能说,一旦说了,马上会引起权贵的注意和打击。事实上,东方朔也是借古讽今,用古人的情况和理想中的情况,来影射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合理。那些不懂世事的儒生博士们只听到东方朔有理有据的经典言论,而不知道东方朔这番话背后的一片苦心。
滑稽人生的最后箴言
因为东方朔有才干,又懂得韬光养晦,不和权贵发生冲突,所以汉武帝十分欣赏他、信任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需要他回避,甚至汉武帝和后妃们调笑鬼混的时候,东方朔都可以站在房门外等候。但是汉武帝和东方朔都明白,东方朔现在没有发展的空间,那些功臣后代不会甘心退出政治中心,所以东方朔难以有出头之日。就像当年汉文帝召见贾谊的时候谈的只是鬼神之事一样,汉武帝和东方朔在一起,谈的也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有一次,在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中,有一只动物跑出来,它的形状像麋鹿,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四不象。这个消息传到宫中,武帝十分好奇,亲自到那里观看。看了之后,武帝不认识这种动物,就问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知道它是什么动物。汉武帝比较失望,特别下诏叫东方朔来辨别这是什么动物。东方朔来了之后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请赐给我美酒好饭让我饱餐一顿,我才说。”武帝说:“可以。”吃过酒饭,东方朔又说:“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陛下赏赐给我,我才说。”武帝说:“可以。”于是东方朔才说:“这是叫驺牙的动物。远方当有前来投诚的事,因而驺牙便先出现。它的牙齿前后一样,大小相等而没有大牙,所以叫它驺牙。”后来过了一年左右,匈奴浑邪王果然带领十万人来归降汉朝。武帝于是又赏赐东方朔很多钱财。
其实,所谓的远方有投诚之举而国内先出现预兆的说法,只不过是古人的一种迷信,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因为当时全国上下都相信这样的说法,所以出现了特别的自然现象,比如出现了这只驺牙,就特别地受到关注。而当时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匈奴的投降甚至要求归顺都是情理中的事情,东方朔只不过是借这个特异现象来表达他对政治的看法,这个做法符合了武帝的心思,所以武帝才对他十分宠信。
可以说,如果东方朔就这样结束一生,那么他一定会被后人当成一个庸庸碌碌蝇营狗苟之徒,因为他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来。可是,他一生的谨慎和低调,都是为了生命中最后的辉煌,为了把所有的理想都绽放出来,得到皇帝的采纳。
到了东方朔临终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去规劝汉武帝。他说:“《诗经》上面讲,‘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我希望陛下能够远离那些巧言谄媚的人,摒弃他们的谗言。”
东方朔这番话,说得含蓄但是不失尖锐。他表面上没有说汉武帝应该远离哪些人、贬退哪些人,但是当时中央的政治局势,正是很多小人利用汉武帝意气风发、爱听奉承话的弱点努力钻营并且取得了一定职位的时候。这些人身居高位,但是除了进行权力争夺和互相倾轧之外,没有做过什么有建设性的工作。另外,那些功臣后代也是除了骄傲自满、狂妄自大之外没有其他能力的国家蛀虫,不适应汉武帝时期积极进取、进行国策调整的需要。东方朔这种欲言又止的做法,并不是闪烁其辞求得自己的平安,而是想要让汉武帝自己去思考然后作出决定。
东方朔大半生都在游戏人间,但是到了最后的日子,说出警示汉武帝的话,并且把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中央政治,他一生的委曲求全,都是为了寻找一个最适合的机会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东方朔的悲哀,到了临死之前才能说出心里的话,不过这样评论似乎过于简单化而且不切实际了。
事实上,儒家强调“朝闻道夕死可矣”,反过来说,也就是只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得到肯定和承认,那样就不枉此生了。东方朔正是这样的人,他一生隐忍,就是为了最后能说出心里话,所以,他不算是遗憾的,如果说这个现象是一种悲哀的话,那就只能说是当时政局的悲哀了,有才能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只能沉潜下去,混迹于官场的交游和虚假的人情中,而且还是在西汉号称最美好的时代——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
汉武帝听了东方朔的这番话,十分感慨,他说:“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
其实,汉武帝对东方朔提到的这个情况也有感触,只是没有进行处理、也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罢了。朝臣们因为需要互相掩护互相扶持,也没有人能对汉武帝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汉武帝觉得无人支持他的想法。这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如果谁都不去捅破,看上去就像是永远都不会破一样,但是只要有人伸手出去,窗户纸马上就变得不堪一击。而东方朔的这番话,就是对朝政这层窗户纸伸出的手,汉武帝再要伸手去捅破它,在心理上也就容易多了。
东方朔说出那番话之后不久就病死了,但是他的建议却被汉武帝牢记,并且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实施了。东方朔把朝廷当做山林来隐居,为的不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是找寻合适的机会,摆脱隐居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在传统政治的酱缸中挣扎甚至逆来顺受,不是想要变成酱缸中的一部分,而是要彻底改造这个酱缸。他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了改造的机会。
2。魏征:长袖善舞
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臣子性格。有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南宋出了个大奸臣秦桧,许多南方人都以姓秦为耻辱,于是有一次,皇帝发现当年科举考试的状元姓秦,就问他:“你是南秦,还是北秦?”如果是南秦,就有可能是秦桧的后代,这样一来在皇帝眼中这个人的印象分就会差很多。这位状元头脑倒也十分灵活,当场作诗一首回答皇帝:“莫问南秦与北秦,一朝天子一朝臣。历代忠奸相对出,如今淮河也姓秦。”这位状元的回答既巧妙回避了自己的出身,又暗示皇帝,只有宋高宗那样昏庸的君主在位,才会有秦桧那样的奸臣把持朝政,如果政治清明的话,奸臣自然就没有容身之所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环境与大臣品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整个的政治氛围都是混浊黑暗的,那么再清白高洁的人都无法立足,如果政治氛围是开放的清明的,那么佞臣奸臣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这是一个比较令人灰心的环境造人的情况,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政治氛围形成了某种惯性的因素,身处这个氛围中的人就不得不受其制约,不能融入这个环境的,就要被淘汰出局,因为环境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因素,也是许多身处这个环境并且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的个体在维护着、巩固着的有生命的力场。因而,在政治清明的时代,那些敢于畅所欲言的大臣,也许并不是真正的耿直,或许只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所进行的作秀而已。
中国古代以进谏而著称的魏征,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秀者。这么说可能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在人们的印象里,魏征就是一个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形象,确实如此——看上去很美,但是实际上,谁又知道呢。
几经沉浮雨打萍
魏征的出身实在是不算好,他的家族并不显赫,只能算是当时的“小农场主”,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从魏晋时代开始,在政治上就强调家族门第的作用,出身低微的人,除非遇到特殊的事件,否则是永远不可能成为公卿宰相的。
到了隋唐时代,虽然门第的作用不像以前那样重要了,但还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朝廷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家庭出身还是一项重要内容,所以家族门第不那么高的人往往要通过各种方式抬高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伪造出身,攀附门第,或者是通过重金收买那些门第高但是已经破落的家族,硬生生把自己的家族塞进人家的家谱中,名正言顺地变成优等门户。
魏征没有那么做,或许是他觉得用不着,或许是因为没那个能力,不过他总算是遇上了一个好时候,那就是隋朝末年的大起义,天翻地覆慨而慷,一切都靠实力说话,有能力有计谋的人才是最受欢迎的,门第成为鸡肋,起义军甚至见到出身高贵的人就杀掉,因为他们觉得正是这些人帮助隋朝的皇帝去压迫自己。因为这个原因,魏征的出身劣势一下子变成了优势,而且他凭借着自己青年时代学过的《左传》这些书本上所记载的谋略和纵横家的学说,为义军领袖献计献策,很是有些作为。可以设想,如果起义军最终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工作,那么魏征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开国功臣而享受荣华富贵。
可惜,事情总是事与愿违,曾经声势浩大的起义军,还是没有把皇帝的宝座掌握在手中,反而是出身于隋朝国戚和高官的李渊发动了军事叛乱,最终统一了全国,而魏征也从起义军中的谋臣将领一下子变成了被收编招安的降将,而且还不是高级降将,其在唐朝初年的地位可想而知。
不过,处于开国阶段的唐朝对人才还是特别看重的,所以,魏征终于有了机会,成了太子李建成的东宫属官,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太子的班底。说到这儿,就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隋唐之际的时候,那些大家族出身的人归降唐朝之后,多数是投靠唐高祖李渊的——因为李渊可以任命他们做高官,而大家族成员除了李渊之外,选择的另一个主人则是当时到处领兵打仗的秦王李世民,而不是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身边的人,最为得力的,又是那些没有家族背景的社会中下阶层人员,比如魏征、王珪等。
如果说政治路线的区别造成了这样的分野,从历史上来看,李建成和李世民在当时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不可能会形成这样泾渭分明的界线,所以,我们只能从谋求个人权力与地位这个角度来解释那些没有家族背景的士人投靠李建成的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