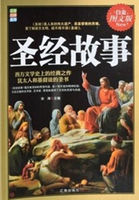[27][后秦]僧肇集:《注维摩诘经》卷一,《大正藏》第38册,第331页上。
[28]《佛说法集经》卷六,《大正藏》第17册,第650页上。
[29]《佛说法集经》卷六,《大正藏》第17册,第643页下~644页上。
[30]该经梵文本已发现,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泉芳璟校刊出版(京都,1934~1936)。
[31]后世所流行的《华严经》是唐代实叉难陀的八十卷译本,其中《入法界品》中的观音译作“观自在”,故抽出的有关善财参拜观音菩萨的经文称作“观自在菩萨章”。
[32]《华严经》卷五十,《大正藏》第9册,第717页下。
[33]《佛说罗摩伽经》卷上,《大正藏》第10册,第859页下。
[34]《华严经》卷五十一,《大正藏》第9册,第718页上。
[35]《佛说罗摩伽经》卷上,《大正藏》第10册,第859页下。
[36]《佛说罗摩伽经》卷上,《大正藏》第10册,第860页上。
[37]《华严经》卷五十一,《大正藏》第9册,第718页中。
[38]上述词语均引自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卷五十一,《大正藏》第9册,第718页中。
[39]《佛说罗摩伽经》卷上,《大正藏》第10册,第860页中。
[40]《华严经》卷五十一,《大正藏》第9册,第718页中。
[41]《佛说罗摩伽经》卷上,《大正藏》第10册,第860页下。
[42]《华严经》卷五十一,《大正藏》第9册,第718页中—下。
[43]《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217页上。
[44]《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687页上。
[45]《大智度论》卷二十六,《大正藏》第25册,第255页中。
[46]《大智度论》卷三十,《大正藏》第25册,第283页下。
[47]《大智度论》卷三十三,《大正藏》第25册,第305页下。
[48]《大智度论》卷五十一,《大正藏》第25册,第309页上。
[49]《大智度论》卷四十,《大正藏》第25册,第350页上。
[50]《大智度论》卷四十,《大正藏》第25册,第350页下。
[51]《大智度论》卷七十五,《大正藏》第25册,第615页上。
[52]经云:“弥勒、文殊、观世音、普贤等而为上首,如是等恒河沙诸大菩萨,若人于百劫中,礼敬供养,欲求所愿,不如于一食顷礼,拜供养地藏菩萨。”见:北凉失译《大方广十轮经》卷一,《大正藏》第13册,第685页上。
[53]《思维要略法》,《大正藏》第15册,第300页下。
[54]现存此经的梵本,有在尼泊尔发现的大本和日本保存的各种传写模刻的小本两类。1864年,比尔始据本经奘译本译成英文。1884年,马克斯·穆勒同日本学者南条文雄校订本经大小两类梵本,1894年,穆勒重将本经译成英文并编入其著名的《东方圣书》之中。
[55]《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正藏》第8册,第847页下。
[56]关于昙无谶来姑臧时间,史料记载不一。此说根据协助昙无谶译经的道朗所记。见:[北凉]道朗《涅槃经序》,《大正藏》第55册,第59页下。
[57][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第11页中。
[58][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519页中。
[59][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六,大正藏》第49册,第62页上、64页中。
[60]《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4页下。
[61]《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5页上。
[62]《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5页下~176页上。
[63]《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6页中—下。
[64]《悲华经》卷二,《大正藏》第3册,第179页中。
[65]《悲华经》卷三,《大正藏》第3册,第185页下~186页上。
[66]根据唐代静泰的《众经目录》卷三,《大正藏》第55册,第197页中—下。
[67]隋代《法经》记载:“《光世音大势至受决经》一卷(晋世竺法护译)、《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一卷(宋世沙门昙无竭于扬州译),右二经同本异译。”见《众经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117页下。唐代智升记载昙无竭译此经时说:“《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一卷(一名《观世音受决经》,第三出,与西晋法护、道真出者同本。见王宗僧李廓《法上》等录及《高僧传》)。”见《开元释教录》卷五,《大正藏》第55册,第530页中。
[68]《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12册,第355页下。
[69]《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12册,第356页上。
[70]《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12册,第356页下。
[71]《观世音授记经》,《大正藏》第12册,第357页上—中。
[72]《中阴经》卷下,《大正藏》第12册,第1070页上。
[73]《佛说佛名经》卷二,《大正藏》第14册,第124页中。
[74]《佛说华手经》卷三,《大正藏》第16册,第146页下。
[75]《佛说佛名经》,《大正藏》第14册,第185页下。
[76]《佛说佛名经》卷三,《大正藏》第16册,第147页下。
[77]《佛说佛名经》卷九,《大正藏》第14册,第163页上。
[78]《宝云经》卷一,《大正藏》第16册,第209页上;《大乘宝云经》卷一,《大正藏》第16册,第241页中。
[79]《大方等如来藏经》,《大正藏》第16册,第457页上。
[80]《佛说造塔功德经》,《大正藏》第16册,第801页上—中。
[81]全称《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收于《大正藏》第16册,第714页下~718页上。
[82]《佛说解节经》,《大正藏》第16册,第711页下。
[83]《佛说解节经》,《大正藏》第16册,第714页下。
[84]《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大正藏》第16册,第714页下。
[85]《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大正藏》第16册,第715页上—中。
[86]《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大正藏》第16册,第716页中—下
[87]黄心川:《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1~42页。
[88]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卷四将此经列入失译录之中,但到了隋代的费长房根据《法上录》认为其为东晋竺难提所译。分别见:[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大正藏》第55册,第22页中;[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七,《大正藏》第49册,第72页上。此后各经录沿袭费长房的说法,如[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卷十二,《大正藏》第55册,第89页、第601页上。
[89]根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第13页中。
[90][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95页下。
[91][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100页下;[隋]翻经沙门及学士等合撰:《众经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152页中
[92]《七佛八菩萨所说大陀罗尼神咒经》卷一,《大正藏》第21册,第542页上。
[9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112页中。
[94][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三,《大正藏》第55册,第624页中。
[95]吕建福:《中国密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8月,第140~141页。
[96]《观世音说灭罪得愿陀罗尼》,《陀罗尼杂集》卷六,《大正藏》第21册,第612页下。
[97]《观世音说除一切眼痛陀罗尼》,《陀罗尼杂集》卷六,《大正藏》第21册,第613页上。
[98]《观世音说咒涧底土吹之令毒气不行陀罗尼》,《陀罗尼杂集》卷六,《大正藏》第21册,第614页中。
[99]《观世音说咒药服得一闻持陀罗尼》,《陀罗尼杂集》卷六,《大正藏》第21册,第614页下。
[100]《观世音说咒五种色昌蒲服得闻持不忘陀罗尼》,《陀罗尼杂集》卷六,《大正藏》第21册,第614页下~615页上。
[101]任继愈:《〈中国居士佛教史〉序言》,《中国居士佛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2页。
[102]这里应该指竺法护的译本,即《光世音经》,因为其时当在罗什译出新的译本《观世音经》之前。
[103]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大正藏》第50册,第371页上。
[104] [隋]灌顶:《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正藏》第50册,第191页中。《佛祖统纪》卷六亦载:“七岁喜往伽蓝,蒙僧口授《普门品》,一遍成诵。”(《大正藏》第49册,第181页上)
[105]其中《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被称为“天台三大部”。如《天台三大部补注》序云:“玄、文、止观共三十卷,时人谓之三大部。”(见《卍续藏经》第43册,第871页上);《法华文句记》卷十云:“非玄文无以导,非止观无以达,非此疏无以持。”(见《大正藏》第34册,第359页下)
[106]“天台五小部”中的《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都是对《观音经》即《普门品》的阐释。
试论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
谢瑞 逸舟
观音是东方世界最流行的一个信仰对象,历史上在东方流传的各种宗教崇拜对象没有一个像观音这样具有持久而深厚的民众基础。在佛教体系内,观音的知名度和普及度也是所有佛菩萨崇拜体系中最流行的一种,自古以来崇拜观音的信众最多,尤其是在中国的汉族地区,观音信仰的流传更为广泛,“户户观世音”这样的俗语就反映了这种流传的广泛程度。不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人们对观音信仰在中国盛行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可是,对这种奇特的宗教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考察,却一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学术领域。人们对观音信仰往往有一种误解,似乎“称名救难”就是全部观音信仰体系的唯一内容。这种误解已经有相当长的时期了。其实,观音信仰这种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宗教文化现象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体系之庞大,包纳之广博,不亚于任何一种宗教文化现象。它既集中体现了大乘的基本精神,又自成一种相对完整的宗教文化体系。这种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形态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宗教现象的特点。分析研究这些特点,对于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的观音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学术界在观音研究方面偶见一些成果问世,但是从观音文化的体系,观音信仰的形态,观音法门的结构,观音思想组成、架构与特征以及观音信仰的中国化表现、中国观音信仰传播史的基本特征等角度进行研究者极少。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方面正是体现中国观音文化特征的主要因素所在。在这里,我们试从这些方面入手,对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作一系统的阐述。
一、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类型
中国观音文化是由三大类型组成的,即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藏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和汉族地区民间的观音信仰。这三大信仰类型也可以叫三大信仰体系,其中汉传佛教观音信仰自魏晋时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南北朝时期的盛行,隋唐时期的普及和元明时期的变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僧俗佛教信仰者尤其是观音崇拜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下,继承印度佛教有关观音经典的说教,并根据大乘佛教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大乘菩萨信仰的基本教义,对印度佛教观音类原典进行进一步的发挥演绎,从而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佛教信仰体系。
藏传佛教观音信仰自前弘期便传入西藏,中间经过一段沉寂后,在后弘期始得源源不断地从印度传入藏地。由于这时印度逐渐兴起了密教,而原来的显教观音信仰也在佛教密教化的过程中,逐渐地改造演化成密教的观音信仰体系。传入西藏的观音信仰基本上就是印度密教的观音信仰。这种信仰形式又经西藏佛教信徒的进一步发挥,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体系,并在整个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以至认为观音菩萨就是整个藏族人民的祖先,历世达赖则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布达拉宫也被看做是观音菩萨所居的宫殿,观音的六字真言更是至高无上,几乎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象征,有关观音类经咒、仪轨、法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形式的造像极为丰富。与汉传佛教观音信仰不同的是,藏传佛教观音信仰以各种真言、印契和与之相关的观想等宗教义理与规范为主体,所以,尽管在观音信仰的基本理论上,与汉传佛教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由于主体表现形式的不同,以至在造像、仪轨及具体修持方法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