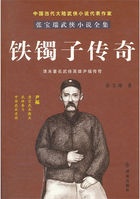许燕影
子虚像他的名字虚虚实实地婉若一场飘渺的梦,七个月后渐淡渐远了。
那是凤凰花开得最热烈的五月,在一个大型晚宴上,子虚从主桌举着酒杯绕过来和锦年打招呼,愣了一下,锦年遂想起多年前还是小小办事员的自己曾因业务关系和他打过不多的几次交道。事隔多年,呵呵,眼前这个人名片上已赫然印着某集团公司总裁了。
很自然他们就开始了进一步的交往。
公众场合子虚话不多,很内敛,城府深得你永远不知道他的喜乐。但他却是不多的爱用香水的男人,身上隐约的木质香感觉得出是香奈尔,这气息让锦年沉迷。还有他干净的全棉衬衫,靠近时能闻到阳光晒过的味道。在一起的时候,锦年像任性的孩子浪漫、随性,总是用手指轻舒他微锁的眉,有时候也逗得他哈哈大笑。当他终于轻拍锦年的头,很自然的以“乖”字代替锦年的称谓时,锦年成了子虚怀里温顺的一只小猫儿。
转眼间已是凉意习习的深秋了。
锦年最爱和他在海边散步,微雨的日子坐他的车兜风,听他天南海北地侃,原来他并非她所想的不爱说话,天文、地理、中医、命相无所不知,锦年几乎把他当成了身边的活字典崇拜得不行。有时候锦年伸出手让他看爱情线,他会说:你逃不过这次的情劫。偶尔他也会几语带过他曾无疾而终的很短暂的二次爱情。接着他会很深沉地来一句:我知道我也逃不过这次情劫,认真得像假的一样。锦年这样的时候就在车上和他闹,揉乱他的头发,冷不丁吻他的脸,告诉他她喜欢他。而子虚从不说爱她,说过几次“你很漂亮”,说最多的是“带你出来玩像带孩子一样”。但当他弯下一米八几的个头屈身为她系鞋带、为她拿拖鞋,餐桌上殷勤为她夹菜、为她剔鱼刺时,锦年知道他是喜欢她的。每一次细微的体贴总是让锦年觉得,除了妈妈外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
这个冬天异常的冷,锦年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依恋他了。
睁眼闭眼都在想他,她渴望缠绵相守,爱让她觉出从未有过的寂寞,尤其夜深人静时。她需要他问寒问暖的电话,其实他们一直离多聚少。子虚总是天南海北地飞,他的业务遍及多个省市,照他的话说,很累很忙。十天半月见不到一面是常事,电话也极少。像是默契,锦年从不主动电话,但心里的抱怨却一天天一点点积储,在他生日那天终于爆发。那天午夜接到他醉意醺醺的电话,说是刚陪完客商。锦年第一次发飙,抱怨重重。她认为最重要的日子应该和最喜欢的人一起度过。她觉得子虚不在意她。子虚不停地解释,完了很无奈地告诉她:“我不会花言巧语,但我却在用心爱你。”锦年哭了:“我只听得见你的声音,我看不到你的心啊。”
锦年的生日在春天,春天迟迟不来,锦年等不到和喜欢的人一起庆祝了。最冷的冬末,做了最快的决定。订票、收拾行囊,从没有过的决然。厚厚的毛衣、长长的围巾,还有一本安妮宝贝的《清醒纪》。锦年大部分时间泡在“我在丽江等你”,白天躺在二楼书吧的榻榻米看湛蓝的天空。晚上会在音乐火塘听这首同名曲,偶尔喝酒,偶尔也会哼着“我在丽江等你”的旋律在青石板的小街徜徉,“穿过那条街能否遇见你/想想该有多么惊喜……”这个冬天,锦年发现,任何一个地方的阳光都暖过自己居住的海岛。
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爱有爱的原因,不爱有不爱的理由。锦年没有刻意去遗忘。春天终于来时,锦年换了手机,复制电话本时顿了一下,随即把那个用“风”字替代的他的名字轻轻点了删除。爱情伤逝了,也许七个月的爱情原本就不是爱情。花开得越纵情凋零得就越快,五月火烈火烈的凤凰花啊,事后才知道它最初的寓意就是别离和思念。
安妮宝贝说:某天如果我觉得不再爱你,我就不会再感觉寂寞。
如果没有很爱的人,一个人的生日其实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