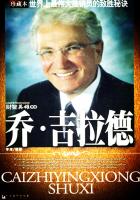搬家
社里的人们欢庆收获了头一批苹果后,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南赛、池底、刘家底、灰沟、东峪沟、古罗等自然村办的小社,与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并成了一个社。李顺达仍然担任社长,申纪兰是副社长,张俊虎接任了会计,为了让李顺达集中精力领导好生产合作社,经支部大会讨论,重新选举了支部委员会,由池底的马河则担任支书,南赛的赵相奇为副支书。
几个社合并以后,有二百八十多户人家,分散住在四十四个自然山庄,沙底栈接近于中心位置,为了便于领导生产,社员和干部们都希望李顺达搬一处家,从比较偏远的三岔口,搬到沙底栈。但是,谁也不敢说这句话。大家都知道,李顺达从河南逃荒来到西沟时,挑了一担破行李,现在,他已经整修了那三孔破窑洞,还盖起上下六间新楼房,在院里搭起棚子,凿了井。窑顶上种了杨树、柿树,在门口和院里种了苹果树、梨树。这些,都是他多年的劳动换来的。
搬到沙底栈住在哪里?社干部犯了愁:寻不下个合适的地方给上老李住。
后来有人找到山路边上的三孔小土窑,在里面住过的两户人家都相继出了麻烦,于是说这窑洞的风水不好,谁也不肯在那里住。主人有意要出售,也没人敢要。
过罢老年,正月初三社员开始做活了,李顺达也看出了大家的心事,他向干部们说:“我是不是还应该搬一次家?搬到沙底栈,开会、研究工作,或者社员有个什么事情找我,都要方便些。”干部们心里都很高兴,他们相互看着,又看着顺达,顺达呵呵地笑着说:“为甚都不说话?”申纪兰心直口快,她说:“大家早就有这个心思,可是沙底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叫你搬来在哪里住?”李顺达早已经盘算过这个问题,他说:“我看路边那三孔土窑洞就能凑合,还有个旧马棚子,收拾收拾,比我刚从河南逃荒来到西沟时强多了。”可是这三孔窑洞实在太破旧,连个院墙也没有,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顺达又认真地说:“咱们如今是新农民,在哪里不一样?”“这话说得好。咱们现在不管住在甚地方都是在天上生活哩!”赵相奇很感慨。沉思了一阵,他又难为地说:“老李你的那些房屋树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李顺达好像也早想好了,他说:“那还用处理?反正都在咱们社里,谁想搬到那里住,让谁住上都行。院里院外的果木树一道给了他。”“那你到了沙底栈什么也没有还行?”李顺达轻松地说:“只要咱们不偷懒,有两只手还怕没有家当?
这一所院子几棵树,能把一个人的心牵挂住么?咱还得往前走,好日子还在前面哩。”顺达的话,使大家感到眼前开阔了许多。
第二天是正月初四,纪兰、相奇、俊虎、河则等人把路边那三孔上土窑收拾干净,糊上窗纸,生着火。正月初六便一块去找李顺达。
李顺达望着他们说:“你们说,我哪天搬家?”纪兰说:“我们把那三孔土窑收拾了一下,火也生着了,窑里还暖和。”李顺达看出了他们的心事,说:“是不是催我现在搬家?”马河则是个爽快人,他说:“老李,现在搬最好,你看有没有困难?”赵相奇不紧不慢地说:“现在是一大家子,叫老李准备上两天。”“没有什么准备的!现在摊子大了,一担子担不了,咱就多跑几趟。”李顺达说着从炕上跳到地上,说:“你们今天要没有很要紧的事,就帮我搬家。”李顺达是个痛快人,说搬就搬,大家动手,担的担,抬的抬,比起从河南逃荒到西沟气派多了。李顺达从三岔口搬到了沙底栈,离开了经过多年修整已经拥有十二间住房的四合小院,搬到了破破烂烂的三孔土窑里,没有院子,一出屋门就是个野场子。晚上,不时有狼守在窑门口,狐狸刨着鸡窝响;白天,一阵一阵的山风撞开门,沙土树叶在窑里转圈子。
桂兰免不了说几句埋怨的话,顺达总是嘿嘿一笑,对她说:“日本鬼子扫荡那阵,妇女娃们躲在山上石窟里,没有一个嫌赖,也没有一个怕狼。现在有了暖窑热炕,你倒有了意见不成?不会吧!”顺达这样一说,桂兰也就不开口了。他们一家人闲着时,就收拾这个新住处,打土坯垒院墙,在院里挖坑栽树,把一个简陋的马棚子四堵墙垒起来,也成了住人的房屋。房子都在人收拾哩,没有过多久,这儿就变了样。随后他们挖井、扩建,1962年还建起了两层楼,于是这年出身的儿子,起名叫“建平”。这个小院后来被多次摄入镜头,与这位中国劳模一道扬名世界。
公私之间
搬到沙底栈这个中心地带,社员们找李顺达确实方便多了。这天,李顺达收工回家,有两个社员站在街门口等他,两个人脸红脖子粗,一个脸朝南,一个脸朝北,看样子还憋着一肚子气。见了李顺达就抢着告状,一个说:“老李,你给评个理!入了社牲口合伙用,我的牲口和他家的牲口合耕地,他舍不得使自己的牲口,把拉套放得长长的,一鞭也舍不得打。把我的牲口挽的拉套紧绷绷的,一鞭接一鞭打,你去瞧,看看把我的牲口打成甚样子了?要他赔!”另一个掏出自己的烟袋,不紧不慢地说:“谁的牲口谁心疼,你的牲口不想合耕,干脆拉回家去,拴在炕头!”“拉回就拉回,拴到哪里由自己!这一回的账还得算清楚,我的牲口,不能白吃亏。”李顺达听他们各说各的理,心里在捉摸:刚解放那阵子,政府鼓励发家致富,可现在倡导“公有”,这大概也是发展的需要吧。李顺达耐心地给他们做了一番说服工作,妥善地处理了这场纠纷,但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前些天在县里开会,领导也说到如今的分配制度不够合理。还给他布置了任务,要琢磨些办法改一改。
晚上,他一直在想着这些事。当时合作社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人、物两重分红,人参加劳动挣工分,有土地和牲口的,也折合成工分,参与分红。虽然土地分红比例年年在降低,由1952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降到了1953年百分之三十。但是一些贫雇农出身的人还是有意见。他联想起社里一位老中农编的那段顺口溜:“我有土地老牲口作价归社上犍牛,秋后粮食不发愁。隔一天,动一天,也是余粮户。”正是这个靠土地分红和牲口挣工分的老中农,一年只做了七十个劳动日,却分到了粮食二千五百斤。可是有的贫农、下中农,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却远比不上中农靠土地挣到的分红多,他比成天干活但没土地和牲口的社员多了许多。
那天在县上有位领导讲以前认为生产资料也是财富,现在改朝换代了,旧的做法也要改一改了。一些贫雇农认为现如今是穷人的天下,土地分红的政策不该继续保留,也应改变一下。如果还是采用“动弹不动弹,土地分一半,死土地剥削活劳力”的做法,怎么体现穷人当家做主的社会呢?
看来这种分配方法已经到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顺达在炕上死劲翻了一个身。他又想到住在刘家底村的玻璃老哥,他老家也是河南林县。旧社会,他爹给地主扛长工,养不活一家人,才把他卖到了山西。在旧社会,连吃糠咽菜的苦生活也难维持。断顿以后,免不了接受穷人的帮助,这家一把菜,那家一碗糠,搭救他支起熬汤的锅。
解放后翻了身,他日子过得红火了,前些年也实现了发家致富的美梦。他买上大牲口,套上车,还开起了油坊。这人的长处是手勤腿快,脑子也精灵,所以人们都称他“玻璃脑筋”。
玻璃老哥听说要办社,先买了骡子,后又买下马,要跟合作社比高低,比了两年觉得不合算,又入了社。可他在社里也不肯好好劳动,是靠牲口挣工分吃饭哩。村里地少的或没有地的人家当然不满意。县委李书记讲,这是新式的剥削。他说共产党领导群众干革命,就是要把这些不合理的事情改掉。以前的老规矩不行了,应该重新制定。他让顺达发动全体社员讨论,如果大多数社员同意,可以立即取消土地分红,牲口作价入社。顺达一听,着实又惊又喜:“原来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自己的土地、自家的牲口,统统归社里也省心省事了。但这么做合适吗?”他和几个干部商量,大家都说:这个办法不赖!革命么就得不停地往前闯,不能像小娃娃扭秧歌,老在原地圪扭,虽说也在走,太慢了!
这天正巧顺达在乱石河滩上碰见玻璃老哥,玻璃穿戴得干干净净,肩膀上搭着个麻袋,看样子是到什么地方赶庙会。顺达和他打招呼说:“老哥,你在忙什么呀?”“我的那几头牲口,都叫社员牵着上地里劳动去了,不能让它们歇着不做活。社长,咱县最近有几个庙会,我想再买一头骡子,也交给咱们社里使,你看行不行?”不等顺达回答,他又说:“咱们办社的第一年,还得人拉犁,现在虽说不用人拉犁了,可是牲口还不多呀。”“老哥,在过去,你一听说要办社,就赶快把好骡子卖了。现在,为甚又专门买上牲口给社里使?来,咱俩谈一谈。”李顺达拉了玻璃一把,两人并排着蹲在路边石头上。玻璃难为情地笑了笑,说:“过去俺的思想不对,不了解党的政策。”“现在呢?”玻璃抓了抓后脑勺,眨巴着眼睛瞧着顺达。他想:一些社员对俺有意见,是不是顺达听了他们的话?他说:“社长,别看俺出工不多,俺赚的工分还真不少!俺有几头大牲口,社里使一天,就顶俺好几天做活哩。”李顺达说:“你吃了蜂蜜觉着甜,难怪还想买骡子。”玻璃一听站起来,瞪着眼说:“怎么,买骡子给社里使也不对?”李顺达拉拉玻璃,让他重新蹲下来,说:“你是为了社里发展生产买牲口?不见得吧!我看是为了让牲口挣工分,自己坐着不动弹,吃轻巧饭哩。”不等顺达说完,玻璃又睁大眼睛争辩说:“我也是为了社里发展生产,社里用我的牲口,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不好吗?”“县上的领导布置要让全体社员讨论:取消土地分红,牲口作价入社。”玻璃一下子愣住了:“这……这,社员中有土地和牲口的人少,他们当然同意,可是,这、这也太过分了吧!”顺达说:“如果社员大会通过了,你还买不买骡子?”上社里的马在县里配上了前苏联种马,生下了小马驹“那、那……”玻璃结巴了一阵,费力地说:“那就叫社里买吧,我还买它做甚?”在崖上地里做活的几个社员,一直注意着李顺达与玻璃的谈话,他们听说要取消土地分红和牲口作价入社,都高兴地扔下手里的活计,一起朝河滩跑来。
有个叫安根的社员说:“顺达,这你也知道,俺爹娘给俺起名叫安根,就是希望俺能有个地方安根。可是在旧社会东飘西荡半辈子,到哪儿也没个立脚的地方,解放后才算能安根了。俺常想,这个根要安牢靠,就得取消畜力记工,土地分红。这些也是剥削,影响咱穷人吃苦耐劳安根呢。”玻璃又忍不住跳起来,冲着安根老汉说:“俺剥削你来?”“你叫俺把话说完!”安根激动了,推开玻璃说:“旧社会地主收租子是剥削,现在土地分红为甚就不是剥削?玻璃,拿咱们俩做个对比,我赶上你的两条牲口耕地,你到外村去逛游,我做一天活得十分工,你甚也不干就得三四十分工,这是不是剥削?”“好好,我把牲口都卖了,从今以后不剥削你,还不行?要不行,俺就退社。”玻璃老哥很委屈也很生气,他打量着李顺达,希望他说几句使他宽慰的话。李顺达的心里也很乱,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县里领导说要大胆地打破旧框框条条,建立新规章,以前所有的旧规矩都可以取消了重立,这多好呀!有人想不通也是自然的,他收入减少了么!
李顺达说:“老哥,在旧社会,你也是无处安根的一棵黄连树,从河南林县到山西平顺,换了两个主儿还是穷得吃不上饭。你在饿肚子的时候,也恨透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今天是毛主席、共产党让咱们翻了身,咱们才富余起来。现在共产党又号召大家走集体化的道路,咱们跟着走,不会差!”玻璃头一热,觉得这世道简直乱了套。但他又能怎么样呢?只是想以后不用心气那么高去闹腾了,没有用!便丧气地闷坐在石头上。
社员们见他被李顺达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耷拉着头用脚踢石子。
经过社员群众民主讨论,绝大多数人要求取消土地分红,牲口作价入社。有地有牲口的心里不大痛快,可也不敢举拳头反对。
接下来,社员共同关心的问题是牲口作价。有牲口的社员中间,有担心作价低了自己吃亏,没有牲口的人担心牲口作价太高,集体吃亏。有人提出要按市场价格,也有人提出要卖价高,还有的提出低于市场价格。
李顺达发言了:“咱们不是卖牲口哩,是给社里投资,为的是发展生产么!”有人说:“老李,你的牲口多,你带个头。”可是,玻璃老哥在心里嘀咕:可不敢叫老李带这个头,他多会儿也是叫自己吃亏,咱跟上他沾不了光。
李顺达站起来了:“好,我开个头。按市场价格,我没意见。”一听这话,玻璃老哥心里踏实了点。他思忖:看样子,老李同意市场价格,这还不错。
老李用眼睛扫视着在座的社员,继续说:“不过,大家都清楚这一点,牲口这东西不比别的,它不能用秤称,也不能用斗量,是用眼看哩,所以,同一条牲口牵到市场上,一高一低也相差几十块、甚至百把块。咱不是做牲口买卖,不能斤斤计较,钱多钱少是小事情,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大事情。”李顺达无意间学着领导讲话的语气,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
社员们静静地听着,有些人虽然想不通,但想想李顺达也是个有牲口的主儿,便不好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