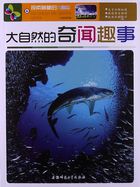亦轩说得没错,如果她的才华为众人所知,一定会成为众多男子争相爱慕的对象,如果自己不好好珍惜,一定会失去她。不,自己其实已经失去她了!她先前一定是为了能够逃出去,才一直藏匿自己的怨恨,而被抓回来之后,觉得心思已经暴露,再也没有必要掩饰,所以看向自己的眼神里,只有憎恨,愤怒,嘲讽,不服。
是的,自己如同仲勋所说,已经开始后悔了,只是,恐怕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心,撕裂一般痛苦不已,为她,也为自己!尉迟慕白,你何其有幸,能够娶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女子,你又何其不幸,弃之敝屣之后,才逐渐发现她的好,才来后悔,却又无以为悔!
她嫁入王府七个多月了,可从她嫁入的第一天起,自己就没有让她过过一天好日子,一再地凌辱,仇视,还亲手打断了她的胳膊和腿,甚至还被她得知“自己”要利用她怀孕生子,不着痕迹地灭了她。而她遇到那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提出的要求,却让自己几乎暗自垂泪:自己营造的地狱般的氛围,让她的梦想只不过是正常地有尊严地活着!可以想见,自己在她的心目当中,是如何低劣、丑陋、恐怖,让她除了活着,不再折磨她,对自己再没有一丝幻想。
“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是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她的心里印上了无法磨灭的恶劣印象!是自己完全以对待仇人,对待敌人的心态来对待她,而阖府侍卫更是一心帮着自己出气,一同虐待她!天哪,尉迟慕白,你都干了些什么?!
一直为人坦荡磊落的自己,即使向来与她父亲政见不合,阵营不同,却也不曾用过什么卑鄙手段,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已。而在发生了她大姐陷害诬蔑自己的事情自己深受其害之后,却一改往日为人处事的作风,尤其对她家的所有人仇恨不已,以至于迁怒于她,造成了今日这样难以挽回的局面。
尉迟慕白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内疚,越想越悔痛,心如刀割,黯然神伤,后悔莫及。离开此地,似乎成了现在唯一的选择。
还未迈出第一步,就听到有人朝这边走过来,是秋亦轩和祁伯。
几乎同一时间,司空凝心似乎心有灵犀般,开始唱起歌来。
尉迟慕白一惊:他们有约?!要干什么?不行,自己要留下来看个究竟。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自从我披上那白大褂,就深感这份责任重大,处方纸上把无情的病魔驱除,手术台上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这就是医生的光荣使命!
是谁,总是在用行动去展示生命的珍贵!
是谁,总是在用真情去谱写一首动人的生命乐曲!
是谁,总是在争分夺秒挽救危难之际,用汗水汇集成那激情的旋律!
又是谁
总是在工作之余挑灯夜读,甘愿为老百姓的健康,做忠诚的守护神!
又是谁
即使遭受了多少埋怨与误解,风风雨雨总是用微笑去面对!
这就是医生的崇高使命!
没有假日的休息,没有昼夜的分明,甚至是就餐也常常时断时续,但这并非我内心真正的苦闷,病人的痛苦才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
不会有怨言!
不会有悔变!
无论洒下多少血汗,期盼的不是金钱的收获,病人的康复才是我心中最大的欢乐!
这就是医生的神圣使命!
这是司空凝心进入首都医科大学后,同学们时常挂在嘴里,用来激励自己的歌,也是胸外科医生工作的真实写照。事隔多年之后的今日,再次出手救人,令司空凝心回忆起那青春飞扬,热血澎湃,激情四射的学生时代,不由轻轻哼唱出声。虽是轻哼,在这寂静的夜,却清晰地传向四面八方。
秋亦轩和祁伯踏着歌声而来,那清唱的小调,虽过于直白,言辞间无甚韵味,却将歌中所要表达的“医生”的使命,和其中的酸甜苦辣,阐述得详尽得当,一听了然。只是,“医生”?唱的不是大夫的事么?!难道是扶遥国对大夫的称呼?秋亦轩和祁伯互望了一眼:她真的是期待已久的,能够彻底治愈顽疾的大夫么?!
秋亦轩有伤病在身,走得很慢,司空凝心哼唱完第二遍,秋亦轩和祁伯才走到院中屋前。房门紧闭,看不到人,秋亦轩依然不顾伤病,躬身行礼:“不才秋亦轩有事特来请教,不知司空方便否?”
司空凝心也不开门,只冷冷应道:“请教不敢当,有事儿就说吧。”
秋亦轩闻言没有再出声,祁伯却感受到了他无言的失落,哈哈一笑:“丫头啊,老夫一把老骨头了,来把椅子吧。”轩儿因着才华,因着顽疾,一向被人捧着,宠着,何时受到过这样的冷遇!这个丫头倒好,明知他的病,却丝毫不假以辞色,也不怕他听了又犯病。更令自己担心的是,轩儿对这丫头似乎动了心思,再不是第一次见面后的无动于衷。
祁伯开了口,司空凝心再也不能装作不知道他来了,只好拎着两把椅子走出门来:“二位请坐。”然后站在二人面前,明显一副不欲久留的意思。
此举也让躲在暗处的尉迟慕白松了口气:不是先前约好的,她也还知道深浅,没有深更半夜地将男子让进房中。
两把椅子,三个人:一个今日犯病差点丧命,一个是大腹便便的孕妇,一个总是自称老夫,却又看不出年纪有多老的“老人”。
三人谁也不肯坐,你让我,我让你——
“司空,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你坐,我年轻力壮的,站着没关系。”
“祁伯,我年纪轻轻的,怎能在您老面前落座呢!孕妇就应该多活动,何况我刚才在房中已经坐了挺长时间了。再说您老远来是客,哪有客人罚站,主人坐着的道理。您坐,您坐。”
“你们俩一个是病号,一个是孕妇,老夫年纪虽大,身体却比你们都好。你们俩都听老夫的,统统坐好。”
“秋公子,你今天犯了病,又受了伤,还是你坐吧。就算你想再挨一戳,我也不敢了。”
司空凝心巴不得就这样一直推来让去,再过一会儿,就好说累了要休息了。他们俩这么急巴巴地赶来,还不是为了秋亦轩的病,当自己不明白么。
果然,祁伯沉不住气了:“丫头啊,我们可不是来找你玩坐座儿的,你想必也能猜到,老夫是想请你出手,彻底治好已经折磨了轩儿十几年的顽疾。”
“祁伯您太抬举我了,我哪儿会什么医术啊,不过是胡乱扎了秋公子一下,结果还扎出好多血来了,吓得我赶紧逃了。我这正心虚着呢,就怕是来找我算帐的,没看我门都不敢请你们进。”我虽然会医术,可此医术非彼医术也,我的医术在这儿没有条件能够施展开来,也无法和你们解释清楚,还是否认最好。
“老夫虽然当时不在场,没有亲眼看到丫头你施救,却也能从轩儿的伤势,判断得出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稍有延误,便万劫不复。你从来不知道轩儿的病症,却这么快就诊断出来,而且及时进行了完美的救治,说明你对这种病很在行。”祁伯意味深长地看了司空凝心一眼,“老夫不会去探究你是从何处习得的医术,也绝对不会偷艺,只要你肯出手彻底治好轩儿的顽疾,老夫便从此了无牵挂,可以任你差遣。”
“我真的不会什么医术啊,祁伯您一定是弄错了,”要来的还是来了,为了不露馅,只有一装到底,“秋公子当时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什么掐住了他的喉咙似的,无法呼吸,所以我就顺着他的喉咙往下摸。结果摸到胸口就发现里面软软的,我摸一下,就波动一下,就象水一样,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就找侍卫要了管子戳了一下。谁知道里面全是血,吓得我赶紧逃了。”
司空凝心自顾自说得起劲,另两个人却不听她胡诌,只是双双盯着她看,看她究竟要演戏演到什么时候。
司空凝心可没有一点儿心虚,眨巴着那双澄澈的眼睛,回望二人:“你们真的不怪我么?”
秋亦轩叹了口气:“祁伯,我们走吧。轩儿在您的庇佑下,能多活了这么些年,已经知足了。那些医生的光荣、崇高、神圣的使命,只不过是唱来玩儿的,当不得真的。”
司空凝心没有吱声,自己岂能被这么肤浅的激将法给带进笼子里!而且那秋亦轩一看就是个腹黑之人,心里鬼主意定然多着呢!就算你们俩都曾经帮过我,那也不过是受那畜牲所托,我可不欠你们什么!
那祁伯竟似能看透人心似的,人虽然开始跟着秋亦轩往院外走,口中却说道:“你的伤,老夫能够轻而易举地治好,可是那疤痕,却要天下伤药至尊‘凝脂’方能不留一丝痕迹。如今洪武国仅存一瓶,全给你用了,当初我可是连轩儿都没舍得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