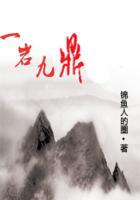“那是他们蠢——这宝贝玉瓶有灵性——它们发了脾气才沉入水底的。”郑通达说着皮笑肉不笑,竟勒住马头不走了。
潘六也赶忙勒马,呲呲牙可心里揣摩大少爷的话,总觉他故弄玄虚,“大少爷,这会儿也没外人,小的请您不吝赐教!”
“你小子别打老子的鬼主意!”
“哪敢啊——求您了——小的长了见识——也好对付那帮来进货的玉商啊!”
“嗯——”郑通达想了想,示意潘六附耳过来,“这趟带咸盐了吗?”
潘六不解,“按您吩咐,整整三大麻袋咸盐,可这跟玉瓶水上漂何干?”
“笨蛋!我爹的玉瓶口小肚子大,水里加上大把的盐,浮力倍增,再加上木制底座,能浮不起来嘛!”
“原来如此——”潘六猛拍脑门,“我上次没放盐,还把玉瓶的木座给卸了……大少爷,这毕竟是弄虚作假,据说真玉瓶可是一直能浮在水面啊!”潘六竟担心起来。
“他妈的——真玉瓶价值连城——可谁见过?”
“这倒也是——无假不获利。”
“所以然,我爹的玉瓶一直销往外地,咱润宝城内从来就没货!”郑通达得意起来。
“听说马一坤也做玉瓶,偷偷把玉瓶销往外省……”
“马家贼得很,总想抢生意……老子教了你小子这么多——你如何报答?”
“小的领情,把您老在‘怡红院’的账结了……”
“可这趟送货去会盟县,季掌柜老奸巨猾,你我如何能当着人家的面造假?”
“猪脑子——我拉他先去喝酒——你们偷偷往水盆里放盐……”
“大少爷真英明——”潘六竖起大拇指。
“你小子又学了一招——”
“回头再把您老在几家赌场的账也结清。”
“哈哈哈哈——算你小子鬼机灵。”郑通达破天荒夸了潘六一句。
俩人一阵大笑,郑通达这才抬眼朝前望去,众家丁跟着马车已离开很远,他赶忙策马追赶,潘六随后紧随。
这会儿,风停雨住,半空中突然雾气蒸腾,右岸边的水草、树林顷刻已被迷雾笼罩,可天际边却有一抹彩虹飞挂,郑通达和潘六策马刚刚追上了队尾,谁料,潘六此刻骤然惊叫了一声:大少爷,那,那那是什么?
郑通达闻声一惊,赶紧顺着潘六手中马鞭望去,只见前方不远处,河中间雾气奔腾,几大团迷雾缓缓聚集一处,片刻之间一动不动了,浓雾竟隐约好似呈现出一张硕大笑脸,似笑非笑的脸型与远处的那抹彩虹交相呼应,霎时显得很是诡异,而这种奇异的景象,顿时令众家丁们瞠目结舌。
“别他妈的一惊一乍的,不过是海市蜃楼!”郑通达顿觉浑身毛骨悚然,但仗着胆子吼了一声。
“不是吧!这笑脸小的真眼熟。对了!是在咱府的祠堂里见过,就是祠堂那张王一刀的大画像,一模一样啊……大少爷,您再仔细看看。”闻听此言,郑通达心里连连惊叫:乖乖!王一刀早年死的不明不白,这是要显灵啊!
众家丁盯着半空迷雾,个个双腿瘫软一动不动。这档口,小道旁草丛内竟有几个人影晃动,紧接着一声振聋发聩的怒吼: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郑通达等人正聚精会神望着半空,众人却听见背后突如其来的一声吼,个个吓得一激灵,潘六妈呀一声从马背上跌落,顿时裤裆里湿乎乎一片。郑通达也吓得跌落马背,可他还是连滚带爬站了起来,神色慌张打量四周动静。这时,已有一群手持刀枪的汉子聚拢过来,潘富贵大叫一声:有劫匪,赶紧抄家伙!他头一个拔出手枪,刚想瞄准土匪开火,谁想,一声清脆的枪响过后,潘富贵已倒地咽了气。匪首膀大腰圆,泛着黄光的方脸上满面杀气,他三两步上前,扬起手中冒着青烟的手枪一挥,伸出一只脚重重踩在了那具尸首身上。
俩个家丁扑通一声跪地,浑身体如筛糠,潘六掉头飞奔逃走,还边跑边大喊:大少爷——赶紧逃命啊!郑通达总算定住神色,拔出腰间手枪麻利地上了膛,可一个矮个土匪眼疾手快,他手起一记飞刀,飞刀正中郑通达的手腕,手枪哐当落地同时,一股鲜血从手腕上汩汩冒出。郑通达一声惨叫,扭头就跑,几个土匪随后拔脚想追,匪首却大声制止了他们。
弟兄们——劫货要紧!匪首命令众手下。随即,众手下围住马车,几个土匪喝令俩车夫赶车前行,俩车夫乖乖听命,摇晃起马鞭赶车。匪首看着马车前行,转身带了几名手下围住7、8个跪地家丁,一个家丁连声求饶,可匪首抬手一枪,那名家丁当即毙命,不由分说,众土匪顷刻之间纷纷挥刀一阵阵乱砍,顿时家丁们连声惨叫,一个个直挺挺倒地身亡……
河边小道静悄悄的,唯有河水哗哗流淌。
方才,一阵砍杀后,泥泞道上缓缓淌过殷红血水,横七竖八的尸体卧在路旁。不远处,一片小树林内,一名年轻男子朝这里飞奔而来,他刚刚亲眼目睹了惨烈一幕。这时,男子来至近前逐一查看了尸体,又在潘富贵的尸身前驻足,他伸出脚尖踢了踢尸首,突然又从腰间摸出一个玉石面具,他蹲下身将面具套在了尸首脸上,又摸出一张银票塞进了尸首怀中,随即男子起身朝城内飞奔而去。
潘六和郑通达一路逃回郑宅后,俩人哭爹喊娘向郑四义回禀。堂堂大玉商郑家的货竟遭劫!郑四义又惊又气又急,他一边吩咐潘六和大儿子火速报告官府,一边带领众家丁赶往城外。
当郑四义带人赶到出事地,四周早已空无一人,只有几只飞鸟啾啾鸣叫滑过他的头顶。围着几具惨不忍睹的尸体转了几圈,郑四义被那张怪模怪样、呲牙裂嘴的玉石面具所吸引,索性蹲下身子一把扯了这张面具,下面露出潘富贵灰白的圆脸,脸上那双圆睁的大眼依旧露出恐惧,他显然死不瞑目。
郑四义无心盯着死尸,转而反手查看面具,这才看清面具内竟赫然刻着“内奸”二字,他顿时吓得手一抖,面具霎时落地。众家丁看见郑老爷惊慌失措,赶紧聚拢过来,郑四义命令家丁们对查看尸首,俩家丁细细搜查了尸首后,竟从潘富贵怀中搜出一张银票。郑四义接了这张银票细看,发现这是城内“盛祥号”钱庄的银票,他立马连声惊呼:富贵是内奸,幕后真凶是马一坤!
“盛祥号”是大玉商马一坤所开,而他因生意竞争素来与郑四义不和。此时此刻,郑四义万万没想到,师弟竟然对他下了如此黑手。好你个马一坤!老子绝饶不了你!郑四义连声大叫,气急败坏。
少顷,官兵并没出现此处,郑四义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他顾不得多想,慌忙命人将几具尸体装上一辆马车,一行人匆匆赶回城内。
郑家遭劫,衙门竟没派人出城。郑四义回到家中大骂官府,可潘六小心翼翼回禀老爷:县衙中没见着知县影踪,只是一个师爷胡乱说是乱党作乱犯案!郑四义闻听郁闷不已,平日里他没少往衙门里送钱,可这节骨眼上却人来撑腰。然而,郑四义此刻并不知晓,因眼下时局纷乱,知县吴良臣早已坐卧不宁,哪有心思去管郑家之事。
次日,天刚亮,吴良臣派胡师爷去请驻军“精骑六营”的管带多尔衮.舒禄。
多尔衮.舒禄八旗子弟,是此地界手握军权的实力人物,正值壮年的他身高马大,脾气暴躁,胖脸上连鬓的络腮胡子,说话嗓门极大,下属背地里叫他“二踢脚”。
“来!喝两杯,这有油焖鹿肉!”多尔衮.舒禄走近后堂的朱漆木门,人没进来可肚皮倒先露了头,嗓门依旧底气十足。吴良臣紧走几步迎他,俩人分别落座,多尔衮.舒禄将装着鹿肉的皮囊一巴掌拍在八仙桌上。
“老弟。这月初,武昌乱党开枪开炮大闹后,湖广总督瑞瀓吓得领着妻妾逃了,他们慌得连茅厕都不敢上!孙大炮(孙中山)、黄兴真厉害,你我赶紧找退路!”
听他开门见山,多尔衮.舒禄一拍胸脯,“鸟!上峰命你我捕杀乱党,我让此地血流成河,何愁乱党不灭!”
“问题是——同盟会乱党们——脸上没刻——贼人二字!”
多尔衮.舒禄拔出手枪挥舞,“那好办,看着挂相的,全砍了!”
吴良臣心急如焚,“此言差矣!我师兄来信说,京师的王公大臣如热锅里的蚂蚁,纷纷准备后路,你我又算得了什么?赶紧狠捞几笔——溜!”
一听捞钱,多尔衮.舒禄顿时来了精气神,“倒也是,大臣们满脑子浆糊。我得到线报,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乱党秘密潜入咱润宝城,八成是来闹暴动……皇上年幼无知,起个名吧还叫宣统?宣统宣统,统统掀翻!得——大清朝怕是狗熊窝窜进老母鸡——凶(熊)多吉(鸡)少!”
“与其杀人,不如敛财!”
“朝廷一倒,钱财何用?”
“嘿嘿——官印如妓女,谁钱多谁上手;谁权谋老辣谁风流快活,哪朝哪代不是卖官买官,官帽子轮流转圈,再改朝换代都得拿钱开道,那时只怕钱不够用!”
“哥!兄弟听您的!”
“你立马领兵前往‘宝善街’,让脑满肠肥的玉商们……如今是宣统三年10月末(公元1911年10月),再捞三个月——撤!”吴良臣边说边伸出三根手指。
多尔衮.舒禄掐指一算,“我出力,你坐着,这次分钱,我拿8成、你拿2成?”
“你比我小,哥拿大头,我7你3?”吴良臣一瞪眼。
“你岁数大,该让老弟!我6你4?”
吴良臣摸了张银票递过去,“先给你跑腿费,就55分账吧,与其磨嘴皮不如多捞钱!”
多尔衮.舒禄笑着揣起银票,俩人又交头接耳……
时局一乱,城内谣言四起,百姓们更心神不宁,这使街面的生意骤降,但城内西仓巷的小铺“玉缘堂”倒买卖兴隆。
店主是顾玉鹤,健硕的他高且瘦,五官端正,算得上是英俊小伙儿。而妹妹月亮的瓜子脸上总露出开朗、单纯的笑容,唯有灵动的眸子偶尔闪现一丝忧郁。月亮很爱笑,一笑露出细密白玉般的牙齿,凡是进店的男客总觉她媚极了。
“玉缘堂”货品大到和田玉透雕摆件,小到卧于掌心的玉螳螂,全部惟妙惟肖雕工了得。小铺镇店之宝是“龟纽印章”,它的印座是浮雕和田玉,印把是惟妙惟肖的玉龟,但凡拿起印章一盖,那缩着脑袋的玉龟会弹出润白的脖颈!此印章被顾玉鹤取名为“独占鳌头”并吸引了众多买家。不仅如此,因市面上真假玉器珠宝鱼龙混杂,深信“以玉结缘”的顾玉鹤无偿给客人们鉴别真伪,如此一来他的生意竟红火起来。
“顾掌柜,看看我这块玉,说是宫里弄出来的稀罕物!”一个穿着绸布长衫的壮汉站在柜台前,满脸得意。顾玉鹤笑脸上前,双手捧过这枚泛着绿光的翡翠玩件。
“小弟鉴宝分文不收,可要是哪句话得罪您,我先给您赔礼了!”
“行啊——我不太懂行!”
“御用雕刻师刀法细腻,抛光细柔,此玩件是挂在腰间的饰物,可工匠刀法力度不够,没准头!我把它贴在脸上,冰凉度低于真正翡翠!是一件赝品!”
壮汉又摸出一块玉佩,“啊,赶紧看看这块和田玉的玉佩!”
“这是岫玉(价值较低的一种玉,产地辽宁省鞍山地区),质地细腻,水头较足,呈油脂光泽,常把它做旧来冒充和田玉。但岫玉质地软易吃刀,如用普通小刀刻几下,吃刀的是岫玉,硬邦邦纹丝不入的是和田玉。细看雕刻时的刀痕处,和田玉的刀痕不会起毛,而岫玉则有起毛……”顾玉鹤一口气滔滔不绝。
壮汉抄起两块玉便走,“老天爷啊——这两件东西我花了800块大洋!我找他们去,奶奶的真吭人!”
望着壮汉远去,顾玉鹤摇摇头暗想:这年头,晕乎乎上当的人真多!
这时,店里进来一位年长男客,他一言不发围着店内转了两圈。顾玉鹤坐在柜台内,手持刻刀篆刻一枚印章,旁边站着一个女客,她这枚印章是来料加工。顾玉鹤看见年长客人,赶忙起身招呼,可他根本没听见。月亮笑眯眯迎上前去,还问客人想看那种玉器?可客人还是一言不发,盯着她从头到脚扫视一遍,又从脚到头再扫视一圈,月亮笑吟吟望着他,觉得这位客人是个聋子。
顾玉鹤抬头看看此人,又低头刻起寿山石印章,只见印章和刻刀在他手中上下腾挪,左右翻飞,刻刀触碰之处顿时扬起细小碎料。顷刻间,一枚寿山石印章已刻好,刻法纯熟,刀纹清晰,当即博得女客的连声喝彩。
可一言不发的年长男客走到近前,一把抓起这枚印章细看。顾玉鹤问他是不是也想刻印?但他却惜字如金只说了三个字:好刀法!顾玉鹤和月亮满腹纳闷,可俩人并不知晓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大玉商——郑四义。
城里,红火的玉器生意都会引起郑四义警觉。这次,他信不过潘六干脆装成买主暗访后,总觉此人雕玉的做派很像王一刀,可几番暗访却毫无结论能把王一刀和顾玉鹤联系一处!
但说来奇怪,自“玉缘堂”开业后,郑四义和马一坤家里分别死了一名姨太太且死因蹊跷,两桩人命都是毫无征兆的猝死并死相恐怖,郑马两家请来仵作查看也均无头绪。但两桩怪事却令郑四义感到莫名恐惧,总觉与来路不明的顾玉鹤有关。与此同时,马一坤偌大的宅子每逢半夜就闹鬼!马家老少也开始疑神疑鬼,派人暗查“玉缘堂”店主的来历,可查来访去也没头绪。
原来,郑四义和马一坤之所以恐惧,都与一名女子密不可分,她是王一刀的老婆沈桂花。王一刀前妻病亡后没留子女,沈桂花刚嫁给王一刀不久,她父母双双病故,孝顺的沈桂花回乡守孝,可她的老家远在异乡。后来,沈桂花在老家产下一女取小名——月亮,族里规矩大守孝要三年,沈桂花等月亮满周岁托亲戚送回丈夫身旁,还稍信让丈夫给女儿取大名,但王一刀想妻子又碍于面子,一心要等夫妻团聚再给女儿取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