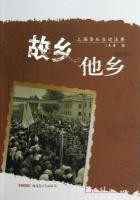正堂内,马鸿宝眼睁睁又见玉瓶漂着漂着,竟一头沉入了水底再也浮不起来,他和顾玉鹤不约而同连声惊叫。马鸿宝冷眉一横,一掌抓起宝物举到半空,只见几串水珠在半空中划出漂亮弧线,玉瓶被狠狠摔在地上,顿时碎片四散飞溅,它香消玉损。
马春芳再也忍不住,她箭步上去蹲下身,轻轻捧起玉瓶的碎片,眼中泪水流淌在润白碎片上,她哭着喃喃自语:碎了——真的被摔碎了——我的玉瓶啊!
顾玉鹤吃惊地盯着马春芳,心中极度纳闷:这小女子一惊一乍,看来马家人脑筋都有毛病!
“大胆顾玉鹤,敢用赝品羞辱我!这赝品恰恰证明你是卑鄙小人、虚情假意!亏你还是七尺男儿身,干脆阉了下面从此像个娘们蹲着尿吧!”
侯钱眼见大少爷如发怒雄狮赶紧冲出正堂,眼见月亮和俩家丁一同走来,他几步上前朝家丁一挥手,俩家丁心领神会押着月亮重又返回。
顾玉鹤此刻不知前院情况,瞬间怒火冲天,“马鸿宝——无耻小人——货收下还不放人!”
“放你个狗头!月亮迷途知返真对,我今晚就与她男欢女爱、整夜消魂。”
“我宰了你——”顾玉鹤冲上前去飞起一脚。
马鸿宝机警一闪,顺势给了他一记“黑虎掏心”,顾玉鹤气虚火旺,脚底发软,此刻根本不是马鸿宝的对手,他一闪身却被击中胸口,顾玉鹤哼了一声当即倒地,但他强忍剧痛一个“鲤鱼打挺”又翻身跃起,挥拳朝马鸿宝打去,俩人顺势扭打在一起……
其实,狡猾的马鸿宝早知宝物难觅,但故意刁难顾玉鹤,是想以此试探他对王家“藏宝”知道多少?如顾玉鹤胆敢拿赝品,趁机羞辱他解气并彻底断了其念想。马鸿宝果真得逞,还让顾玉鹤吃了哑巴亏,甚至击碎了他营救月亮出火坑的计划。
次日正午时分,黄澄澄的太阳斜照着一派喜庆气氛的马宅内外。
马鸿宝披红挂彩站在正堂门口,吆五喝六指挥东跑西跑的佣人们,周围张灯结彩、敲锣打鼓,他终于等来迎娶月亮的良辰吉日。
前院内,布满一桌桌摆着各色佳肴的丰盛酒席,前来马家贺喜的人们围坐桌边,他们有说有笑,交头接耳。少顷,一阵刺耳鼓乐霎时响起,门外一阵鞭炮齐鸣,炸开花的红色纸屑飞扬在半空,空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道。
正堂石阶上,小眼睛乐成一条线的年迈司仪一声高喊:婚礼开始!马鸿宝和蒙着火红盖头的新娘子缓步走来,俩人还被一条中间系着硕大绸花的彩带相连,众人随即一阵响亮喝彩。
仓促拜完天地,新郎并没掀开新娘红盖头,扯住扭扭捏捏的新娘径直奔了洞房,客人们露出一张张纳闷表情,可俩个团防局的军官高声笑着,齐声高喊:鸿宝老弟悠着点儿——别一使劲儿把床压塌了!
众人一片哄笑,俩军官得意抄起桌上酒碗相互一碰,各自一饮而尽,那个五短身材的胖军官扯下一条烧鸡腿塞进嘴里大口撕扯。这一刻,酒宴正式开始,杯盘碗筷声叮叮当当热闹响起,四周满是一张张涨得通红的脸,人们醉意朦胧、彼此的目光充满着笑容,放荡的话语不绝于耳,一张张长得或大或小、油晃晃的嘴嚼着喝着说着撇着,还有不停在红色桌布上流着酒肉汁水的大嘴。总之这一切,喜滋滋的人们正大吃喜酒。
一个时辰后,马鸿宝回来走到宴席正中,顿时又一片喝彩声,他端起一个碗酒大声说:“诸位静一静——谢谢大伙儿捧场——吃好喝好乐呵好!”
黑压压的人堆里,已喝得烂醉的胖军官摇晃着站起,他上身的军装被肥肉绷得紧紧的,扬起红彤彤的麻子脸用力大喊:马老弟——咋才来啊——新娘子屁股亲够啦!众人又是哄笑,马鸿宝非但没生气还大声回应说:“刚乐呵完了——味道不错——你小子羡慕嫉妒恨去吧!
这时,一位满头银丝的耄耋乡绅脸色煞白,弯腰朝地上“哇哇”吐了口酒,脸上忽然又老泪纵横,他站起来猛然大喊一嗓子:“这事儿太妙啦——”喊完,老者醉醺醺的一头往后躺倒。旁边,邻座的几个人七手八脚将老者抬起,可他已醉得鼾声大作。老者语惊四座,又一片哈哈大笑声骤然响起,马鸿宝慌忙吩咐佣人们将老者抬走醒酒。
马家盛大喜宴惊动城内,一时间引发城内街头巷议:马副官和月亮真成亲了!喜讯传得飞快,这些不明就里的热络议论传至顾玉鹤耳中,他万念俱灰,一口鲜血从口中喷出,郑翡翠见状吓得浑身冷汗。
与此同时,月亮被软禁在马宅后院一处东偏房内,外边马鸿宝大摇大摆迎娶之事,她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马鸿宝唱得这出空城计,是招摇过市的真成亲假迎娶,蒙着红盖头的新娘竟是一个冒牌货。此前,月亮根本不让马鸿宝近身,还时时刻刻要自杀,马鸿宝虽着急上火的三番五次来骚扰月亮,可无奈下半身根本不管用,他干脆将计就计,想出这一怪招再狠狠惩治顾玉鹤。
入夜,喧闹一整天的马宅终又恢复平静。
这时,偶然瞥见月亮正在东偏房内梳洗,马鸿宝又进来调戏月亮,俩名看守家丁一见慌忙躲出门外。屋内,月亮再次以死相拼。这档口,马鸿喜闻声从前院赶来制止哥哥,还拉着他一起去喝酒。马鸿宝心有不悦,但弟弟曾献妙计令他克敌制胜,马鸿宝转怒为笑还是给了弟弟面子。随即俩人并肩来到书房,又命佣人摆好了酒菜,兄弟俩把酒言欢好不欢喜。
俩兄弟酒酣耳热之时,马鸿宝舌根发硬地告知弟弟,顾某在较量中落败必定气病交加,着实心头大快,他明知那小子的复仇计划,但就不给郑老贼送信儿,彻彻底底感受一下借刀杀人的快感,毕竟坐山观虎斗挺爽!
马鸿宝竹筒倒豆子般又说,他早在郑四义身边安插了眼线,就是郑家三姨太李巧珍,珍儿风骚爱钱,你哥我也风流倜傥,我和她都觉相见恨晚,不过我还是下血本才拉她入伙,郑家一举一动她全掌握,咱要出阴招尽快搞垮郑家,重夺马家大玉商的地位!
俩人又一番推杯换盏,正聊得热乎,突然一阵凄惨“鬼哭”传来,只听书房门外有个家丁边跑边叫:北厢房又闹鬼了!
屋内,马鸿喜闻声震惊起身要去开门,而马鸿宝一脸不屑地朝他摆手说:“扯淡!厉鬼怕恶人,好人不能当!”说完,马鸿宝哈哈大笑起来。一霎时,他的笑声伴着窗外又一阵呜咽地“鬼哭”着实瘆人,马鸿喜手脚发抖,感到后脊梁一阵发凉,额头渗出一层冷汗。
后院内的北厢房闲置很久,原是马一坤二姨太“秀姑”住处,“秀姑”生前貌美,秀发飘逸,马一坤很是宠爱她。但两年前的一个冬夜,“秀姑”毫无任何征兆的莫名上吊而死,那时的前清衙门曾派仵作来验尸,仵作称她是被人掐死后制造上吊假象!事后,衙门断案不力,却在佣人里胡乱找个替死鬼了事。从此“秀姑”住处阴森空荡,没人愿意靠近这处凶宅。不久,每逢夜深人静,北厢房内鬼影飘飘,此处竟变成了闹鬼场所。据偶然遭遇过女鬼的三个女佣说,每逢西北风狂吹的子夜,“秀姑”两眼淌血,披头散发,两脚离地,僵直伸着又长又尖的滴血指甲,四处游荡来找“真凶”。神乎其神的鬼事连马一坤都信了,可唯独胆大的马鸿宝不信邪,曾硬拉弟弟潜入北厢房一探究竟,结果俩人什么也没查清,倒是马鸿喜吓尿了一裤子。
这会儿,月亮被软禁在东偏房,这里距离北厢房很近,外边又传出阴森嚎叫,一阵狂风猛地吹开东偏房的一扇窗户,房内的月亮吓得浑身颤抖,她本想夺门而逃,但房门已被看守她的家丁从外反锁,而家丁们也怕厉鬼上身,他们扔下月亮抱头鼠窜,东躲西藏。
月亮自从被禁马宅后,曾遇到过两次闹鬼,偶然还听到看守家丁嘀咕这事,她此刻越想越怕,吓得连连倒退不觉已缩到墙角,颤抖身子紧贴在冰冷的墙上,可这时房门突然大开,一阵阴风迎面吹进来,风声呜咽,月亮想上前关门但腿脚瘫软,又顺着房门朝外一看院中毫无人影,唯有月影下一片竹林随风摇曳,发出阵阵沙沙响声。
月亮一激灵,鼓足胆量冲到门口关门,只听一个清脆女声骤然响起:“别关门!”
一个人影突然从斜刺里闪出,来人竟是马春芳。马春芳是马一坤独女,她个性磊落敢爱敢恨,是个地道的新派女性。她早听说顾玉鹤的事情,也替月亮惋惜鸣不平,但对一向胡作非为的大哥却没办法。
“你怎么在这儿?”月亮颤巍巍问。
马春芳笑着进屋,反手关了房门,“瞧你吓得脸色煞白,好像女鬼的脸。”
月亮一听女鬼又一激灵,重又快速缩到墙角,惊恐望着马春芳,“你见过女鬼?”
看月亮吓成这样,马春芳没再开玩笑,“如今这世道,人比鬼可怕。”
“啊——”月亮似懂非懂。
“我没见过鬼,跟你一样,不过我有这个!”说着,马春芳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晃了晃。
月亮更恐惧了,“你,你你,想干什么?”
马春芳笑着把匕首往桌上一拍,“我来陪你!”
望着她一脸真诚,月亮稍微,“大小姐,你甘愿来陪我?真的假的?”
月亮可怜兮兮的,娇小身躯不住颤抖,马春芳心里怜香惜玉起来,她上去一把揽住月亮身子,“别怕——你把我当成大哥——我保护你!”
窗外,又一阵狂风呜咽刮过,月亮抬眼望着她,眼里闪烁泪花。这夜,马春芳留在月亮房内,还劝慰月亮说,马家闹鬼已久,看开也没什么可怕,毕竟身正不怕鬼叫门!月亮觉得马春芳很和善,便恳求她协助自己逃走,可马春芳摇头说,大哥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做得出,他曾放言只要月亮逃走,就立马派人秘密杀掉顾玉鹤。一番话令月亮垂泪,不禁又想起了情郎。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月亮给马春芳哭诉了“哥哥”的事情,从她只言片语中,马春芳竟对顾玉鹤陡生了好感。
月夜,暮色苍茫,万籁寂静,天穹中惨白的星星眨着眼,仿佛注视着凡间一切烦恼。这恼人寂静之中,偶然会有几颗流星瞬间陨落,发出耀眼闪光的轨迹映在清溪上空。顺着清溪吹来的轻风,还将湿漉漉的野花芬芳一路送进郑宅,宽敞院落内的草地上露水很重,几只蛐蛐躲在草丛内不停发出哀伤鸣叫。
顾玉鹤再次病倒后,郑翡翠每日悉心照料他,端茶送药,就连郎中开出的药方,她也一味味药的亲自过目。可郑四义得知后很生气,女儿并未嫁人成天却与顾某厮混,有事没事就往这个大男人的房中跑,他借机训斥了女儿几句,可骄横的郑翡翠根本不听劝,反而怒气冲冲对他说,不是爹当初糊涂犯错,我能落得个如今凄惨下场,何况现今还有人敢要我嘛!郑四义哑口无言以对,只得听任女儿来去自由。
冷冷夜风随窗而入,顾玉鹤醒来起身下床,恍惚中看见郑翡翠对他眯眼笑着,可他沉默不语,脚下如踩棉花,轻轻一纵身竟腾空而起飞出门去,他穿过一片透明旷野,四周静得出奇,使他耳朵里嗡嗡直响。俯身鸟瞰,视野舒远,下方是一条闪烁光亮的群山,头顶是布满灰色云片的茫茫天穹。云海迷幻,顾玉鹤伸手去抓空空如也,但一处云朵后面分明显出月亮的音容笑貌……他奋力飞身过去,却见月亮笑脸陡然变成马鸿宝的狞笑,他用力一抓,那狞笑又成了一个美貌女子的粉脸,但他似乎从没见过她。听见一群飞鸟发出凄厉惊叫,他霎时从云端跌落下去,身子径直坠向无穷无尽的深渊,他急忙抬头往上看去,陌生女子已不见踪影,霎时又见郑四义探头探脑,旋即又换成郑翡翠那迷人的笑容,他瞬时重重摔在硬邦邦的地面。
这一惊,病榻上的顾玉鹤从梦中惊醒。他大梦初醒,用六神无主、眼眶深陷的眸子向四周扫视,这才发现郑翡翠坐在床边已是泪眼婆娑……
日夜轮回着从润宝城的上空飘逝,时光一周周地飞逝,一晃一个多月过去。
顾玉鹤大病已愈,苍白面色的他眼神里看不出任何悲伤,他面无表情只是嘴角仍挂着从前的淡定,仿佛此前什么事情也没经历过。重回“大观斋”总店后,顾玉鹤每日起早贪黑忙碌,似乎拼尽全力又给郑家卖命,郑四义暗中注视着他的举动很是纳闷,不过他心里反倒掠过一阵轻松。
郑翡翠历经婚变后,她那女人晚来的爱情已变得疯狂,好像道旁的迷人野花。而顾玉鹤一直躲避她成亲的要求,对此郑翡翠倒也大度,直言表示她不会逼婚,会等顾玉鹤完全接受她时才行。
然而,顾玉鹤外表平静如水内心却波涛汹涌,心爱妹妹被“贼人”抢了,身边女子却是仇人的千金,他暗下决定彻底斩断一切儿女情长,痛定思痛后的他再把复仇大计提上心头,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最后放手一搏。
夏去秋来。强劲西北风横扫润宝城,这风将城外蟠龙河的气息一路卷来,散发出的水草腥气还和着一丝淡淡的野花香气。白天,狂风裹挟落叶,逐街追逐。夜里,满月高悬,风刮乏了,但每条街巷里凉气阵阵,显得冷冷清清。
座钟刚过子夜,顾玉鹤又换上一袭夜行衣,他悄然出了房门,像脱兔般跃出偏院,沿着高大的院墙一路弯腰小跑,又蹑手蹑脚来至后院一处厢房门外,他蹲在窗下四下里查看一番,又拔出腰间匕首撬开了一扇窗户,一闪身翻窗而进。
此刻静得出奇,这间南厢房内伸手不见五指,宽敞外屋家具却很少,只有一张八仙桌和一口木箱,房门两侧是几扇雕花木窗。顾玉鹤半蹲着扫了一眼,三两步进了里屋,窄小里屋竟然没有窗户,墙角竖着一个梨木雕花大立柜,旁边是一张顶子床。南厢房的陈设显得异常简约,但这是郑四义的第6处寝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