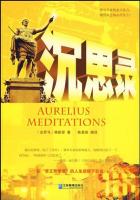明代晚期及清初,儒学有一种“平民化”的人文倾向,儒学不再是精英之学而走向大众,这当然是一种时代精神。但另一面,清儒特别是戴震,则不满于宋明儒对人之自然情欲的忽略,将理与情统一起来;王夫之亦复如此,将理寓于事中,是他的最根本的理论宗旨。总之,清儒强调人事的重要性已超过宋明儒,这显示了一种新人文价值的转换。尤有甚者,王夫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担待,而系统论述了“时”与“势”的价值意义,将理与势打成一片。他和黄宗羲、顾炎武等清儒同样,重视“人为”的重要性;但对天理人事统一,则是王夫之一生的理论方向,作为清代大儒,他似乎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人物,而其新人文价值取向的理论实现,也充分体现在王夫之身上。如果说,宋明儒学的人文精神体现在要人“作一个真正的人”,顶天立地的人;那么,清儒则更重在“成事”的制度精神与经验上。但无疑,二者均是本于儒家一以贯之的人格、人道的人文价值前提,来突出其价值转换的。
人类的生存、发展毕竟要靠道德的维系,法治无法取代德治,正如技术文明代替不了道德文明一样。而诚信作为人类最基本、最必须的伦理准则,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修身实践中,都成为了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最核心部分,从而在历史过程中,人们无不将其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价值取向。深究诚信巨大的社会协调、和谐功能,我们当知,诚信代表了人性中最为初始、最为自然而毫无造作的善德。儒家之所以极端重视个人修养,追求个体的人格完善,首在让人们能持守这一最基本而内在的善德;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修持方式如:切己省察、涵养持敬、慎独主一等途径,达至圣人境界。试想,没有“诚”,何有“敬”?心有不诚,何能尊敬他人?所以儒家讲“诚敬”,毕竟诚在前。再设想,没有信用,何谈互利?所以儒家认为只有在诚信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从个体道德扩及人类道德。千里之途,始于足下;再复杂的伦理体系与社会行动,也将始于最基本的人之诚信。王阳明当年说他看见满街都是圣人,其实并非真的满街圣人,而是王阳明以其所达致的极高道德境界,俯看人类,悟及人人都有修德成圣的可能。用佛教的术语,王阳明早已洞明人人皆有佛性。
然而时代又毕竟转入技术文明带来的市场经济社会,时代既不可扭转,难道最基本的道德律条就可弃置吗?否!从古到今,儒家并没有排斥必要的经济活动;相反,儒家认为,越是复杂的经济活动,越要依靠信用制度体系来维系。否则,就会象庄子所言,人类在机巧发明用尽后,最终毁掉的是自己。儒家虽然以义利之辩来区分君子小人,但从来就没有否定“利”的基本合理性,而是要人们以合符道德的途径、手段、方法去获取正当利益;在根本上,儒家要求一种较完美的境界:义利统一。实在不能统一,将取义弃利。
当然,古典伦理形态在现时代,需要向现代形态转换;但这并不意味着须推翻根本原则,而是要根据时代特色作些“协变性”调整。试想,上古时期“以物易物”的经济活动,转至近代货币体系发明后的经济交易,难道不需要新制度的加入与相应经济法则的调整?其实近代群体儒商的出现与现代“信用社”(取信用二字正好合于儒家诚信理念)的出现,都从积极的价值取向上,反映了儒家道德信条的坚挺与经济活动中“协变”姿态。须知,儒家的经典文献《周易》就有“与时偕行”的观念,孔子本人则在儒学史上被称之为“圣之时者”,程、朱、陆、王都讲“时为大”,王船山更是主张要“协于时”,然而他们无不坚守最基本的诚信美德。西方学者在深入了解了孔子儒家思想后,大为感叹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作为整个世界的“道德金律”。1988年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发表宣言,极称21世纪的人类社会当重新汲取孔子儒家的智慧。
在新的时代,我们之所以要讲“协变”精神,就因为我们仍然要在新的文明中获得进步,但这一进步决非单一的直线的弃置人性内在美德的进步,而是要获得一种圆满的保持人性美德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要时时、处处显示出真正的人格魅力。儒家认为伴随道德文明的进步才是真正圆满的进步。“协变”之变,就表征了变的进步;而“协”的前置限定,更代表了一种更为基本的准则、态度、价值取向的持守,这就是几千年来儒家一直要人们牢记的“如何取得和谐条件下的进步与发展”。须知,“协”,不仅有协作更有和谐之本义。所以用“协变”这一范畴,本身就在知识论上比儒家单纯用“和合”范畴,更进了一步。
仅举一例,西方社会中讲究的“公德”文明,就值得我们关注,而儒家只是一味地认为,讲究个体修身的私德,必然地会发展出公德,然而社会运转越快、人口越多、人群相处形态越复杂,其中就越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系统因素和需要沟通的环节,例如现代社会的“社区”形态,就和儒家所重的以家庭为主村落形态有所区别,又如现代信用体系,是基于独立、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的活动,而儒商“诚信”的信用规则,大致在“承诺”等基本尺度上与现代信用体系可沟通,而在一些层次上仍有些区别。所以基于时代,不变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儒家本身是极重视“常”与“变”的辩证法的。
然而同时,我们也要切记,诚信乃人的“自然良知”,它就像现代人倡言“自由”的天然前提那样,有着人性深处最具始源性的基础。因此,伴随良知的“节制”,就如同伴随自由的“选择”一样自然而然,一样源远流长。此外,即便站在“现代”人的角度,也将会与儒家一样认同“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一命题,然而重要的是,人的自然天性中,就包括了最卓越的社会品性——诚信。所以本文的结论是:社会越是复杂,发展速度越快,就越是需要人自然本有的诚信之品性。笔者坚信,儒家的这一思想资源,不仅没有过时,还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更为系统的深度发掘;从而为现代制度文明中的信用体系建设,作出新贡献。
笔者的结论是,现代文明的制度文明,仍离不开人类历史文化中的“诚信”源头,且须以这一源头为前提。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原是不可分割的。
二、从古代诚信观到现代信用体系的实践
对儒家而言,诚信当然不只是观念,儒家一开始就讲知行合一,道德实践须与道德观念须完全统一。然人类历史演进与行为体系复杂性的增加,可以说出乎儒家预设范围的事情在日益增加。我们从商业领域中“山西票号”的最早出现,发展到今天强大的银行信用体系的完善建构,完全可透视到中国古代儒家诚信观的烙印。“儒商”一词的出现,表征的就是以儒的诚信观为前提的商人及商业系统的出现。可见,儒家仍在其中大有功劳。
从中我们该悟解现代认知科学中所谓“人工事物”为何愈来愈发达,而现代信用体系只是其中一桩而已;当然,缺失诚信观的依托与支撑,这一人工体系的现代建构是难以想像的。没有基本的诚信,整个社会行为体系将成一团乱麻,而这恐怕首先是认知体系中的一团乱“码”造成的。所以我们所可庆幸的是我们的先人有那么深刻而丰富的“诚信”思想。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西方著名哲学家卡西尔是怎么认识自然与人工符号的:“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人不仅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中,而且他自身也变成了相应的符号。”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物理”符号,也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天文”;但人不仅被“天文”这种物理符号所包围,也被自己人为的“人文”符号所包围,所以卡西尔得出结论说人是能够使用符号的动物。
从技术的角度看,人文符号也就是人工符号,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就相当有见地地指出过:“工业机械文明之价值,吾将不由其表现吾人征服自然之精神以说,吾唯说其可使物力互相转化,物质互相变易,此即使分立之物力物质实显其纵横交错之文理。”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创造》,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412页。在自然之“文理”基础上的人工“文理”之创造,是中国儒家重视积极的“人为”,感受人工事物的起始点。荀子早就指出了这点。
再来看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对人工事物的看法:“我们称为人工物的那些东西并不脱离自然。它们并没有得到无视或违背自然法则的特许。同时,它们又要适应人的目标和目的。……人的目标变了,其创造物也随之而变。” 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7页。西蒙强调了人工事物要符合于自然法则与规律,这与中国儒家人文通天文的“同构”的先见之明有一致之处。西蒙还区分了人工事物与自然物的四个方面以确定人工科学的范围:
1、人工事物是经由人综合而成的(虽然并不总是周密计划的产物)。
2、人工事物可以模仿自然物的外表而不具备被模仿自然物的某一方面或许多方面的本质特征。
3、人工事物可以通过功能、目标、适应性三方面来表征。
4、在讨论人工事物,尤其是设计人工事物时,人们经常不仅着眼于描述性,也着眼于规范性。 赫伯特·A·西蒙:《人工科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9页。
无论是卡西尔所说的“符号”,还是西蒙所说的“人工物”,都和儒家经典文献易经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有着同等重要的人作为创造主体存在的人文意义,“人文化成”一语被后儒时常引用,道理即在此。关键在于,儒家还自此开始了对人的生存方式、道德行为以至制度文明的高度关注,这是与其早期对“人文”的认识分不开的。
要之,“人文化成”一语意味着人是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他能创造并使用符号,以促成人工事物的完善,而这正是儒家以观念、信仰以及器物、风俗、制度来构成其特有文明的创造力所在。儒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伦、人道、人性、人格等一系列思想,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文思想体系。如果说,儒家学说以其巨大的功能而成为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代码(代码的意义是在日常生活中可随时见效),那么,这一代码本身就是由博大精深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资源所转换而成。直到今天,这一人文代码仍在无形中发挥其功能,我们现在常说的德治观,其实就是儒家“人文化成”的一个积极成果。
而从中国儒家的诚信观,到近现代信用体系的建立,这当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创造性的转换。从货币、银行到健全的信用体系,虽是一种“人文化成”的人工事物的发明,但决非说人在其中可胡作非为;相反,人在其中完全是规律的发现、遵从乃至执行者。因而现代制度文明的建构,就显得尤其必要而紧迫了。质言之,现代市场离不开诚信基础,而诚信基础之上的信用体系的完善则离不开现代社会整体性制度的建构。
三、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必然性与紧迫性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目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的难度之大,各种实质性问题的呈显,使得制度文明的建设显得尤其重要。
亚当·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是合乎自然与人性的、天然的自由制度。市场经济若不符合人性的规律,就没有基本的合理性;而符合人性的市场经济,必定是能调动人的内在潜能的经济。从人文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在发挥它本有的经济职能的同时,还最佳地利用了人类最宝贵而稀缺的资源:能力、智慧。“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当今最普遍的、唯一可行的经济形式,是因为它是人们经过漫长的探索和积累所得到的最契合人之本性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也最契合人的有限理性,因为它能以制度的自发性来运转、自动地配置、自动地调节市场(当然历史性看制度本身,它有时也是需要人来作调整),但,不需要人的全知、全能;也没有任何这样的全知、全能者。然而计划经济是建立在计划者的全知全能的假定之上,由于这样的人不存在,无限的理性不存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就注定要破产。”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见《学问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2页。斯密认为,使一个国家最快强大起来的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虽然在市场经济中人的出发点可能是自身利益,但相互作用自然或者必然会导致对社会的有利。如此看来,“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03页。而哈耶克则总是从“自发的”开始的符合理性的制度角度去看待市场经济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