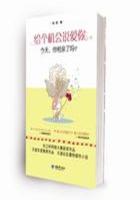王梅花大半辈子生活在忧虑之中,花甲之年就满头白发了,饱经风霜的脸上也爬满了一条条皱纹。年岁不饶人,孤身一人的她只得进了乡敬老院。这天,她忽然听到,住在梅杏尖的张阿福,也要到敬老院来了。她原本平静的心,顷刻不平静起来。
其实,张阿福是胖是瘦,是长是短,她也没有看见过。可是,几十年来,张阿福又搅得她心神不宁。
解放那年,王梅花听到自己的恋人张大年为逃壮丁跳青山溪而死的消息后,也跳进了溪中。幸亏被开会回来的村干部看到救起,漂泊流浪的王梅花在青山村住下了。
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青山村正在分田地,王梅花分到了房屋和土地,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勤劳贤惠秀丽的王梅花,自然招来了不少求婚者。她也知道,一根柴草难起火,单枪匹马困难多,何况她还年轻,也有七情六欲,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对对,也有成家的想法。
一天,邻村的媒婆李三婶前来提亲,说是离青山村二十里远的梅杏尖小山村,有个民兵队长叫张阿福的,愿意到青山村入赘落户。王梅花经过反复思考,也就答应了。在这古老的山村,男女婚姻大事还得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梅花没有父母,只得由媒人了。双方约定,中秋节那天,张阿福背上铺盖,下山和梅花办理登记结婚手续,并举行简单的婚礼。
八月十五那天,梅花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换上一套新衣服,等待那个没有见过面的新郎。可是,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下去,一等等到月亮像个大银盘挂上天空,也不见张阿福的影子,贺喜的人只好三三两两地散去。真是水深好测,人心难探,张阿福到底为了什么呢?王梅花和李三婶,一个埋怨在心里,一个唠叨在嘴上。十六的太阳刚露面,李三婶又去梅杏尖了。
直到日落西山,李三婶才气喘吁吁地回到王梅花家。说是有个叫宋嘉罗的地主,解放前夕拉起了一批地痞恶棍,上山当了土匪。昨天一早,土匪来到梅杏尖村附近,张阿福听到这个消息,放弃了自己的结婚大事,带着民兵和解放军一起剿匪去了。
战斗中,宋嘉罗被当场击毙,但张阿福也负了重伤,送到省城医院去治疗了。木不钻不透,人不说不明,王梅花心中暗暗称赞,张阿福是个好样的。
几天后,传来一个噩耗,李三婶在给别人做媒途中,失足跌在一个一丈多深的石坎下,头撞在石头上当场死了。张阿福和王梅花这对靠李三婶单线联系的婚姻,也就断了线。王梅花虽对张阿福牵肠挂肚,但世上只有靴紧袜,哪有袜套靴的,何况又没有见过面,王梅花只好是大风地里吃炒面——开不了嘴。她想,只要张阿福没有生命危险,肯定会来找她的。
可是,一年年过去,张阿福像断了线的风筝,一点消息也没有。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对于后来的求婚者,王梅花一概回绝了,在黄昏的孤灯下,她常常拿出一只布鞋看了又看。
春去秋来,转眼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期。一天,王梅花忽然收到了一封县民政局寄来的信。在县城,她一无亲戚,二无朋友,这是谁写的呢?亏得解放后在扫盲时识了几个字,拆开一看,竟是张阿福写的。信中说,以前的事只好请你原谅了。那年伤好后,我的脚跷了。李三婶死后,本想直接来找你,但一想自己成了一个残疾人,不知你是否会答应呢,就死了这个心,准备过独身生活了。后来,我在县民政局工作了,脚也医好了。最近听人说你也一直未嫁,不知是否真的,如可能,两个独身人组成一个家。今天投石问路,急盼回信。
断了十多年的红线又接上了,人到中年的王梅花,胸口像有一只小白兔,怦怦地跳个不停。她马上写好回信,投进了邮箱。可那只绿色的邮箱成了蓝色的大海,这信也就如石沉大海。后来,王梅花又去了几封信,竟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张阿福啊张阿福,梅花心中的爱情之火已经熄灭,你来点了一把,当她的心被重新燃着后,你却避而不见了,这不是在捉弄人吗?
星移斗转,30年又过去了,张阿福在乡干部的帮助下,也来敬老院了。这张阿福是否那个张阿福呢?王梅花可要问个明白了。她一看,这张阿福有点面熟,又记不起在哪里见到过他。见他在整理床铺,就走过去帮忙了。趁此机会问:“你是否在县民政局工作过?”
张阿福点了点头反问:“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王梅花。”
他们谁也不会想到,第一次见面竟会在40多年后的敬老院。两位老人的心中泛起了一种共同的渴求。同样的惶惑,同样的忐忑不安,过去的一切在他们面前旋转着。和王梅花相聚,又引出了张阿福在“文革”期间那段痛苦的往事。
那年,他寄信给王梅花后,“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在他的档案袋中发现一张他枪杀地下党员的检举信,一审查,张阿福在这段时间被抓了壮丁,时间上吻合。这样,证据确凿,他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分子抓进了监狱。王梅花自然收不到他的信了。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原来,他参加工作时,那个节约模范的文书看到一只装过反革命分子张寿福档案袋空着,就擦掉一个寿字,改成了阿字,装入了张阿福的档案。那只档案袋中遗留了一封小小的检举信,在那个说不清的年代,造反派说张寿福就是张阿福,使他蒙受奇冤。等到真相大白,他已到了退休年龄,没有上班就领到了光荣退休的镜框。在县城举目无亲的张阿福,就回到了梅杏尖安了家。年岁大了,婚姻也不去考虑了。
这又不是张阿福的过失,王梅花擦了擦盈眶的泪花,默默地为张阿福端来了热水。
张阿福洗好了脸后准备洗脚了,他在那只藤箱中寻找袜子,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放到床上。一只老式圆口布鞋出现在眼前。王梅花的眼睛模糊了,她感到自己的呼吸分外急促,好像在做梦。这时,张阿福卷起裤脚洗脚了,王梅花偷偷一看,他膝盖上有个伤疤。就连忙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那只珍藏了40多年的布鞋拿了出来,和张阿福的那只放在一起,刚好是一双。
张阿福也看到了王梅花耳垂下的那颗黑痣。“你是大年?”“你是杏花?”他们已老泪纵横,不知是辛酸的泪还是幸福的泪。
解放的前一年,同在宋嘉罗家做长工的张大年和做丫头的王杏花相爱了。有一次,张大年砍柴时不小心在左脚的膝盖上斩了一刀,是王杏花采来草药,及时地换洗包扎才痊愈的。一天,王杏花得知宋嘉罗要收她做小老婆,就趁风雨之夜和张大年偷偷地逃跑了。
这天中午,他们刚在凉亭休息,忽然过来一队兵,二话不说,把大年抓了壮丁。杏花死死地抱住大年的脚不放,结果被一个兵用枪托敲了一下昏死过去了,等到醒来,只看到手中抓住的是只张大年的布鞋。
王杏花也学孟姜女千里寻夫,为了避免碰上宋嘉罗及他的走狗,她梳了个盘盘头,讨了件破大襟衫换上,脸上用灰尘抹了一下,改名为王梅花,一路要饭,一路打听张大年的下落。
一年后,她来到青山溪边,听一个摆渡的老船工说,去年这个时候,大雨过后的溪水又混又急,一队兵拉着几个壮丁过来,要老船工把他们送到对岸。船到溪的中心,一个只穿一只鞋子的壮丁趁他们不注意跳进了滚滚的溪中。那些兵连忙朝水中开枪。这么急的水,就是不被枪打着,也难活命。
王梅花瘫坐在溪边,一阵难以抵挡的悲痛揉断了她的心肠,那个穿了一只鞋的壮丁不是大年又是谁呢?大年已死,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树高百丈也是烧,人生千年还是死,一死就一了百了,她大呼一声:“大年,我来了!”就“扑通”一声跳进了溪中,幸好被人救起。
其实,张大年并没有死,他跳水以后,一个猛子随急流斜游到岸边,钻进了下垂的柴草中。那些兵朝下游开枪,自然伤不着他。他在水中浸了七八个小时,夜深了才上岸,却已找不到杏花。为了避免宋嘉罗及那些兵的寻找,他改名为张阿福,在人烟稀少的梅杏尖上安下身来。后来听说王杏花已经投溪而死,就把那只杏花亲手为他做的鞋子保存下来作纪念了。
敬老院的老人们知道了他们的曲折遭遇后,一定要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婚礼。他们让出了最好的房间,粉刷一新,门上贴上了大红喜字。
这天,乡干部都来贺喜,县里电视台还来拍了新闻。一对古稀之年的新人,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在大家的簇拥下进入洞房。
这正是:棒打鸳鸯两分离,红线几度断又连。风风雨雨几十年,敬老院结并蒂莲。
(载浙江《山海经》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