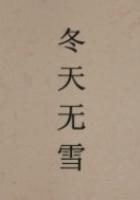曾经许多个早晨,我穿过从芦苇湖中开辟出的一条道路去上学。路两侧,是挤满芦苇的绿色的湖,暗色的芦苇丛的上方,白色的水汽在晨曦中蒸腾缭绕。一只红掌的黑色水鸟从一边的苇湖中跑到路上,又飞快地钻入了另一边的芦苇丛。拥挤的芦苇给众多的鸟儿营造了一个安全的家,最多的是一种类似于麻雀的我们叫做“麻喳喳”的鸟儿,在芦苇丛中不知疲倦地欢叫着。那鸟儿是芦苇的音响,但那不是芦苇的歌。风起时,芦苇丛荡起飒飒、沙沙的沙哑而低沉的歌随风飘扬,这歌声常常会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这里面蕴含的生命气息多么浓厚呵。
芦苇是一种美丽、柔韧而坚挺的植物,有着晶莹剔透修长有节的枝干,芬芳劲挺的青绿的叶子,头顶一束紫色的盔缨般威风的缨穗,线条流畅,气宇轩昂,坚挺而不乏柔韧。他们密密匝匝地拥挤在湖沼中,枝干挺拔独立,风骨劲然;根节在地下纠缠不休,彼此连接,情谊绵绵。
后来,我偶尔会去看画展,发现芦苇也是经常入画的题材。可惜的是,我看到的画中的芦苇总是大面积的芦苇荡,覆着白色头花的枯黄的芦苇丛空旷辽远,中间几汪水泊,呈现出一片寂寥、悠远的意境。或者,芦苇只是作为其他景物的陪衬而入画。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芦苇的特写,没有青葱的充满生机的芦苇入画?几株青翠可人的芦苇,顶着紫色的头穗,迎风招展,身姿挺拔,骨节挺立而不失秀雅,悠然从容而不失劲张,该是多么美的画面。我想大概画家没有读懂芦苇的味道。这也许和芦苇的常态有关。他们总是密密匝匝地拥挤在湖沼中,根节在地下纠缠不休,彼此连接,就像芦苇湖间的村庄里朴实平凡的人们。
根据大人们的记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生长的这个小村庄被芦苇湖所包围。东面、西面、北面全是湖,湖中布满芦苇,整个村庄就像一座深入芦苇荡的半岛。芦苇丛碧浪如潮,芦苇丛间的湖面映衬着蓝天白云宁静悠远。远望,北边是隐隐约约一座叫做银川的城市,西边,巍巍贺兰山隽秀屹立。芦苇湖之间的村庄里的居民除了人以外,还有很多叫做“青木桩”的鸟儿。“青木桩”是农民对苍鹭的称呼,这个名字有误导的倾向,农村人的朴实把一种美丽的鸟儿给丑化了。那些鸟儿亭亭玉立、毫无戒备地在人们周围优雅散步,或者跟在劳作的人们的后面觅食,或者翩然飞过。更多的它们是娴静地静立着,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半岛”是“青木桩”和人们共同的家。
我没有赶上小村庄那段美丽的历史,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听着大人们的描述,我心仪无比,为此,我一直遗憾我晚生了好多年。到多年后的现在,在一次大型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我们制作了一本宣传画册,其中有一幅体现本地自然风光特色的典型照片:一只巨大的仙鹤展翅飞过广阔的芦苇湖,远处,还有许多仙鹤在芦苇丛间或飞舞或静立,美极了。这是画册中一幅标志性的照片,但却是通过电脑合成的照片,是在本地现存一个最大的芦苇湖的写实照片的基础上,通过电脑合成技术,加入了仙鹤而制造出来的。但我相信这美丽一景曾经无数次地在我的小村庄子的旁边出现。那个村庄沉入芦苇丛的时代应该是产生神话或者传说的时代。农民们对苍鹭的称呼虽然缺乏美感,却直接、真实。苍鹭在人们的身边可以毫无戒备完全放松地静立成一截木桩,这显示出一种人与动物完全和谐相处的状态。现在,这种状态也许只能到传说中去寻找。人们还允许鸟儿和我们以伙伴的形式共处吗?
二十几年前,在我小的时候,湖泊已经大面积减少,大部分湖泊被改造成为田地。村庄和田野组成了灰黄的天空,湖泊是上面灿烂的星星。肥美的湖泊变成了贫瘠的土地,土地碱性很大,出产粮食很低,这使我们的这个村子里的人付出同样甚至更多的的劳动,收获的粮食却比其他生产队里的少很多,这造成我们比周边的人们的生活要贫困一些。硬性地改造自然给我们带来的是艰辛和贫困。那时还间或有野鸭之类的飞禽飞过我们的村庄,落入芦苇丛中。每到这个时候,一个叫老葛的人就开始背上他的砂枪向鸟儿落脚的芦苇湖潜行,第二天,他的餐桌上就会出现一两样野味。鸟儿在人们眼里不会再是伙伴的关系,而是被利用的或者满足欲望的对象,动物对人不得不始终保持戒备和远离的状态。动物的远离让人们只好自己给自己做伙伴,但是这个伙伴关系也逐渐变得有待商榷。人和人之间更多地充满了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即使是见面亲切地像亲人一样,心底里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疏离和小心。尤其是在人群集中的城市里,几乎所有人不得不保持着对人的一种猜测和防备心理,在复杂无比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小心翼翼地探寻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小路,所以不得不时时绷紧那一根心弦,疲惫的感觉过多过早地爬上了年轻的心灵。芦苇遍布时代那种完全放松融入自然的感觉该是多么让人怀念和向往呀。
现在,当芦苇丛像记忆一样远去、稀薄乃至消逝,看芦苇该去风景区里面看了。这让我格外怀念芦苇融入我们的生活的日子。芦苇的气息和精魂坚挺地留在了我的记忆的深处,乃至融入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