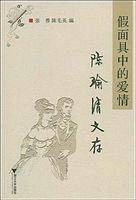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臻于完美的短篇
至20世纪90年代,门罗的个人生活早已安定,她和弗兰姆林的关系非常和谐牢固,两人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弗兰姆林的家乡克林顿,距离门罗的家乡也不远,冬季则会至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的一个小镇康莫克斯度假,那里气候温润,门罗和弗兰姆林常常一起滑雪。门罗的二女儿雪拉恰好也住在距离康莫克斯镇不远的另一个小镇。雪拉于1990年结婚,很快就有了两个孩子。升级为外婆的门罗很乐意常常去女儿家探访照料,享受天伦之乐。这一时期门罗也发展了新的个人爱好。在克林顿居住的日子,门罗最喜欢去附近的剧场客串演出,自得其乐。传记《艾丽丝·门罗:书写她的生活》中援引了一次有趣访谈,门罗这样谈论自己参与的两场表演:
“在其中的一个剧中——两个都是谋杀悬案——我是一位日渐衰老却风韵犹存的英语教授……在另一个剧中,我演的是一个女作家。她走进图书馆去找那里有没有她的书。我真的很喜欢。”当记者问她,既然她是出了名地不喜欢为她的写作抛头露面,为什么她还会喜欢演戏呢?门罗的回答非常耐人寻味:“呵呵,那是因为做宣传的时候,我必须成为我。而演出的时候,我喜欢有面具。”
门罗似乎严格地将她的公众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作为普通人的门罗乐于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而写作似乎也只是她的个人爱好之一而已。她不再需要为经济压力而写作,也不再需要为时间压力而挣扎,在写作中她回顾过去的生活并升华人生的感悟,表达对现实的洞悉并对未来寄予期许。
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与自然的状态下,作为作家的门罗真正进入了创作的盛年。门罗基本以三年一本的速度稳定地推出新作,同时也是《纽约客》以及各类文选集的常客。此时的门罗已经被评论界公认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我们这个时代的契诃夫”更是广为流传。这句话最早出现在美国版《我年轻时候的朋友》的书封上,是作家辛西娅·奥兹克为门罗写的推荐语,一经提出便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这个评语也成为了《公开的秘密》美国版与加拿大版封套上的标志性推荐语。《公开的秘密》出版于1994年秋天,收录了包括《阿尔巴尼亚处女》、《公开的秘密》、《荒野车站》等八个短篇。至1995年1月《公开的秘密》加拿大版的销量已经接近4万册。同在1995年,门罗因《公开的秘密》获得了英国W.H.史密斯文学奖,奖金高达一万英镑。同年9月,门罗再次获得了5万美元的莱南基金会文学大奖。创立于1989年的莱南文学奖旨在褒奖“作品质量超凡”的作家。这次获奖也被认为是对于门罗整体创作水平的肯定。除了加拿大版、美国版与英国版,《公开的秘密》随即也出版了法语版、德语版、挪威语版以及西班牙语版。这一时期门罗之前的大多数作品也都拥有了各种语言的译本,譬如说,《我年轻时候的朋友》虽然还没有挪威语版,但是却有了丹麦语版、荷兰语版、瑞士语版以及日语版。据统计,至1996年,门罗的作品总计已被翻译成13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欢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门罗作品精选集》的出版计划被提上了议程。1995年出版的精装本《门罗作品精选集》的主要受众为美国和英国的读者,他们大都在80年代才开始阅读门罗,对作家之前的作品依然有着旺盛的购买需求,当然,精装本也满足了加拿大本土读者收藏门罗的热情。《精选集》共收录了29个经典的短篇作品,其中,有4个故事出自《快乐影子之舞》,3个故事出自《我曾想对你说的事》,4个故事出自《你以为你是谁?》,6个故事出自《木星的月亮》,5个故事出自《爱的进程》,3个故事出自《我年轻时候的朋友》,4个故事出自《公开的秘密》。虽然都是门罗已成集出版过的作品,《精选集》的意义在于,它是对门罗文学成就的一次致敬。评论家们也毫不吝啬溢美之辞,大量的书评同时出现在加拿大、美国与英国的重要报纸与杂志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英国作家A.S.拜厄特在《环球邮报》上的书评。同为作家的拜厄特是不择不扣的“门罗迷”,她在创作《占有》时,显然借鉴了相似的现实表现手法。在她的书评中,拜厄特是这样开篇的:
艾丽丝·门罗是一位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她足以与契诃夫、莫泊桑与福楼拜三人比肩,其创新性与启发性不相上下。她的作品完全改变了我对于短篇小说的成见,同时也在过去的十年间影响了我自己的创作方式。
她的故事是纯粹加拿大的故事,扎根于特定的土壤与社会,描绘细致入微,刻画栩栩如生,一个外国读者读后也会感慨故事中的那些人物与环境是如此地准确无误。(很多本地优秀的作家都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种艺术转化。)她是作家中的作家——这句话我已多次强调,的确语义双关、非常恰当——不过任何人都可以读懂门罗,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被意想不到的故事所震撼。
拜厄特尤其强调了门罗典型的叙述方式:
即便是在她写作生涯的最初阶段,她也几乎没有写过传统的那种“结构结实”的小说。她的故事是片段性的,时空颠倒的,启示性的,但是它们通常能在很短的篇幅中表达出一种整体性,一种完整的生命体验,并指明背后所蕴含的哲理。
门罗作品的哲理性思辨在《好女人的爱》这部作品表现得尤为突出。《好女人的爱》出版于1998年秋天,至1999年6月已经再版5次,销量超过6万册,同时获得了当年吉勒文学奖与总督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赢得了吉勒文学奖。作品包括了《好女人的爱》、《孩子留下》、《我母亲的梦》等众多名篇。作品中,伦理问题成为这一时期作家最主要的关注点。事实上,在整个90年代,健康问题,尤其是心脏问题,是门罗生活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困扰。《我年轻时候的朋友》出版不久,门罗就曾做过一次手术。上了60岁以后,门罗又再次做过一次心脏手术。正是因为这种衰老和死亡的威胁,使得作家能够以更加成熟的心态去考量生命中的两难选择,同时对于伦理的是非观做出反思。这个集子中的很多作品同样带有强烈的自传成分,例如《孩子留下》中抛夫弃子去找寻快乐与价值的中年母亲,《我母亲的梦》中那个挣扎在艺术家的理想与母亲天职的矛盾中难以取舍的年轻妈妈。在类似的伦理困境中,简单的“对”或者“错”并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反而凸显了道德的含混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拜厄特在《环球邮报》上为此特别撰写了第二篇门罗书评,指出诸如《孩子留下》之类的作品,是“含混”的绝妙例子,孩子不会永远留下,他们会长大,会离家寻找他们自己的空间,但同时对母亲宝琳而言,她若想寻求自我,就必须同时割舍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的孩子永远留下了。拜厄特同时感叹门罗在故事叙述上对于时间的处理也相当复杂精巧,“可能只有另一位作家才能真正体会到引导与控制叙述节奏是多么地困难”。
就《好女人的爱》一书的出版,另一篇重要的评论文章则强调了门罗作为作家的加拿大身份。阿丽莎·凡·贺克在《加拿大论坛》上指出,门罗的天才与成就主要是通过《纽约客》这份美国杂志得以“墙内开花墙外香”。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和门罗过去的小说集一样,《好女人的爱》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已经在《纽约客》上单独发表过,《纽约客》几乎成为了衡量所有加拿大作品优异与否的一个权威标准”。如此的状态当然是有着复杂的历史与文化原因的,但是凡·贺克提出:“是否门罗的作品印证了一种感觉,即加拿大文化中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是源于50年代的。”阅读门罗就好像翻开了一本关于50年代的黑白影集,“她的故事表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疆土,是我们所共同参与其中的空间”。总而言之,凡·贺克在文章的最后总结:门罗的作品是“加拿大自我意识的标尺”。
门罗这一时期继续源源不断地在《纽约客》发表新作。与之前的作品相比,故事的篇幅显著增长,这也给《纽约客》杂志制造了一些“甜蜜的烦恼”。之前《纽约客》好不容易找到了足够的版面发表门罗的《好女人的爱》(近80页),后来却不得不割爱放弃了《恨、友谊、追求、爱、婚姻》(50多页)与《法力》(60多页)。那篇与《纽约客》遗憾地擦肩而过的作品《恨、友谊、追求、爱、婚姻》最后成为了门罗下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同名开篇故事。短篇集《恨、友谊、追求、爱、婚姻》出版于2001年10月,当月中旬便登上《环球邮报》的畅销书排行榜,到次年1月的时候,单加拿大本土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3000千册。11月份同时还出版了美国版与英国版。三地的评论界也反响热烈。在加拿大,布朗温·德莱尼在文学评论杂志《纸与笔》上这样写道:短篇《恨、友谊、追求、爱、婚姻》是其中“最发人深省的一个故事”,几乎可以用“冷酷无情的年轻女艺术家的画像”来概括,代表了“作者之困境与作者之魔咒”。“要想有独创力,就需要自私自利,但如此一来,作者就与她最爱与最在乎的人被迫隔离了开来。”而莫娜·辛普森则在美国的《大西洋每月评论》上指出,门罗就如同是“成年人观看儿童在幼儿园的嬉戏那样,描绘着笔下的男男女女。她从来都不做评判”。同时,辛普森还指出其中的《家庭装潢》既有强烈的自传成分,也是作家的虚构性再创作。劳瑞·穆尔同样在《纽约书评》中认为《家庭装潢》是门罗新作中最优美有力的作品,它探讨了“作为一个作家,如何为了精神的自由而不得不承受感情创伤”。这个故事:
表达了作家如何在生命中不得不舍弃某些东西,从而超然于普通人的情感之外,以便能换得作家的生命力。这个短篇是作家夹杂着宽慰与羞愧的心灵之歌。门罗忠实无误地捕捉到了作家这种含混的心理状态——她并没有想做任何的道德评判,而只是顺从地去接受……《恨、友谊、追求、爱、婚姻》作品集最终进入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大奖的决选名单,并获得“加勒比海与加拿大地区”英联邦作家奖,以及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同年门罗获得“瑞短篇小说奖”。
2003年,一本新的门罗作品精选集《爱的迷失》由新加拿大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共计430页。第二本精选集强调了门罗作为经典作家的地位与号召力,其中的故事编排独具匠心,并没有按照原有故事的写作与出版顺序,而是以主题发展的顺序,突出展现了门罗的创作理念,即打乱时空,强调“生命的存在感”。同时,《纽约客》也以高密度的刊发频率以及门罗专辑向门罗致敬。在2004年的6月刊上,《纽约客》一反其惯例,即同一期杂志只刊登同一作者的一篇作品,而是推出了一期门罗特刊,在同一期上刊登了《机缘》、《匆匆》与《沉默》三个短篇,总字数超过3万字。并且,在此前的3月刊,《纽约客》刚刚刊登过门罗的《激情》;而在随后的8月刊上,《纽约客》继续刊登了门罗的《逃离》。门罗所享受的这种频率与待遇,也是在《纽约客》杂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那年在《纽约客》刊发的那些故事后来统统都被收录进了门罗新的短篇集《逃离》。
2004年9月,《逃离》加拿大版出版,初次印刷了4万册,至当年11月,美国版出版,则一口气发行了10万册。《逃离》再一次在评论界获得了热烈的反应。加拿大的各主流报纸杂志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长篇的评论文章,菲利普·马常德在《多伦多星报》上指出,“门罗的语言精准,具有无可比拟的控制力”,“她标志性的叙述手段”复制出栩栩如生的场景,而最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直击读者的内心”。《国家通讯报》则评论说:“门罗作为短篇小说家所创造的奇迹之一就在于她能够让她的读者感觉和作品中的人物惺惺相惜,甚至作品中的人物比他们的家人还要熟悉。”乔纳森·弗兰泽则在《纽约时代书评》中以整整四页的篇幅介绍门罗。弗兰泽在开篇强调:“门罗被认为是目前北美最好的作家,在加拿大她的作品销量总是高居榜首,但是在加拿大以外的地区,她的读者群依然不算庞大。”弗兰泽这里主要以美国的销量标准来衡量读者群的大小,正确与否尚有待商榷,但是弗兰泽显然注意到了门罗作为短篇小说家的边缘性身份。无论如何,正如弗兰兹所承认的,仅创作短篇小说的门罗还是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自己主流作家的领军地位。《逃离》最后在加拿大销售了72000册精装本,6万册平装本;在美国销售了10万册精装本,超过20万册的平装本,在英国的精装本略少,为8000册,但是平装本超过7万册。这是一个绝对不输于任何一个优秀的长篇小说家的销售数据。《逃离》同时获得了当年的吉勒文学奖,这也是门罗第二次获得吉勒文学奖。门罗证明了自己是名符其实的“当代的契诃夫”,她的短篇小说女皇的地位确实牢不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