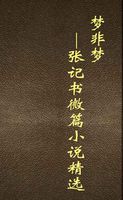最可笑的是,我这句格言我知道,只是出于害羞,犹豫着不愿告诉这个滑稽的家伙,仿佛这是我一生纯粹的秘密。最后实在顶不住了,我真的气得直发抖,用失真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我们每个人都要表演。”
他惊愕地看着我,终于松开了我的纽扣。
“好啊,成啦!孩子。”他嚷道(他比我大得多),“表演吧。”
对这句“格言”如果不稍作解释,我的确就显得太蠢了。尤其当时它专横地支配着我的思想,简直成了新的主宰。直到这时我据以生活的道德观,近来让位给了我还没弄得太明白的某种更绚丽多彩的人生观。我开始觉得,义务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上帝本人很可能对这种千篇一律也感到厌恶;造化就反对千篇一律,但基督教的理想却似乎力求千篇一律而压抑天性。我现在只接受具体的道德,这种道德有时会提出相互对立的绝对必要的要求。我深信每个人,或者至少上帝的每个选民,都要在世间扮演某种角色,确切地讲就是他自己的角色,与其他任何人的角色是不相同的。因此任何让自己服从于某种共同准则的努力,在我看来都是叛逆,不错,是叛逆,我将之视为反对圣灵的这样一种“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因而使个人丧失了自己确切的、不可代替的意义,丧失了他那不可复得的“味道”。我在我当时所记的那本日记的题词中,写了不知从哪儿来的这句拉丁话:
人类特有的使命,就是完全承诺始终给予可能的智力以充分的动力。
的确,我被开始呈现于我眼前的生活的多姿多彩陶醉了,也被自己的变化陶醉了……不过我决意在这一章只谈他人。现在再回头来谈吧。
贝尔纳·拉扎尔真名为拉扎尔·贝尔纳,是出生于尼姆的犹太人,个子倒不算矮小,只是又粗又短,其不讨人喜欢难以言喻,一张脸只看见腮帮子,整个上半身只看见肚子,两条腿只看见大腿;透过单片眼镜,他对人对事都投以尖酸刻薄的目光,仿佛他对所有人和事都不欣赏,都极端蔑视。他心里充满最高贵的情感,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对同时代人的粗俗野蛮和荒淫无耻感到义愤填膺。可是,他似乎又需要粗俗野蛮,只是通过强烈的反衬才意识到自我,义愤填膺一旦减弱,就只剩下反光了。他正在写《传说的殷鉴》。
拉扎尔和格里芬将他们好斗的性格结合在《政治和文学对话》之中。这本封面为深红色的小刊物,说真的编写得倒是挺不错的。我那篇《论那喀索斯》发表在上面,令我欣喜异常。我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地缺乏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在许多情形下是胆大的基础,亦即是对自己在别人思想上的信誉的直觉。我所追求的总是低于我应得的份额,不仅什么也不懂得索取,而且对人家给予一点点东西感到荣幸,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喜。到了知天命之年,这无疑是个弱点,可是我才刚刚开始弃旧图新。
贝尔纳·拉扎尔令我感到担心。我本能地感到,他身上存在着可能误入歧途而又与艺术毫不相干的因素。这种感觉大概不止我一个人有吧。它不至于使齐亚尔和埃洛德与拉扎尔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都持同类的意见,免不了要走到一起去,但至少使雷尼埃、路易和我与他保持距离。
“你注意到雷尼埃善于掌握分寸吗?”路易对我说,“那天他差点儿情不自禁把拉扎尔完全当作伙伴了。可是正要去拍拉扎尔的膝盖时,他控制住了。你没看见他的手停在空中?”
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法国军官,犹太人,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引发要求释放他的政治风波,即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后经重审,德雷福斯被平反昭雪。发生时,拉扎尔准备投入战斗,担当了众所周知的重要角色。我们顿时明白了,他找到了自己的路线。而直到此时,在文学上他只是在候见室里等待接见,正如其他许多人终生所做的一样。
阿尔贝·莫凯尔我还没有提到过,他领导着一个小小的但重要的法语比利时语刊物《拉瓦洛尼》。在一个流派之中(我们的确形成了一个流派),由于相互切磋琢磨,每个人的审美观都有所克制,变得高雅,因此我们之中很难有一个人会犯判断错误,要么至少这个错误会是整个流派犯的。除了这种集体的审美观,莫凯尔还有着非常精辟的艺术见解,甚至精到纤毫必究。与他这种精细的思想比较起来,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思想未免鲁钝而粗俗马拉美谈到一位非常高雅的夫人时说:“我对她说‘你好’时,总感到是在对她说‘他妈的’。”。他的谈吐之精妙十分罕见,而且充满精细的暗示,你非得踮起脚趾尖跑才能跟得上。交谈因为过分诚实,一丝不苟,所以通常是一种令人晕头转向的说明,谈到一刻钟,你就会忍受不住了。他此时正在写他那本《略显天真的弹词弹词是中世纪一种半诗体半散文作品。》。
以上这些人我每周要在埃尔迪亚家、马拉美家或别的地方会见好几次。除了他们之外,我经常交往的人之中,还有一个可怜的小伙子,我不敢明确地称为朋友,但对他充满一种特殊的情谊。这个小伙子就是安德烈·瓦克纳埃,一位博学的文人的孙子。多亏这位文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出色的《拉封丹传》。小伙子体弱多病,禀赋聪颖,当然了解他无法获得的东西之可贵,但造化只给了他一副悦耳的嗓子,即仅够他抱怨所必需的东西。他在巴黎文献学校毕业后,即在马扎利纳当图书馆助理管理员。他与我的德马勒斯特姨妈有相当近的亲戚关系。在姨妈的安排下,我在一次晚宴上遇见了他。那时我还没写完《安德烈·瓦尔特手册》,即还差一点才满20岁。安德烈·瓦克纳埃大我几个月。他的殷勤和对我的关注立刻博得了我的喜欢。为了不欠情,我想象在他身上发现了与我模模糊糊计划写的一本书的主人公,有非常相似之处。那本书的题目拟为《情感教育》。不错,已经有一本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但我这本书更切近题意。当然,瓦克纳埃很兴奋,爱上了我打算描绘他的这本书。我问他是否愿意来给我摆姿势,就像给画家摆姿势一样。我们约定了日期。这样三年间,凡是我在巴黎的时候,每周三下午两点到五点钟,安德烈·瓦克纳埃都来我家里给我当模特儿,除非我去他家。有时我们把时间延长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不知疲倦地、滔滔不绝地闲聊。普鲁斯特著作的文本最能使我想起我们山南海北的闲扯。我们无聊地议论一切,大钻世事的牛角尖。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不这样想,因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精辟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不经过吹毛求疵是不可能得到的。我说了可怜的小伙子身体很不好,他脆弱的体质不患哮喘,就会全身生满湿疹。看见他那样形容憔悴或听见他喘息不止、哼哼唧唧,真叫人可怜。他也因为写作的欲望而悲叹,可是他什么也做不来,只有在思想上可怕地折磨自己。我听他倾诉自己所遭受的挫折和自己微弱的希望,显然没法安慰他,只不过表现出有兴趣听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而让他感到有理由生活在这世界上。
他让我认识了一个比他自己还可怜的人。这个人的名字我不会说的,就叫他X吧。他那身体非常单瘦,只能在各家沙龙里展示他那身剪裁得无可挑剔的衣服。你与他一起去上流社会,会惊异没有看到他,连衣带人整个儿给挂到衣帽架上。在家家沙龙里,他那部琥珀色柔软光滑的长胡子后面,发出幽灵般的、非常悦耳的声音,柔声柔气地说一些乏味得不能再乏味的平凡琐事。他每天饮茶的时候才外出活动,奔走于上流社会,在那里充当小广播、传声筒、和事佬、旁听者。他不断把我带到瓦克纳埃也经常出入的这样一些地方。幸好,我身上没有任何特点,会使我在上流社会非常引人注目。我误入歧途地迈进一些沙龙,在那里显得像只夜鸟。不错,我所穿的剪裁相当好的礼服、我长长的头发、竖得高高的衣领、欠身的姿势,都引人注目,但我一说话就令人失望。我的头脑很迟钝,至少是根本不会推销自己,所以我不得不保持沉默。每当要开玩笑时,无论是在波雷夫人家、拜涅尔夫人家(这位夫人一点也不蠢),抑或在丁·子爵夫人家(——啊,X先生,她大声说,给我们朗诵苏利·普吕多姆的《摔碎的花盆》吧。她经常说错别人的称谓和姓名,例如谈到她对英国大画家JohnBurns的仰慕时,可能说成Burne—Jones。),总之每当要开玩笑时,我总是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
在乌卢索夫王妃府上,大家兴致更高,至少都挺开心,谈话无拘无束,最疯狂的人受到最热情的接待。王妃有着丰满的美,一身东方式的打扮,态度和蔼可亲,说话滔滔不绝,看上去对一切都感到开心,能立即使每个人都不感到拘束。交谈疯疯癫癫,有时显得荒诞不经,人们不免怀疑,某些非常粗鲁的话,女主人是否真的听不明白而上当。不过,她总是保持着一种天真、真诚的态度,使人家不好意思一味地冷嘲热讽。在一次盛大的晚宴上,当穿号衣的仆人端上美味佳肴时,大家突然听见她用次女低音冲他喊道:
“你那个肿块怎么样啦,卡西米尔?”
不知什么鬼促使我,有时我单独与她呆在一块,会突然揭开她的钢琴,开始弹奏舒曼E调《新事曲》。这时我无法弹出应该弹的节奏。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她对动作的批评非常准确,和颜悦色地指出几个错误,显示出她对这首曲子完全熟悉和理解。而后她说:
“你觉得我这架钢琴好,就来这里练吧。你会使我感到愉快,又不会打扰任何人。”
那时王妃刚认识我,这个建议令我感到窘迫,而不是让我感到适意。因此我没有接受。我作为例子提及这件事,是为了说明王妃不假思索的可爱的处事方式。但大家经常悄悄议论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所以我在她身边呆的时间长点儿,就担心她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真正的精神错乱。
有天晚上我带王尔德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爱尔兰作家、诗人、戏剧家,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为艺术而艺术”的倡导者。去她家,出席亨利·德·雷尼埃在什么地方描述过的那次晚宴。席间,王妃突然大叫一声,宣称她刚才看到这个爱尔兰人的脸四周有一个光环。
也是在她家的另一次晚宴上,我认识了雅克-艾弥尔·布朗什——在这一章里我唯一点出姓名的仍在交往的人。但关于他有那么多事情要说……关于梅特林克梅特林克(Maurice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马塞尔·施沃布和巴雷斯巴雷斯(MauriceBarres,1862—1923),法国作家、政治家,以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倾向给同时代人很大影响。,我也留到后面去描述。我一脱离童年,就迷失在这片黝黯的热带雨林里。也许我已经使它的氛围,也使我游移不决的憧憬和我对热忱的寻觅,太过沉重了吧。
我将这本回忆录给罗杰·马丁·杜·加尔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MartinduGard,1881—1958),法国小说家,剧作家,193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帝波父子》。看,他责备作品总是说得不够,让读者感到不满足。然而我的意愿一直是什么都说。不过,吐露隐情要有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得做作、勉强了。我追求的主要是自然。我思想上大概希望使整个描述更加清纯,所以写得过分简洁。描述不能不有所选择,最棘手的是,乱糟糟同时发生的情况,却要写得似乎是相继发生的。我是一个爱自言自语的人。我内心的一切都在相互争吵,相互辩论。回忆录永远只能做到半真诚,不管你多么关心真实,因为一切总是比你说出来的更复杂。也许在小说里更接近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