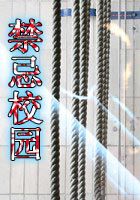员工开饭时,老乌就在饭堂里忙进忙出,看到厂长和李彩凤坐一起吃饭,心里掠过一丝遗憾。倒不是因为李彩凤,而是时间久了,厂子里渐渐就有了多对情侣。王一兵和一文员相好,每天吃饭在一起,下班后一起在厂里打羽毛球,或一起去瑶台逛市场。好几个机修,也都在和同厂的妹仔谈恋爱。瑶台厂女工多,男工少。三百多号人,男工不到二十,除老乌、李钟二人,几乎所有男工都有恋爱对象,吃饭时皆成双成对,如胶似漆,这对老乌是个不小的打击。他已近而立,若是在家,这个年纪尚未婚配,基本上就要纳入老光棍的预备队了。之前老乌独身,是因工作没什起色,自然心不在此,如今有了这份体面工作,在工人中又有不错口碑,难免会触情而生温情,饱暖而生淫欲,操心终身大事了。有时,他会拿出当年阿霞给他买回的笔记本,看他写下的话,怀想阿霞的容颜,但已难想起阿霞的样子,便有了沧桑之感,时作情何以堪之叹。然而,他工作再出色,厂子里男女员工比例再失调,依然没有另外的一个阿霞出现,老乌便越发念阿霞的好。在宿舍里,又写了幅字: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老乌的心思,被李钟瞧出了。李钟笑老乌没出息。说:“我比你还大俩月,我不也没有女朋友吗?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趁当总务的机会狠狠捞一把,有了钱,自己当老板,到时什么样的美女找不到?”
老乌说:“我没有你这样的野心。再说,我到哪里去捞一把?”李钟说:“对兄弟我还不说实话?把着这么好的肥差,每个工人的餐费里每天捞一毛钱,三百个工人,一个月就是九百,捞两毛,就是一千八。瑶台厂还要进人,开过年,最少有五百人,这笔账你还不会算?”老乌说:“不是不会算,我的账记得清清楚楚,真是一分钱没捞。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黄叔对我这样好,我再捞他的,那还是人呀?再说,我要是捞了,工人的伙食就差了,都是打工的,这样的缺德事,我做不出。”
李钟说:“得,算我没说,真是个死心眼。你知道有句话怎么说吗?三年总务头,一幢小洋楼。你现在就是总务头。说实话,如果让我在当总务和当厂长里选一个,我想都不想就选总务。从打工仔起家,后来做老板的,多是业务和总务出身,你知道为什么吗?”
老乌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李钟说:“跑业务的,长期和客户打交道,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业务网,哪个还甘心当打工仔?因此业务员出身的老板特多。”
老乌说:“那当总务的呢?”
李钟说:“当总务的,主要是靠吃回扣,报假账,挖了第一桶金,再肥的差使也看不上了,不如自己当老板来得痛快,因此总务出身的老板也多。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跑业务出身的,多开工厂做实体,当总务出身的,多开公司做贸易,这其中奥秘,大有文章哪。”
李钟一席话,听得老乌目瞪口呆。李钟说:“不过你这样也好,赚一份安心钱。哥也给你算个命,如果你这性格不改,这辈子,别想发财。遇上黄总这样的老板,还有你一口饭吃,遇上不上路的老板,你就等着瞧吧。”
老乌说:“那我就永远跟着黄叔。”
李钟说:“别黄叔黄叔地叫,多肉麻呀。你以为黄总真是对你好呀,他对你好,还不是因为你有价值。哪个老板的第一桶金是干净的?就说黄总,他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提高工价?为什么我们加班加点干活不发加班费?为什么星期天没得休息?为什么他明知道天那水有毒会致人得病,却不和工人明说?”一连的几个为什么,把老乌问得哑口无言。李钟最后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作结,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肮脏的东西。”
老乌从前没想过这样的问题,细细一想,黄叔的财富,除了他自己苦心经营外,还真是靠榨取打工者的血汗慢慢积累的。这才几年时间,老板的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在迅速增长,可是工人的工资却一直没增加。老乌觉得李钟比他活得清醒,也活得实在,而他呢,一直生活在自己建构起来的想象与温情中。老乌想,如果让他选择,他还是愿意选择这样稀里糊涂心安理得地生活:“李钟太聪明,太多想法,也太偏激,”老乌想:“李钟这样的人,将来是要吃亏的。”
老乌的这个预感,果然为现实所印证。事情的起因,是湖北帮和两广帮之间发生的那次斗殴。此事发生,起因看似简单,深究起来,却是由来已久,不过是借个机会,来了一次爆发。原来,瑶台厂食堂的几个厨房佬都是广西人,打菜时,自然对两广人要好些,同样一勺子下去,区别还是蛮大的,见到广西人来,勺子就往肉多的地方去,见到外省人,勺子里偶尔舀了两片肉,还要抖掉一片。时间长了,工人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那会儿,工人的确是欠肉吃,因此外省人对厨房佬深为不满,也有人把这意见向老乌反映过。老乌去过问了,厨房佬一句话就把老乌噎了回来:“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打菜哪里能打得那么准?有本事你打几勺子我看看。”老乌说:“不用打,你们心知肚明,谁都不是苕佬。”这样说上一次会好上两天,不说又不灵了。老乌也没办法,他不可能每次打饭都盯着厨房佬,除了对他们讲“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这些道理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正是因了这长久的积怨,到了一定时候,借一点星星之火就爆发了。
引爆斗殴的原因其实小得不能再小,一个湖北妹对厨房佬说给她多打点菜,说前面的韦细妹为什么打那么多肉,到了她这里一片肉都没有。厨房佬不耐烦地拿勺子敲着盛菜的铝盆喊:“下一个。”跟在湖北妹后面的,恰好是两个广西仔,他们急着想早点打了饭去打汤,去迟了,汤里就什么也捞不着了。因此就用粤语骂湖北妹:“丢你老母个嘿!”其实也算不得骂,两广人说话,父子兄弟间,这样“丢”来“丢”去是常事,但在外省人听来,肯定是骂人,而且是极为难听的骂。湖北妹没打到肉,本就窝火,又有人拿白话骂她,还推了她一把,于是就呆在打饭窗口不走,说是要讨个说法。老乌那时还在维持打汤秩序,不知这边发生的事。站在另外一排的,有个湖北仔,见有人欺负老乡,趁广西仔不注意,拿手中的饭碗,往广西仔头上一记猛敲,敲毕,手迅速收回,装着无事一样。广西仔捂着头大骂:“丢你老母!”问是哪个打的,身后有广东仔看得真切,拿手悄悄指向敲他的湖北仔。广西仔个子虽小,人却赤躁,跳过去冲打他的湖北仔就是一拳。饭堂里顿时炸开了锅。老乡帮老乡,很快就形成了两派,一拨湖北人,一拨两广人,拳脚相向,打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转眼功夫,已是稀里哗啦不可收拾,老乌再出来干涉已不起作用,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老板不在厂里,黄小姐来了也不管用。老乌知道,只有黎厂长和李钟能管住大家,去寻李钟不见。原来李钟见打起来,有心让他们打,论打架,两广人个子瘦小,湖北人身高力大,断不会吃亏,因此溜到车间,抓了扳手假装修机器。等这边黎厂长赶到食堂,再怎么叫也没能制止住,李钟心下得意,看看打得差不多了,再打下去会出大事,这才拿着扳手,又抓一块满是油污的纱布,搓着手,慢慢踱到饭堂。急得跳脚的黄小姐见了李钟,如同见了救星,喊:“李主管,你快来,他们打起来了。”李钟不慌不忙:“怎么就打起来了?”黄小姐说:“你先别问那么多,快把他们劝住。”李钟就跳到一张桌子上,大喊住手。李钟嗓门大,这一喊,大家都听见了,湖北帮的人见李钟喊停,况他们又占了上风,见好就收,自然就停了,两广人处于下风,再打下去要吃大亏,也巴不得有人来制止,因此也停了。李钟自然是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事情最后的处理结果,把厨房佬和拿碗敲人的湖北仔炒了,厂里出钱给受了伤的买药包扎。那个起先骂人的广西仔变成了熊猫眼,身上也受了些拳脚,后来几天,被工人戏称为“小乌”。两广人说要报治安队,黄叔说:“你们要是报治安队我就不管了,你们自己处理。”两广人这才罢休。老乌因此被黄叔狠狠训了一通,说:“这事你要负首要责任,厨房佬做事不公,你身为总管,就该报告给黄小姐,把他炒掉就完事了,这事幸亏没有闹大,闹出人命,你负得起这个责吗?”缓一口气,又说:“老乌呀老乌,叫我说你什么好呢,你就是一个老好人,总怕得罪人,可是做管理,是不能总当老好人的。”一席话,说得老乌也自觉责任重大,惭愧无比,低了头,说:“黄叔,要不您罚我吧,罚我的款,撤我的职,都行。”黄叔说:“罚款有什么用?我是教你怎么当一个管理人员。管理管理,一个管字,一个理字,把人管好,把事理顺,就成了。不是让你去当杂工,当煮饭婆,什么事都亲自去做,那要你这个管理人员干啥?”老乌后来细想,黄叔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依然做不来,老乌有些悲哀地想,看来,自己不是做管理人员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