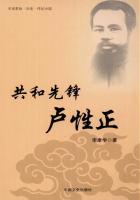庄敏柔声应着,将小手轻轻放入胤禩掌心,二人若无旁人般恩爱着,并肩离去。
宛秋欢笑一声,挽住毛氏的胳膊,笑吟吟道:“灵儿,我难得见一回毛姨娘,今日少陪了,改回再和你叙话!”说罢,像是小鸟般依着毛氏,坐到亭前一丛花树下,倾谈起来。
弘旺叹息一声,深深地看了一眼呆若木鸡的张氏,两眼空泛,一言不发。
慕灵福身道:“旺阿哥、张姨娘早些歇息!慕灵告退!”二人并无反应,慕灵只得讪讪离去。隐隐地,风吹来弘旺的一句话:“既知她容不得你,何必多言惹她不快呢?”慕灵脚步一滞,心中疑云顿起。
很快,慕灵从佩儿那得到了全部答案。
宫中有规矩,皇子大婚前,会指定年长使女教导房中之术,毛氏便是内务府安排给胤禩的第一个女人,换言之,庄敏入府前便已有了毛氏的存在。庄敏嫁给八阿哥近十年,膝下并无所出,八阿哥不纳妾室,连惠妃指的侧福晋都屡屡谢绝。
那张氏原是庄敏的陪嫁丫鬟,春意萌动,起了心思,趁胤禩酒醉之时,**成了他的女人。张氏心计甚重,暂时对庄敏隐瞒了下来,直到庄敏进宫向惠妃请安时,张氏做为随侍婢女,竟然在惠妃面前,声泪俱下,坦言自己已怀上胤禩骨肉。庄敏遭到背叛,恨不得将张氏当场撕成碎片。惠妃等了多年,终于有胤禩骨肉的喜讯,且当时胤禩为太子呼声正高,子嗣更为重要,怎能不重视?惠妃声色俱厉,称若张氏和孩儿有何不测,无论是何因由,便是庄敏这个嫡福晋无法恪尽职守,定向皇上请旨休了庄敏。庄敏怒气冲冲地回到八阿哥府,与胤禩发生了婚后第一场冷战。胤禩苦恼,十年无子,他已成为京中的笑话,执着与庄敏“一世一双人”的承诺,为纳妾一事得罪了不少人,换来的是庄敏的无理取闹、针锋相对。赌气之下,胤禩唤来多年不见的毛氏侍寝,没过两个月,大夫也诊出毛氏喜脉。相较康熙、惠妃大喜,庄敏却是夜夜以泪洗面,那个时候,只有蒋嬷嬷和红儿多番鼓励、规劝庄敏,胤禩身为皇子,怎能无后嗣,张毛二女解了此忧,往后惠妃就不会以此为借口强迫胤禩纳妾。庄敏切不可疏离了胤禩,给其他女子有空子可钻,庄敏这才与胤禩重归于好。
毛氏才貌平平,平日里对庄敏多加恭迎、放低做小,从不以资历有任何狂妄。诞下宛秋后,已是心满意足,素颜简装,看起来与蒋嬷嬷差不多年岁。庄敏并非不知好歹之人,只要毛氏不逾雷池,她对其母女也颇为照顾。
那张氏却心心念念着母凭子贵,不顾庄敏订下的规矩,常常私会弘旺,哭诉自己对庄敏的怨怼,甚至四下传播庄敏身体隐私、闺中秘闻,刻意诋毁。张氏随庄敏嫁入阿哥府,她的话自然十分有力,一时间,堂堂嫡福晋竟成了合府奴才的笑话。可想而知,庄敏得知此事时,脸色会怎么样?原本胤禩要给张氏的庶福晋位份,换成了一顿杖刑。皮开肉绽的杖刑,让张氏一躺三个月,虽然心怀不满,但表面总算规矩许多。
慕灵感叹不已,扳起手指一算:“姑姑与姑父成婚二十年,仍无所出,但恩爱如新婚,如此情深,实让天下女子羡慕。”
佩儿忙做噤声状:“格格,子嗣一事是府中大忌,万万不可当着福晋面提及。”
慕灵拼命点头,佩儿当下又将胤禩如何疼爱福晋、二人情深意长的事件,絮絮讲了半天。佩儿看着慕灵听得如痴如醉,暗暗松了口气,总算完成了蒋嬷嬷的使命。
次日,佩儿带着襄怜帮着慕灵漱洗,却听到门外传来一阵鬼哭狼嚎。不一会,小安子隔着屏风来报:“格格,王福山在外求见!”
佩儿心中一掂,便知何事,她说:“格格正在洗漱,不太方便……”接着,她对慕灵说:“这王福山原是府中大管事,不知怎么的得罪了八爷,今个儿一早通禀下来,赶他去做洒扫的奴役!格格大可不必理会!”
襄怜骄傲地说:“格格,当真是恶人恶报呢!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得罪我家格格!”
莫非,胤禩是为了她?慕灵心里一甜,红晕飞颊。想起那王福山,也并没有印象中那么讨厌了。于是,她说:“他这般来求我,必是有事。我初来乍到,若摆出架子拒而不见,只怕落人话柄。小安子,请他稍待片刻!”
约摸过了半个时辰,慕灵在正堂见到了跪着的王福山。他全然没有了昨日般的气势凌人、作威作福,一见慕灵便跪行于她身下,磕头不已,口齿不清地念着:“慕灵格格恕罪,奴才狗眼看人低,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奴才吧!”
慕灵淡淡地说:“本格格哪有资格治罪王三爷?您还是到静思斋或琴瑟居求求八爷或福晋吧!”
王福山忸怩道:“奴才在府中伺候十年,深受主子和福晋倚重。他人不知,奴才怎会不知?此次八爷罚奴才,纯粹是因为奴才昨日得罪了格格啊!”
此话正中慕灵下怀,她心神旌荡,羞色满面,不由呢喃道:“真的吗?”
“狗奴才!看来你还不知罪!”一抹月白的身影,闪身进入绛珠楼。
“八爷……主子……”王福山面如土色,噤若寒蝉。
清晨灿烂的阳光投在胤禩身上,月白的长衫束着碧玉腰带,挺拔的身躯散发着成熟的王者魅力。慕灵迷恋地看着那不苟言笑的玉面郎,直到感觉佩儿轻扯她的衣袖,才意识到失礼人前,忙红着脸福身道:“灵儿给……八爷请安!”不知为何,潜意识中,她用了自己的小字,并不想称胤禩为姑丈。
胤禩浑不在意,柔声道:“灵儿不必多礼!”一声灵儿,让慕灵感动地全身酥麻,幸福地差点飞升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