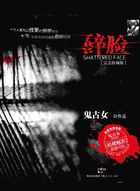1
温伯玉长着一道通眉,许多人便相他命短。他来塔镇教书的次年,当上了小学校的校长,在老师们中间说话很算。
农忙季节到了,平常住校的老师们一上完课就匆匆往家赶,难得有个人陪他在学校过夜,他忍不住这份过度的清雅,就对大家说:
“学校也该有个看门的啦,我们不如把众璞老头儿接来。”
众璞老头儿就是那位刚刚故去的杨校长的父亲,远在泗水乡里。这话说过的后一天,就有一位老头儿身背一副行李卷,跟一位大姑娘相挽着踅入学校里来。
那老头儿满顶银霜,骨格极显健爽,在那里停住,赛如一棵苍松。他大概是要再次辨清一下方位,眼睛正四顾着,却早有一位手执木槌去房檐下敲铁片的老师判他就是杨校长的父亲。那木槌一直地落下去,铁片便嘡嘡地响了,声音首先红红火火地灌进老师的耳朵,很快就由小学校漫入小镇微醺的上空。
在紧接着的一刹间的寂静过后,众多的孩子便骤然出现在老众璞的眼前,并突突如小猪似的向他奔来,躲都躲不及。随他而至的那位大姑娘起先着实惊了一跳,继而也就哈哈地大笑起来。等孩子们从学校里走空了,她依旧笑着,猛看见那位刚才敲铁片的老师正迎面赶了来,也便马上使黑黑的一片巴掌握住了整个嘴。老众璞目示了她一下,就向老师说:
“这是我的孙女小凤。”
那位老师接过他的行李,觉得小凤笑得古怪,也便说她:“你看你,这么大了也不帮帮爷爷。”
他们来到办公室,其他的老师正准备离开,一见了老众璞就都围上去问好,眼里不免暗暗红一回湿一回。他们原来知道温伯玉昨天下午去了泗水一趟,听他回来说老众璞打算用一天时间收拾一下家里,明天才等学校派人去接,没料到他们祖孙俩今天就来了。更让老师们感慨万千的还是杨校长生前从未向他提起过他还有这么一个女儿,在料理他的后事之际才有人看到她,现在她却清清楚楚地立在大家跟前,不能不让人心酸。但是他们又怕老头儿重新难过,竟连安慰一下也不敢了。当下几个人轻轻淡淡地说了一阵子话,就都有些坐不住,心里琢磨外出办事的温伯玉也将返校了,便陆续告辞。
他们一走,只剩下老众璞和小凤置身在桌椅、教具和纸张里面,陌生之感也就悄悄袭了来。
爷爷拉一拉孙女的手,说:“你这孩子,怎么跟看西洋景似的,眼睛睁得有一双牛眼大!”
那小凤刚才在众人的目光中着实地拘束了一回,这时候又自由了,便笑着说:“我是看那些皮孩子,跟个芋头蛋似的。我的两个眼睛都看不过来了。”说着就要伸手去摸身旁桌子上的教具算盘,老众璞刚喝一声“别动!”,她那手早已碰过算珠又退回来了。她说:“我说那子子儿怎么不掉下来,原来是用毛毛绳给穿住了。”这眼睛扑闪扑闪着又去搜索着新奇的东西,忽然又开口道:“那房子檐下的铁皮子一敲怪响,有空我得好好敲敲。”
老众璞说:“你瞧那是敲着玩哪!可不简单!你没见人家老师都对咱好,这里就是教人学规矩的地方,哪像咱家?腿能迈过这门坎可不容易。你想想你爹能比老家的人强出多少!可惜你竟不像你爹。我真得送你进学堂学点心眼子。”
小凤摇着他的胳膊不让他说下去,自己那张嘴却又关不住,嘁嘁喳喳个不停。
祖孙俩这么坐等了半天也不见温伯玉回来,老头儿便渐渐觉出一些凄凉,眼神也开始发呆。小凤不管爷爷听没听,自顾把认为有趣的事情说完,头脑也就马上开始费劲起来,但终归想出了一句,就问:“爷爷,你说我们能不能长住在这里?我是喜欢死了。”老头儿让自己正常一些,告诉她道:“那温校长说过的,咱不想走可以不走。以后你也要少讨人嫌。人家这都是看在你爹的面子上。”这时门一响,两个人掉过头去。脸被晒红的温伯玉正站在门口。
能看出温伯玉已经知道他们来了。他手里带着一些从街上买来的食物,小风立刻嗅出了那种逗人食欲的新鲜香味,肚子里则像打雷一样响。但是在吃饭时,不知是出于太饿拟或胆量突然变小了,她的双手不敢向前伸一伸,只软绵无力地耷拉在身体两侧。她这样出人意料地沉静了许多,令老众璞不由得感到吃惊。他悄悄碰了她一下,她才把紧盯着温伯玉的视线收一点来,但是很快又只顾看着他。
温伯玉本来从户外承受了一团浓浓的热力,这时候身体的温度尚未完全降低下来,却又有小凤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口也难张开,终至于吞不下东西。
这样深重地接受来自一位大姑娘的影响,在温伯玉也还是初次,也便不甘心。他勉强朝老众璞笑一笑,就问道:“你孙女几岁了?”
老众璞回答:“十七岁了。”
温伯玉暗想在她十七岁的腔子里装着的其实只是七岁小女孩的浑朴未凿的心灵。又问:“上过学没有?”
老众璞忽然颔首一笑,说:“我倒想起来让她跟老师学两个心眼子。老家的学堂离我们住的地方远,没法送她上学。现在看果真耽误了她。她这么没规矩我看着也生气!”
那小凤噗嗤一声笑了,半扭着身子哆嗦。温伯玉想不出她为什么笑,正猜测着,她又郑重了,竭力压制着体腔里的笑声,正襟危坐着。温伯玉知道她肚子里肯定空空的,却不好意思劝她多吃,老众璞也吃得少。后来他就把他们领到学校门口近侧的一所半新不旧的房子里住下,自己也去休息了。
老众璞解着放在床上的行李卷,小凤斜斜地倚着个门框对他说:“我一见那个人就想笑。你呢,爷爷?”老众璞头也不转地说:“你可是结结实实地老实过一阵子哩。你要总那样就好了。”小凤从那门里慢慢挪过来,在他铺平的床上坐下去,眼瞅着他的脸说:“我还没见过两条眉毛斗到一块去的人。你想不出一个人怎么会长成那个样子。我现在又想笑了。”身子向后一仰,又抬头问道:“他和我爹谁最了不起?”老众璞说:“当然是他啦!他才二十岁出头,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有出息。”但是眼前蓦地闪出自己儿子的面孔来,内心也就立刻黯然了许多。他在那里木木地呆了起来,小凤却不管他,只在他身上一个劲儿地乱缠。
2
温伯玉住在他们的隔壁。他起初还担心这祖孙俩初来乍到不习惯,当夜里不时听到从他们房间里传出的一阵阵嬉闹声时,也便令那颗心宽一宽。
第二天上午,温伯玉从课堂上下来就跟老师们一起坐在办公室里。老师们刚才议论了一回新来的看门人和小凤,共同认为他们可怜。那杨校长属于那种英年早逝的类型,而这大半生忙碌下来,一事无常万事休,竟连垂死的老爹和懵懂的幼女都不得养活,致使他们流落异乡。老师们顾念及此,唏嘘个不住,昨日未曾泄出的伤感也便趁机排遣了去。
温伯玉低着头弄碎了一棵粉笔,忽然有人敲了一下他的肩膀。他仰脸一看,见是数学老师李迎春。李老师的丈夫是镇政府财政所的所长,没少为学校出力,所以温伯玉对李老师格外敬重。那李老师欲说还休了几次,才一甩手,道:“算了!我是白操心。”温伯玉被搞得满腹疑惑,追问她:“到底有什么事?”李老师笑了一声,靠在桌子上,说:“温校长,你这个人成心要人作恶。”温伯玉紧张了起来,“从何说起呢?”
李老师便放弃了顾虑,接着说:“你想你是怎样安排的人家?那么大的一个姑娘跟一个老头子睡在一起。别说你成心不成心的吧,到底有失体统。真要出了事,看你怎么向大家交待!”
温伯玉身上直冒冷汗,他竟没有想到这个。别的老师也受了提醒,一起觉得学校里出了桩稀奇事情。温伯玉想了半天,才说:“怕什么!他们一个山沟沟里出来的人,哪有这么多穷讲究?我还听说,他们那里还有几代人睡在一条炕上的,跟远古蒙昧时期的人一个样。再说,他们既然那样惯了,你去硬叫分开,他们害起羞来,只怕不会在这里住了。”大家想一想,觉得很有道理。李迎春不再提这事,别的人也就不提了。但是温伯玉心里却没断思量,到底没有个两全之策,只好暂搁下。那手指当他琢磨时已在脸上留下了几个白粉笔印,别人笑着说给他,他才擦掉。
又要上课了,温伯玉拎着一只小闹钟找到众璞老汉,想让他们代替值班老师按时敲铁片。老众璞一早起来就紧盯着学校大门,却一直没有意外出现,现在正觉无趣,温伯玉要他做事,他自然喜欢得要命。小凤也来凑热闹,抻着脖子朝他们身上挤。温伯玉躲一躲她,指着闹钟说指针走到什么地方就该去敲铁片。老众璞笑着,摇摇头说:“俺不懂。”那小凤却叫了一声,“知道啦!”两个人将信将疑地瞅了她半晌。温伯玉又重复了几遍,小凤的眼中就有些不耐烦。
他走后,祖孙俩守着闹钟,目光紧追着指针转。小凤听着里面叭叭的清脆的响声,就说:“真怪,天底下还有这么小的动静。”老众璞忽然深叹了一口气,“唉,你爹说过要给我买的报明的东西,指的就是这个。他后来到底没买。”小凤全神贯注在亮闪闪的表盘上,根本没听爷爷说了什么。
过了一段似乎又很长又很短的时间,小凤啊的一声叫起来:“到了!”老众璞的每条神经都如绷直了,双手僵僵地握住木槌,就要往外走。那小凤迅若猿猱,一把将木槌从他手中夺了过来,直飞出门去。等她在办公室屋檐下的铁片前站住,双腿已颤得厉害。但她鼓鼓勇气,通的一声狠砸下去。她觉得耳朵也聋了片刻。当她重新听到铁片的声音时她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但她知道自己的整个腔子里都是比铁片还要响的笑声。她再次用力去打,铁片在绳索下面摆动着又发出了一声响。这时候就有老师惊讶地从窗户里探出整个头来,看着她敲。她终于在老师遏止的呼喊声中尽兴了,然后笑着将木槌向地下一丢,返身跑回爷爷那里。
老众璞看见孙女完成了一件大事,正满心欢喜。那小凤一到他跟前,就问他听到了没有。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孩子们已经站满了院子,一起朝她望。她一低头,含笑躲进屋里,觉得铁片响亮的声音犹在耳边,但是渐渐地又发现不对了。那是自己的一颗心在啵啵地跳,撞得心房难受。她想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她敲了铁片了,她一出门他们都会睁大眼看她是个好样的。她真臊得慌。果然,一直到天黑,不管老众璞怎么劝她,她也没出门半步。
温伯玉晚饭后走来时她的脸上还有羞色。她坐在老众璞的背后,整个身子缩在影子里,小声喘着气。温伯玉说:“小凤,以后打铁片少用些力,看绳子断了砸住脚。”小凤见躲不住了,索性从影子里坐出来,又觉得坐着也不好,便站起身朝门外的黑暗里走。温伯玉就又笑了。“你慢着点,我想问你愿不愿意上学?”他说。小凤真没想到这件事,不由得停了一下,却又走了。老众璞知道她正在门外听着,就故意说:“你别问她,我就不答应她做学生。她又没心眼子,学也白学,打铁片也才刚打好。”说着,就 着眼跟温伯玉对视了一下。那小凤又突然跳进门里,大声嚷嚷着:“谁在说我坏话哪?我可不饶他!”就扑在老众璞身上。两个人笑着打闹了一阵,温伯玉在旁看着有趣,腿也便拉不动。
小凤第二天就当上了他的学生。他虽是校长,却仍旧教着一年级的语文课。这位大出班上孩子十多岁的特殊学生一早就不见个影子,他和老众璞明白她肯定躲在了什么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看看上课时间就要到了,温伯玉只好把课本往胳膊底下一夹,走进教室。孩子们呼呼啦啦地站起来又坐下,他等到他们全都静下来时就转身在黑板上写字,却忽然听见板凳接二连三地又响了,便回过头来看。孩子们的目光全部投向门口,温伯玉只能看见从那里露出来的一点花衣角。他下了讲台,走过去,躲在门外的小凤吃他一惊,马上又笑着想跑,他伸手捉住她,她才扭扭捏捏地跟他走了进去,那颗头使劲向背后别着。
小孩子们猜不准他们在干什么,一看见小凤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坐下来,就发出了一堂怪笑。等了一阵,小凤明知道小孩子们又开始转身听温伯玉讲课了,可是头却抬不起,深深地埋在胸口。一节课完了,她简直没动上一动,浑身都坐麻了。那些小孩子们见她人大,本是对她畏怯的,现在看她羞涩异常,也便渐渐不怕了,都围过来趴在她前面瞧她的脸,跟她说话,又扯她的衣服。她有些恼了,一时又不敢发作,忽然觉得脖子上痒痒的有一股暖气儿在吹,便猛一回头,吓了探身在她后面的那个孩子一跳。那孩子几乎摔倒,小凤可不知道自己的眼珠子瞪得有多大,但是一见那小孩的慌张样子,自己倒先笑了。她很快跟他们成了朋友,丝毫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表示放学的铁片子声一响,小凤最先一个跑出教室。今天一上午没跟爷爷见面,她觉得就好像隔了几年。她要把班上的新鲜事儿全部讲给爷爷听,爷爷会是怎样高兴!可是爷爷也敲了一上午铁片子,他也要把自己心底的喜悦讲给小凤听呢。两个人一见面,却顾不得说,只抱在一块打转转。转啊转啊,两人觉得各自的脚下升起了一片云,把他们托到了空中,而两个人又是多么轻!他们最终累倒在床上,也不笑,也不动了。小凤撩一撩眼皮,温驯地看一看爷爷,爷爷也在看她。
良久,老众璞说:“小凤,你真成了大孩子了,莫忘了爷爷。”
小凤说:“我是想你颠儿颠儿地敲铁片呢。”
老众璞说:“你学了什么心眼子,说给我听。”
小凤就说:“老师说学生听,动都不动。”
老众璞点点头,说:“嗯,不错。你是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