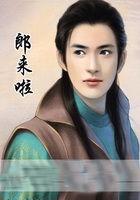“你看,从这边数第三棵大蒜,蒜瓣好大,蒜苗好胖,肯定忒好吃。”隔着窗子,二姐怂恿着我。见我还是不敢翻过去,二姐就软硬兼施:“你再不去,以后就别跟我玩了。”我一咬牙,翻进瘪婶家院子,奔向那棵蒜,拔起,来不及抖落泥土,就跑回窗边准备翻回家。
瘪婶家的门“哐当”一声,接着就是瘪婶那仿佛塌了天一般的声音:“不得了了,李小翠,你家儿子偷我东西了……”
二姐刚伸手准备拉我,一听瘪婶的叫声,就头一缩,跑了。我本来就高度紧张,被瘪婶这一嗓子更是惊得全身酥软了,怎么也爬不上窗台。瘪婶跑过来,用她那粗大而干硬的手紧紧抓着我光光的胳膊,继续高叫着:“李小翠,李小翠,你养了贼儿子……”
我喘着粗气,烂泥一样瘫在窗台下。此时,我最怕母亲回来——她看我偷了人家东西,还是瘪婶家的东西,非打死我。
可是,母亲偏偏从田里回来了。
母亲快步走到窗边,趴在窗台上,揪着我的头发就把我提了过来,往地上一丢,对着我的嘴巴一通左右开弓。
“这么屁大就敢翻墙做贼了,长大后杀人放火还什么不敢做啊?”瘪婶站在窗外,指着我母亲说,“哼!念书好,念书好有个屁用?到头来还不是要吃牢饭?吃枪子?”
母亲还是一句话不说——面对瘪婶的人赃俱获和汹汹气势,她当然无话可说。她又拿起牛鞭子,对着我光光的腿,一阵猛抽。我只有低着头,只有钻心的痛,不敢躲,也不敢哭。
“小的是贼,老的也好不到哪去!老老小小都好不到哪去!”瘪婶冷笑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怎么和这样的人家住到了一起?”
小江瑟瑟地走进院子,扯着瘪婶的衣襟,叫瘪婶别说了,回家。瘪婶却拉过小江的手说:“儿子啊,我们住哪儿去呢?妈妈不能让你和贼住一块也变坏了啊!”小江赶紧挣脱瘪婶,捂着耳朵,跑回了家。
母亲对着我光光的后背,又一阵打。
我终于明白了瘪婶是在报复我母亲:曾经,母亲与瘪婶关系不错,我和同龄的小江也玩得好,但自两年前她俩为一件鸡毛蒜皮的事争吵后就总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和小江自然也被禁止了来往。最初争吵,她俩旗鼓相当,不分伯仲,可随着去年我和小江的入学,这种势均力敌的形势被打破了——小江念书特笨而我特好,于是一争吵母亲就拿小江说事,瘪婶一被提到小江就灰溜溜地退回家,关上门给小江一顿巴掌或鞭子。总之,因为我和小江,两个大人的脸面发生了变化:一个鲜头光脸,一个灰头土脸。
现在,瘪婶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哪肯轻易放弃?
“哼!伤皮不伤肉,有什么用?三天后还不是照样当贼!”瘪婶一边收拾着我刚拔的那棵蒜,一边说,“我家小江,敢拿人家一根草,我就打断他的腿,打残他的脑瓜子……”
三大妈来了,看到我满身的伤痕和满嘴角的血,拦下又要打我的母亲,指着瘪婶说:“你太过分了,孩子不就是拔你一棵蒜?你还真要李小翠把孩子打死才罢休?”
“我又没打他,我又没叫她打,打死是她自己的事。”瘪婶的口气软了些。
母亲终于开口了:“你就是想让我把孩子打死!我儿子打死了,你儿子就能考上状元了!”母亲一边擦着我嘴角的血,一边冷笑着说,“我聪明的儿子啊,你怎么干这种傻事啊?你看,人家的孬子儿子都不干这种事呢。”
小江刚又瑟瑟地走进院子,一听我母亲提到了他,头一缩,赶紧跑回了家。
瘪婶张了几次嘴,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母亲流着泪,轻抚着我后背上她自己留下的巴掌印,大声说:“小人,想把我儿子打成和你那孬儿子一样的铁蛋脑子、死猪脑子,永远都不开化……”
瘪婶忽然低下头,快步向家走去。随着瘪婶“哐当”一声关了门,她家就传来“噼里啪啦”的鞭子声和小江撕心裂肺的哭叫声。
这件事的后果是:小江不久后就辍学了,才九岁;而我,在很长时期里,一听到“偷”或“贼”这两个字,心里就莫名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