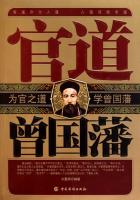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儒家认为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基础、起点。孔子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事亲,事之本”,这个“本”,不仅是根本,更是出发点。因为人会长大、要进入社会,于是逐渐地又会生出君臣(上下级)、夫妇、长幼、朋友及更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事、同学、老乡……乃至中国人、外国人等等)。
处理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的原则,孟子已经告诉我们,即有义、有别、有叙、有信。那又如何来处理与“五伦”之外其他人的关系呢?按儒家的说法,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就是把“孝悌”这种爱人精神向外“推”——推己及人。
所谓“推”,用孔子的话说叫做“能近取譬”,意为能够就近拿自己与别人作比方,再通俗点讲就是将心比心,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把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又称之为“恕”,它与“孝”、“忠”一样属于“仁”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
到孟子那里,说得更明白、也更远:“仁之实,事亲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的实质就是事奉父母双亲;从爱戴自己长辈的体会中推广出也应该爱戴别人的长辈,从呵护自己孩子的体会中推广出也应该呵护别人的孩子;从爱自己的双亲中推广出爱所有的人,从爱所有的人中推广出爱自然界的万物。孟子把这种精神、这种态度又称之为“推恩”。
孔子、孟子的以上思想,所反映的还是儒家“仁者爱人”这个基本主题。只是就“爱人”的程度而言是有差别的,其实质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爱,而这种差等之爱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人之常情”。
儒家这一思想与墨家的“爱人”思想有明显的不同。当时,墨家与儒家齐名,同称“显学”。墨家的核心思想是“兼爱”,即强调“爱无差等”,不能分什么亲疏远近。具体点说那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按墨子的观点,人们只有“兼相爱”,才能“交相利”。
对墨家的“兼爱”之说,孟子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墨家所讲的“兼爱”问题很大。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它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之别,将人父等同于己父,那也就等于没有己父——孟子名之曰“无父”。而“无父”不啻不合人之常情,上纲上线的话就是大逆不道,所以也就等于是“禽兽”,因而必须“距之”(批判之)。孟子这是在骂人,还骂得很凶,似乎有失谦谦君子的风度和雅量。但在战国“百家争鸣”的那个年代里,思想交锋此起彼伏、尖锐异常,大概除了淡泊自守的道家者流之外,诸子中鲜有不骂人的。儒家中不仅孟子,包括后来的荀子,骂人都是够厉害、够水准的。
如果就思想本身而言,儒家的“爱有差等”和墨家的“爱无差等”都有其言之成理的、可取的一面。但就影响而言,由于前者比后者更符合人性的一般特征,所以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原文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今译
君子对万物,爱惜而不待以仁德;对百姓,待以仁德而不亲爱。君子亲爱其双亲,推而以仁德待百姓;以仁德待百姓,推而爱惜万物。
原文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注释
《诗》:《诗经·大雅·思齐》。刑:通型,示范。寡妻:嫡妻。
今译
尊敬自家的长辈,进而也尊敬人家的长辈;爱抚自家的小辈,进而也爱抚人家的小辈。那么,治理天下就像在手掌上转动一件小东西那样容易了。《诗经·大雅·思齐》里说:“先教育自己的妻子,再教育自己的兄弟,然后推行到自己的封邑和国家。”这不过是说拿自己的好心推广运用到别人的身上而已。所以,能推广恩惠,就能保有天下;不能推广恩惠,连自己的妻儿也保不了。古代的圣贤明君所以能远胜过一般人,没有别的什么,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