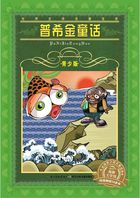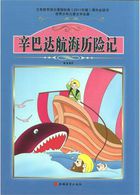塞·巴鲁兹金
有一年春天,我去堪察加半岛的一个养鹿场。虽说已经到了春天,可地上的积雪却至少还有三尺厚,还呼呼地刮着寒风。
这是个长角鹿繁殖场。当然,放养鹿还得到百公里外的苔原去。
我们是乘直升飞机去那里的,我们的飞机降落在阿普卡河的河谷上。养鹿场的凯亚夫和我一起去的。他是养鹿场场长,他把我安顿在他的帐篷里住。
他和我一道走出帐篷的时候,拎上了他那架名牌收音机。
我还没闹明白他出去放鹿,怎么还非得带上这收音机,却不料从另一个帐篷里出来的放鹿人伊利卡尼,也拎着一架同样牌子的收音机。
于是我就问了:“你们都是广播爱好者?”
“不知道各地消息怎么行?不行!”伊利卡尼说,“得知道我们全国各地都发生些什么。我们科里亚人爱听广播,电视得到彼得帕夫洛夫斯克市才能看上!”
我们走出帐篷的时候,一群长角鹿已经在等我们了。
大概上千头鹿呢。一些鹿的鹿角已经长得很长了,很好看,另一些却还小,鹿角才长出一点点,露了点儿头。
鹿们眼睛定定地看着我们。
我看出来,这些鹿的眼眶里似乎都是湿润的,透着忧郁。这样的眼睛有多少啊!海洋般大片的鹿群,都用这样期盼的眼睛看着我们。这鹿的海洋一见主人出来,就都涌动起来,淅淅沙沙地挤着。
“嘘——呜——呜!”凯亚夫一边吹口哨一边往空中甩了一下鞭子。
“哎啊!赫——赫!”凯亚夫又吆喝了一声。
吆喝声一落,鹿们就向苔原飞奔而去。
我跟在养鹿人的身后,追着鹿群向苔原走去。两个养鹿人忙碌起来,我悠闲地跟着他们。我不是养鹿人,鹿们不会听我吆喝的。
我们一路走,时不时坐下来休息一下。鹿们用蹄子、用花角,有的干脆用头去拱积雪,把积雪拱开,把头深深埋进雪堆里去吃苔草,乍一看去,都不见鹿头了。
我和凯亚夫、伊利卡尼一起跟随着鹿群,往前走着。
走出很远了,凯亚夫说:“咱们得吃点东西了。”
“那鹿群怎么办呢?”我问,“它们不会走散、走远吗?”
场长很有意味地朝我笑笑,打开了收音机,开到最响。
“你看着吧,它们不会跑开的!”
我们把鹿皮铺在雪地上,坐了下去。我们身边是一片杂木林,一直向小山那边延伸过去,鹿群在小山那边吃草,简直看不见它们的身影……
伊利卡尼也打开了他的收音机,开到最响。
我还从来没听过这支曲子。两架收音机的高音喇叭震荡着茫茫雪原。
“鹿群这就会回来的。”凯亚夫场长说。
“一定会的。”伊利卡尼接口说,“你就看着好了……”
鹿群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拢过来。花角的,小角的,有的还很小哩。这时我才明白,这长了大树枝般花角的,是公鹿;那些角像小枝条的,是母鹿;而鹿娃娃也不难辨认,那些角才冒个尖尖的,是幼鹿……
鹿们走近我们,亲昵地看着我们,一头头都看得出神。
“它们爱听收音机。”凯亚夫说。
“它们真的是在听收音机吗?”我问。
伊利卡尼说:“它们爱听音乐,新闻就不怎么爱听。它们听熟了的讲故事人的声音传来,它们也喜欢,而新闻就吸引不了它们了……”
我们在铺在雪地上的鹿皮上坐着,吃饭。两架收音机响着音乐。鹿群挨我们站着,它们的嘴唇热乎乎的,亲昵地蹭着我们的手掌。不过,它们的眼睛始终定定看着那源源荡出乐声来的收音机。
“凯亚夫,”我对我的朋友说,“你倒是把收音机停掉看看,要是没有音乐呢……”
伊利卡尼关掉他的收音机。凯亚夫把他收音机的高音扬声器打开。
鹿们于是走得离我们更近,像猫咪似的舔我们的手。
我们吃着带来的烤得香香的鹿肉和鱼肉,喝着茶。
“波尔卡舞曲要响了,它们该来劲儿了。”凯亚夫说。
这时,一个收音机里传来了乐曲声。
“我把我的收音机收起来。”伊利卡尼说。他说着把自己的收音机藏进了口袋里。
随着波尔卡舞曲的乐声,鹿群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哦,简直是一片鹿角的丛林啊。大大小小的鹿全部眼睛湿润,神情忧郁。我听出来,收音机里播放的是柴可夫斯基的乐曲。
“它们爱听柴可夫斯基?”我问凯亚夫。
“我们的鹿特别爱听柴可夫斯基。”凯亚夫说,“就像现在看见的这样。这乐声太美了。但是,你看……”
他换了个台。
鹿们就都发呆了,讶异地看着我们。它们的眼睛一只只都睁得大大的,直直看着我们——这些湿润的、忧郁的眼睛。
它们看了一阵,就渐渐走开了。
它们在苔原上寻找它们的苔草……
后来,我才慢慢想明白:这些鹿爱听的也就是美妙的音乐,像柴可夫斯基那样动听的音乐。而新闻广播,不管这新闻对我们人有多重要,它们也没耐心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