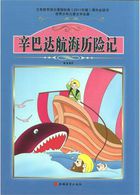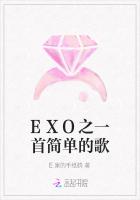米·普里什文
森林里,鸟和兽各住各的楼层。林鼠住在树木的根部,它们住在最低层;各种鸟类呢,譬如野莺这类鸟,将自己袖珍的窝巢紧紧贴着地面;鸫鸟则在稍微上面些,在矮矮小小的灌木上;那些穴居的鸟类,像啄木鸟啊,山雀啊,猫头鹰啊,住得更高;树干的顶端,树冠的最上面,高高低低住着各种各样的猛禽:个儿庞硕的鹞鸟和鹰。
有一次,我在森林里专门留神观察,看见许多小兽和鸟,它们不像我们人似的爱住高楼大厦。我们人住过来住过去,反正都在高高的楼层上。而各种类别的兽、各种类别的鸟再搬再迁,楼层都有一定之规,不会高上去,也不会低下来。
有一回,我们来到一片枯倒了的白桦树的林中空地上。白桦树长啊,长啊,长到一定的高度就枯死了,这样的白桦树我见多了。别的树枯死了,树枝就向地面萎垂,那些落光树叶的木头很快就朽了,不多久就倒地糟烂了。而白桦树的树干却不是这样,枯了也不倒下。这糊满树脂的白色桦木干,看上去依旧好端端的,不腐、不烂,明明死了的树吧,像活着的树一样直直挺立着。
就是已经朽了,桦木木质已经变成渣渣了,整根树干里都已经多半是水分、十分沉重了,这时候的白桦树也依旧如它活着时那样笔挺笔挺的,昂首矗立着。然而,这样的树如果稍稍使上点儿劲推它一把,那么它就会在瞬间碎裂成许多沉重的木块,顷刻间轰然倒塌了。去推倒这样的树,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活儿,不过也挺危险的。要是躲闪不及,饱含水分的沉重木块就会砸到你脑袋上。好在像我们这样经常出入森林的人倒是不会怕这种危险的——要推倒这样的树,我们就只会从树的一边上去,然后一齐用力推,把树一下推倒。
我们来到的就是立着这样的朽木的白桦林中,要把高插云霄的白桦树一棵棵推倒。白桦树倒下后向四面迸裂的木块中,有一块木头是山雀的窝。个头儿小小的鸟在白桦树倒下时也没受伤,只不过是一窝小鸟“哗啦”一下从它们的树洞里震颠了出来。毫毛未及生长的小鸟,光溜溜的,身上只覆着些柔细柔细的胎毛。它们张开红红的小嘴,把我们当做它们的爹娘,唧唧、唧唧地叫着,要我们喂小虫子给它们吃。我们赶忙从地里挖些小虫子,给它们喂进嘴里;它们吃着,吞噬着,吃完了又唧唧地大叫开了。
才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的父母就回来了。是山雀,它们的小脸一律胖嘟嘟的,嘴里都叼着一条小虫子,在窝边蹲下来。
“亲爱的,你们没事吧?”我们向它们问候,“让你们受惊了,我们万万想不到你们的窝会在树上的。”
山雀没有回应我们的问候。它们一定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好好站着的树怎么说没就没了呢,孩子们这会儿都在哪儿?
它们倒是不怎么怕我们,它们焦急地从这根树枝飞到那根树枝,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你们的孩子在这儿哪!”我们给山雀们指了指地上的雀窝,“它们都在这儿,你们没听见你们的孩子在‘唧唧、唧唧’不住声地呼唤你们吗?”
山雀什么也没有听见,它们只顾心烦意乱地忙着寻找它们的孩子,它们不愿意飞下来,它们不想离开它们住惯了的楼层。
我们彼此交换了一下意见:“它们是怕咱们吧?咱们躲起来试试!”这样说着,我们就藏了起来。
不对!小鸟唧唧叫唤,大鸟也唧唧叫唤,大鸟飞来飞去,可就是不飞下来。
我们猜想,鸟儿们不像我们人这样爱待在高楼大厦里,它们不能够适应习惯以外的楼层,它们就只觉得住着它们孩子的楼层消失了。
“喂,喂,喂,”我的伙伴对鸟父母们说,“你们也真是傻到家了……”
这山雀样子挺漂亮的,又长着一对灵敏的翅膀,可惜就是不会变通,死板地在高空中寻找它们的楼层。
于是,我们只好把那一大截筑有鸟窝的桦树木头安到邻近一棵树干上头,使这个鸟窝的楼层位置刚好相当于倒掉的那棵树上的高度。我们耐着性子在旁边一个隐蔽处等待,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几分钟后,鸟父母又能在自己的楼层里欣喜地照料自己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