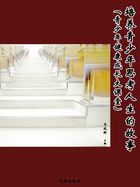参军,当一名军人,就注定了一个人必须在戎马生涯之中度过一生。他必须要有非凡的意志和超强的毅力,才能在南征北战之中顽强地存活。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顽强不屈的意志力和生命力。但话又说回来了,在常年经久不衰的征战中,他们也从一个血肉丰盈的人驯服成了一个石头般刚硬的人。他们鲜活的血肉正在一步步地流失,他们的情感也随之在蒸发,乃至消散得无影无踪了。他们甚至变得异常可怕,丧失了人性,在战场上像猛兽一样乱砍乱杀。渐渐地,他们杀红了眼,把人当成了该死的东西,甚至以杀人为乐趣,以杀人来炫耀自己的本领和英勇,以杀人来获取战功,以杀人来换取别人的尊重。那时,他们也就沦为一部部没有血肉的杀人机器了。到那时,没有杀人他们就会心痒痒,就会坐立不安,他们就会觉得异常难受,所以每当战争爆发了,他们就跟着兴奋了起来。他们赶着要立即奔赴战场再去多杀几个人,不然,他们就生不如死了。
然而,他们也曾经考虑到会有被杀的那一天的到来,所以他们就更加想把握住时机多杀几个人,多立战功,将来如果哪天自己也被杀了,也能光宗耀祖、名扬天下。如果那样,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死一千次也值了,毫无任何遗憾了。他们认为那是一个军人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同时,那也是他们最大的悲哀和罪孽。到那时,他们已经泯灭了人性,甚至比猪狗都不如了。他们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为了被杀而被杀,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迷失了自我。
当然,也有的士兵没有达到那种刚强的程度,他们有幸没有沦为一部杀人机器,但是这同时也注定了他们无法在这样一种屠杀环境之中存活,这或许是他们的悲哀之处了。他们希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不希望看到血肉横飞、你死我活的场面出现。特别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国人遭到他国军队的残暴虐杀,这是他们毅然走向战场的最大原因。
为此,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得不违逆着天生善良的本性在战场上进行厮杀,他们是在内心的极度挣扎之下,杀了第一个人的。即使之后,他们也会慢慢地适应这样一种无情的虐杀,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丧失人性当中某些可贵的东西。他们依旧是一个有血有肉之人,还没有达到杀人成性的疯狂地步。他们参加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换取家人、国人的安全和幸福,是为了能够向世人证明和展示战争的残酷性,让世人谨记战争的危害性,尽量避免战争的再度发生,还人类一个和平的世界,让人类有一片安居乐业的天地和乐园。我们不得不对他们肃然起敬,但同时我们也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同样犯下了杀虐之罪,罪不可赦。
在生前我也是一个征战了半生的军人,这样一种四处奔波的军旅生活我早已经习惯了,那确实是一封家书抵万金的极为难熬的生活,每天闲暇时都有很多时间在思念亲人的状态之中度过。尽管在战场上,我们杀人如麻,但那也是为了活命和继续生存,为了让自己得以和亲人再度相会。那样一种情景是多么令人向往和陶醉啊!还未到达家门口,整颗心就激昂澎湃了起来,咚咚咚跳动个不停的,那是一种没有着落悬空的弹跳。毕竟,已经许久没回家,没见到家人了,家中的情况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之中一无所知,仅能靠着往日仅存的记忆,在回想之中点滴勾起,在心中萦绕不去。
于是,以前家中的一切就先都在脑海之中游荡了起来。我家在一个四合院里,有高高的院墙,是用红砖头一层层天衣无缝地堆砌而成的。从外面放眼看去,极其壮观,红红的一片矗立起来,极富洋洋的喜气,给人以鲜活的活力,让人在它面前不由也挺直了腰杆。这也是我听我那日渐年迈的父亲说的,他说,每逢他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被它们弄得焦头烂额,无处可去,心里烦忧之时,总是喜欢自己一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来到院门外,站在那高高的鲜红的围墙外,看着那直挺的围墙,原先纠缠着的心境仿佛也在瞬间解脱了许多,开朗了许多,他原先被压抑着略略弯曲着的腰,也在瞬间挺拔了起来,恢复了生机和活力,而四周阒寂得几近无声的幽雅的环境,更是让人心境顿时如当时天上所悬挂着的那轮明月那般清明。皎洁无瑕的明月毫无偏袒地把光辉播撒到了世间的每个角落,也力所能及地照亮了世间每个黑暗的所在。它甚至可以直接指涉到每个处于困顿之下的落魄人那寂寞的内心,从而让他重见光明,迎接黎明的到来。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下,黑夜慢慢深了,已经快走到了尽头,这时,四周原先不时传来的夜虫们的低吟声不由也随之慢慢消沉,直至趋于寂静。夜越深,四周也就越寂静了。世间的一切生物都需要在夜晚之中得到一定的休息,积蓄精力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即使是那些需要在夜间进行各项有意义的活动的动物们也不例外,比如夜虫的独奏与合奏,那也是需要在休息之下,重新积蓄力量,为明晚的演奏做好准备,才能让歌声保持清脆、婉转、优雅、动听,不至于沙哑。所以,最终它们的歌声也就会渐渐平息下来的。
每当这时,天边那线曙光也已经慢慢地撕开了夜色的防线,泄露出了一丝丝难以捉摸的光芒,悄悄地打破了这日渐宁静的夜。父亲多次在这样一种越发宁谧的夜色和月光的笼罩之下,带着一种旷达的心境回到了家,原先的寂寞与忧愁竟也慢慢地奇迹般消失了,回到了家,父亲甚至忘记了它走出家门的目的了。他甚至以为自己每次只是被这迷人的夜色所打动,不由自主地迈开脚步来到了那令人沉醉的夜色之下,来驱散白天蒙在自己身上的尘灰与疲惫。然后,带着这样一种欣慰、满足的心境,父亲每每都睡得昏沉沉的(第二天醒来总是发觉自己的口水流了一草席,在早晨初阳的照射之下闪着清澈的辉光)。他也疲倦了,需要补充体力,去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家院中靠西的那棵榆树,大概也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吧!那树上也必定有了鸟儿来做窠、鸣啾,欢快地居住在那里繁衍生息。那是我要出征之前栽种的,想用它来为我们遮挡住强烈阳光的照射,为我们共同居住在一起的院中人留下一荫可供休息和闲谈的好去处。而我那当初还小的白胖儿子也已经长大了吧,变得强壮许多了吧!他是否还和我长得很相像呢!?还是现在已经不像了,变得和他那漂亮的母亲一样俊朗,或者是长出了自己的风格,别有一番风味了?他的母亲是否依旧年轻美貌如初呢?还是和我一样,经不起岁月风霜无情的冲刷而变得苍老了许多!我那来不及刮干净的胡子此刻又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下巴,它们的生命力倒是挺旺盛的。不知道我这样一副模样回到了家中,家人是否会认得出我来。如果已认不出我来,那该如何是好呢?对了,我母亲肯定会记得的,我的后背上有一片很大的黑乎乎的胎记,像是一朵正在盛开的黑玫瑰一般氤氲在身上,只是闻不到花开时特有的香味而已。而家中,也只有母亲能够清晰地记得它的存在,能够辨认真伪,想到这里我的心情也不由轻松了许多,安稳了许多。回家的脚步不由也跟着轻快了起来,我甚至独自哼着军营之中学过的一首以思念家乡为主题的优雅的歌曲来了,那温馨而又夹杂着忧伤的曲调和旋律让人沉湎其中,无法自拔。
兴许,我的妻子还多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女娃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她也应该有我刚出征的时候的个头了。她一定也是很文静的一个孩子,就像我小时候一样。不知道我那傻儿子有没有变得比较活泼了,还是见到了生人依旧还会受惊吓般地躲到可以躲藏的地方,久久不敢抛头露面。我这样一副模样回到了家里,会吓着了他吗?邻居们都还好吗?赵大家的不知道是生了男娃还是女娃。如果是女娃就好了,将来和我家那小子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孤苦无依的李大妈失踪多年的儿子不知道找到了没,回来了没……我纷繁的思绪依旧随着前进的脚步在飞旋着,只要还未到达家中,它就会继续不停地运动。
戎马半生,戍守边疆,直至战死,我也才仅仅得以回归家园屈指可数的几次而已。每次回家,我都老了许多,家里自然也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更。有一次,我回去之后,家里的老母亲刚好病危,一开始,处于极度疼痛状态之中,后来躺倒在床上昏迷已有多日了,看样子,凶多吉少。大夫来了说是操劳过度,才导致在不自觉中昏迷了过去,一时无法清醒过来,至于说,能否清醒起来就得看她自己的造化了。大夫只是开了几帖补充体力消耗的药方,嘱咐家人按时煎熬少许给她服下,暂时保住她的命脉,就面带愁容地告辞了。家人都为了母亲的病情焦灼万分、坐立不安的。一个个都愁着眉,苦着脸,守候在她的身旁,寸步不离,焦急地盼望着奇迹能够出现。而昏迷在床上的母亲倒显得镇定自若的,面目舒展,只是脸色异常苍白,没一丝痛苦的神情,好像她只是非常累了,停下来尽情休息了一会,不一会就会再起来了。这不由让家人更加担忧了起来,生怕她再也起不来了,如果那样对他们的打击将是无可言喻的。
那时,我终于可以回来了。在母亲重病时,得以回来陪伴她渡过难关,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和悲哀。在这样一种复杂心境的支撑之下,我立即跪倒在母亲病床之下,低着头,为她虔诚祷告,希望她能赶快苏醒过来,哪怕让自己死无葬身之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样跪着祈祷了多久,或许连上天也被我的虔诚所打动了,让母亲那温柔的手又得以再次抚摩我身着布衣的身体了。是母亲的手先颤抖着在我的臂膀上蠕动着,才让我惊醒了过来。当我抬起眼,我终于看到了母亲舒展开了她的慈眉善目,眼中闪烁着呼之欲出的泪花。顿时,母子竟然在这样一种难以预想、生离死别的情景之下见面,就都热泪盈眶了。
还有一次,也在我的记忆之中印象深刻,甚至现在我成了飘荡的游魂之后,依旧记忆犹新。那同样是一个寒风呼啸的冬天,漫天飞雪飘扬,草木早已被埋没在层层的积雪之下,动物们都在各自的洞穴之中煎熬着,冷冻得瑟缩成了一团。它们都焦灼地期盼着严冬能即刻过去,迎来万物复苏的温馨的春天。此时回想当时的那样一种景象,不禁让我联想起死后我们那被飘雪覆盖得越发严密和冻僵了的躯体。我死后的灵魂就是从那越发浓厚的积雪之中突围飞升而出,并且得以在人间四处漂流与游荡的。那里面同时还堆积着许多往日战友和敌军冰冷的身躯。我已经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了,只知道他们都是在这场战争中战死身亡,横尸沙场,并且很快就被不断絮絮而下的飘雪所遮蔽住,包裹住了。我的躯体被他们的躯体所层层包裹着,堆压在最低层。我横死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还在奋力拼杀,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会怎样死,什么时候会死,或者能够幸运地得以不死。所以,我的灵魂脱离我的躯体的时候,还能够感受到我的躯体尚余温热,即使我上面是层层越发严密的积雪,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当中。然而,那些横陈在我躯体上面的其他战士的躯体或者是断肢却一层比一层寒冷。我的灵魂在不断地拨开他们躯体的缠绕时,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样一种极致的变化。那时,我感觉到自己好像还没有死,自己的灵魂拖着自己尚余温热的躯体逃离了这个阴森的现场。所以,我的灵魂逃离的动作显得极为夸张和迅疾。逃脱之后,我满头大汗淋漓了,但不一会,就都被极为严寒的飘雪所冻结了,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冰珠,停滞在脸上,让我显得滑稽不堪,像个小丑一样,无脸见人。
推开家中那笨重的院门时,我的手冷得直颤抖,都快被那金属门环异常刺骨的严寒所冻僵了。我搓着双手,不断哈着暖气,快步来到了院中。院子同样一片死寂,有薄薄的积雪堆积在院中,并且还在不断累积当中,而各门户的大门也都紧闭着,没什么动静。那棵枝叶早已繁茂,树干粗壮的榆树依旧挺拔着身躯在与严寒做最决绝的斗争。它是绝不会向它们低头的,这是它一贯的作风。即使它上面也难以避免被飘雪覆盖的命运,但是当寒风一来,它就顺势把它们潇洒地甩开,让它们回归到地面上。它一向认为那才是它们最应该到达的地方,地面才是飘雪的最终归宿,所以它毫不屈服地与它们周旋着、斗争着。那时,我从它的身上看到了往日许多战友的形象,他们与它具有相同的毅力和品质,但他们有的却早已战死边疆、横死沙场很久了,我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我想,由于天气太过严寒,所以家人肯定都躲藏在家中,像过冬的动物们一样畏畏缩缩的,不敢轻举妄动。我甚至想象着见到他们时,他们那被冻红了的脸,肯定会显得更加好看,就像是刚出生的娃娃那般鲜艳,惹人喜欢。而到那时,我那红扑扑的脸无疑会先遭到他们不明目光的审视,然后他们才得以认出我来,就都会哈哈哈互相笑出了开怀的笑声,那笑声所流露出的温暖仿佛也在瞬间把所有的寒冷都驱散了。然后,我们就互相紧紧地抱成了一团,滚烫的泪水随即就濡湿了各自的衣襟。几年不见,再次相见时,情景却格外温馨和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