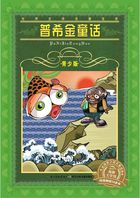据有关研究统计。实际上康有为的弟子数量应该更多,只是其早年所收弟子因缺少资料无法准确统计。,康有为有受业弟子120人,拜门弟子15人,私淑弟子10人。在受业弟子中,自然以梁启超最为世人所熟悉。不过,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有为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已经获取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一方面说明梁启超非同一般的见识和勇气,一方面也说明康有为自有非凡的吸引力。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康有为为师: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一下被康有为的过人胆识和天才学说给迷住了,自此决定了他与康有为一生的师生缘分。不过说起来陈通甫才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因为他比梁启超入门更早,也更得康有为的赏识,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可惜天妒英才,不幸早逝,之后“大弟子”的头衔自然落到梁启超身上。而梁启超也没有辜负这个名号,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再到流亡海外,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后来师徒二人政见虽有不合,但梁启超在视康有为为师这一点上,是没有变化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他是第一个获得德国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前期参加革命,后期全力从事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再就是麦仲华,他先是成为康门弟子,后成为康氏之婿,其弟麦鼎华也随之拜入康门。
在康有为的拜门弟子中,政治方面有唐才常,艺术方面有大画家刘海粟和徐悲鸿;在私淑弟子中,有谭嗣同、吴锡龙等民国名人。
显而易见,康门弟子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演变进程,产生过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主要发生于清末民初阶段,之后,其在文化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便逐渐让位于了以章太炎为核心的浙籍文人群体。而浙籍文人群体的兴起,除了与章太炎这个文人领袖有关,还与另一位为辛亥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浙籍文人有关,他就是蔡元培。从近代以来对浙籍文人群体兴起的作用角度来说,蔡元培居功至伟。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的辉煌。民国时期浙籍文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壮大,与章太炎和蔡元培有直接关系,对此学术界是早已认同的。章太炎从学术上给众弟子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蔡元培则因自己在教育界的特殊地位,为浙籍文人进入北大以及高教界提供了宝贵机会,也就等于从发展空间上保证了浙江文人群体的持续发展与壮大。
蔡元培与“某籍某系”
民国时期的浙江文人作为一个整体,由于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北大等著名高校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巨大影响,颇为引人注目甚至妒忌,所用称呼就成了“某籍某系”。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在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不过,在浙江文人内部,也还是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小群体来,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浙籍章门弟子外,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以施蛰存、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文人群体以及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文人群体等。
在这里我们即以蔡元培如何从浙江进入北京的文人圈子,以及他如何凭借自己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以他和章太炎为领袖人物的浙籍文人群体为个案,来评述浙籍文人在民国期间占据中国文坛主流地位的过程及其特点。
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元培也是从少年时代起就决心通过科举道路进入上流社会的,只不过相对于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少数幸运者中的一员。1872年,虚岁六岁的蔡元培进入私塾学习,这一年他正式使用“蔡元培”之名。尽管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坎坷,但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相比,其科举应试之路倒是较为顺利。17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文化范围之内,但他已开始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举人,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而且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也引来很多学子的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在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乃至国内第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蔡氏进入第一流文人圈子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进士。如此,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很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毫无疑问,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特意将其名姓、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为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多少铺平了道路。
也就是在科举顺利之后,蔡元培有机会游历国内各处,对晚清时国内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也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1894年,蔡元培开始了供职翰林院的京官生活,并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能获得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机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同乡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的作用,以后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但促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也在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时起到了类似作用,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之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语。受这些友人的影响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的打击,多位参与变法好友的受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令他对政治改革丧失了信心,决定回家乡绍兴兴办教育,走艰苦的教育救国道路。但毫无疑问的是,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他所结识的文人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将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以上参看蔡元培的《孑民自述》《蔡元培年谱》和张晓维的《蔡元培评传》中有关内容。
据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日记,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八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此时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
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生于1850年,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他是浙江嘉兴人,当然算蔡元培的老乡。沈氏当时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虽然他自己那时在京城也已算是小有名气之人物了。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可以看出,蔡元培一直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马上就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当然,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关系,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交往的内容就出现了八次之多。对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蔡元培也早就与他密切交往(其日记中出现与李氏交往的时间为1894年6月,但显然应该更早,不过蔡氏日记从该年起始,所以无法找到更直接的证明)。有一点可以断定,蔡元培在京城期间,已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时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蔡元培与张之洞等也有所交往,这表明当时他已经进入中国文人最高层次的群体。虽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无非是那个时代所有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的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所以很难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研究。不过,仅仅就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交往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的。这对于蔡元培后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教育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主要还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家乡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较之与传统文人的交往,这对他以后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影响。在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在回绍兴仅仅一个半月后,随即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郡中西学堂的(总理)校长一职。熊再莘思想较为开明,同情变法维新人士。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年)举人,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学堂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可谓中西之学兼具。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并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入,同时对外开放。古越藏书楼也因此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是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传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其以杜亚泉更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