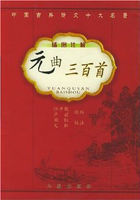至孙氏之对于墨子学说,亦颇有持平之论。其自序云:“身丁战国之初,感悕于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谆复深切,务陈古以剀今,亦喜称道诗书,及孔子所不修《百国春秋》;唯于礼则右夏左周,欲变文而反之质;乐则竞屏绝之;此其与儒家四术六艺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务为和同,而自处绝艰苦;持之太过,或流于偏激,而非儒尤为苝盭,然周季道术分裂,诸子舛驰;苟卿为齐鲁大师,而其书《非十二字篇》,于游夏孟子诸大贤,皆深相排笮。洙泗龂龂,儒家已然;儒墨异方,跬武千里,其相非宁足异乎?综览厥书,释其纰,甄其纯实可取者,盖十之六七;其用心笃厚,勇于振世救敝,殆非韩吕诸子之伦比也。”
稍后于孙氏而研究墨学者,有章炳麟,梁启超。章氏精训诂及佛乘,故所言多独到之处。惟无专书,略见于《国故》、《论衡》原名篇而已。如云:“《墨经》曰:‘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说》曰:‘智者若疟病之之于疟也,自注:上之宇训者。智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此谓疟不自知,病疟者知之;火不自见,用火者见之;是受想之始也。受想不能无五路,及其形谢,识笼其象,而思能造作。见无待于天官,天官之用亦若火矣。五路者若浮屠所谓九缘:一曰空缘,二曰明缘,三曰根缘,四曰境缘,五曰作意缘,六曰分别缘,七曰染浄依,八曰根本依,九曰种子依。自作意而下,诸夏之学者不亟辩,汎号曰智。目之见,必有空明根境与智;耳不资明;鼻身不资空;独目为具五路。既见物已,虽越百旬,其像在;于是取之,谓之独影。独影者知声不缘耳,知形不缘目,故曰不当。不当者不直也。是故赖名。曩令所受者逝,其想亦逝,即无所仰于名矣。此名所以存也。”
其解说颇精,大氐类此。
然自毕氏以来,为墨学者或整理全书,或书中之一部分;虽各有精审之处,然大氐皆训故章句之学;而于墨子之学说,评论者不过千百言之叙文,略见己意而已,言墨子之非者,固自有其卓识;而言墨子之是者,亦多游移于孟墨之间;未有大声疾呼,提倡墨子学说者也。有之,自梁启超始。其于清末撰《新民业报》时,会作《墨学微》。其发端叙论云:“新民子曰:今举中国皆杨也。有儒其言而杨其行者;有杨其言而杨其行者;甚有墨其言而杨其行者;亦有不知儒,不知杨,不知墨,而杨其行于无意识之间者。鸣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之,厥惟学墨;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作《子墨子学说》。”
以墨学为救国之学说,虽似言人所未言,然俞樾于序孙氏《闲诂》云:“嗟乎!今天下一大战国也!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倘亦足以安内而攘外乎?”
则俞氏早已见及此。唯俞氏之说,似偏于战守之具‘而梁氏则大倡其学说耳。梁氏书第一章《墨子宗教思想》,第二章《墨子之实利主义》,第三章《墨子兼爱主义》,言论颇为清晰。胡适谓其能引起多数人对于墨学之新兴趣,其言良是。梁氏至民国十年,复刊行其《墨子学案》,盖为清华学校演讲而作者。其书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墨子之根本观念》,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第四章《墨子之宗教思想》,第五章《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第六章《实行的墨家》,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第八章《结论》并附有《墨者及墨学别派》,《墨子年代考》。梁氏自序谓与《墨学微》,全异其内容去。
梁氏又别有《墨经校释》,刊布于民国十一年。其书一《自序》,二《凡例》,三《余记》,四《正文》,五《旁行原本》,六《经上之上经说上之上》,七《经上之下经说上之下》,八《经下之上经说下之上》,九《经下之下经说下之下》,十《胡序》。此为张惠言后专释《墨经》之巨著。盖梁氏前二书为提倡墨子学说之论述;后一书为校释《墨子》一部分之著作。前者近于义理之学;后者近于考据之学也。兹将梁书分别论之。先略举《墨学微》及《墨子学案》之一二例如下:一梁氏于《墨学微》论墨子之政术,及《墨子学案》论墨子之新社会组织法,均引墨子《尚同·上篇》选立天子之说,以为与卢梭《民约》绝相类;谓选立为人民选择而立。其《墨学微》云:“其谓明乎天下之乱生于无正长。故选择贤圣立为天子,要从事乎一同。谁明之?民明之。谁选择之?民选择之。谁立之?谁使之?民立之,民使之也。然则墨子谓国家为民意所公建,其论甚明。中国前此学者言国家所以成立,多数主张神权起源说,家族起源说;惟墨子以为纯由公民意所造成,此其根本的理想与百家说最违异者也。”
其《墨子学案》且举墨子建立巨子之法,以为例证;而不知此乃大谬特谬。孟胜之传巨子,全为个人之传授;不足以明其为民选,适足证其为独断也。余以谓墨子之所谓选立者,乃言天之选立,非谓由人民选立也。举证如下:甲,《墨子·尚同·上篇》云:“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母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相劳,腐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虖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此段诸“选立”字,且置其选立天子之说而不论;而论其他之选立三公,立诸侯国君,选立正长;果为谁之选立乎?其云:“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云:“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又云:“诸侯国君既以立,以其力为未足”云云;此诸所谓“以为”者,天子三公以为也,诸侯国君以为也。其文义甚明。然则下文接言“选立”,乃天子选立三公;天子三公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选立正长;甚明。此皆由尊立卑,则墨子之意,以选立天子归之于天,可知。
乙,《墨子·天志·上篇》云:“庶人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士正之;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将军大夫政之;将军大夫竭力从事,未得次己为政,有三公诸侯政之;三公诸侯竭力听治,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天子为政于三公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为政于天子,天下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此文云:“有天政之”,云“天之为政于天子”,是明以天为天子之上司。而此文所云,亦皆为以尊政卑,与《尚同·上篇》所云以尊选卑者,文同一例。则彼虽不明言天选立天子;而以此文例之,则墨子之意,固以天选立天子,甚明也。
丙,《尚同·下篇》云:“此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是以厚者有关,而薄者有争。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义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孙诒让云:上“天下”二字,疑当作“天。”柱按:孙说是也。然则,此岂非墨子以选立归之天之塙证乎?又《尚贤中篇》云: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赏何也?曰: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爱之,后从而利之;又率天下之万民,以尚尊天事鬼,爱利万民;是故天鬼赏之,立为天子,以为民父母。’此则明明言天鬼立天子矣。尚可谓之民选邪?尚可谓为无神权说邪?
丁,《尚同·上篇》既云:“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倘选立者为人民,则一人选一人,二人选二人,十人选十人,安能选出一人,立以为天子者乎?
要之,墨子此论,假令以为民选天子,则亦决非初民政治所能,有违事实;如以为天选,亦远不及柳子厚封建论为有合于理;梁氏于此等处,均未阐发,不免多阿所好之言。
一,梁氏《墨子学案》第三章 论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有一段云:“我想现在俄国劳农政府治下的经济组织,很有几分实行墨子的理想。内中最可注意的两件事:第一件,他们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干涉:任凭你很多钱,要奢侈也奢不来;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第二件,强迫劳作,丝毫不肯放松;很合墨子‘财不足则反诸时’的道理。虽然不必‘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但比诸从前工党专想减少工作时刻,却是强多了。墨子说:‘安有善而不可用者。’看劳农政府居然能彀实现,益可信墨子不是幻想家了。”
依梁氏此说,则墨子直二千年以前劳农政府之先达矣。然梁氏谓“墨子的节用主义,真做到彻底了”‘语,考墨子之《节用·中篇》所言“圣王制为节用之法”云云,下文皆继之曰“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此皆与民对言,则其法为专对在位者而言可知。且云,“圣王弗为”,而不云圣王禁民不为;所称者亦为古圣王,则古圣固未有绝对干涉人民衣食住之事者,则墨子此言,亦必非如梁氏所说,都由政府干涉可知。然墨子“尚同一义”,则节用之义,亦必欲强天下之同;是梁氏之言,似亦未为大过;唯言墨子之于衣食住,尽主由政府干涉,则终属臆测,而无显证耳。
至梁氏又谓“遍查《墨子》书中并没有一个字说君位要世袭”云云,尤为不然。考《天志·上篇》云:“然则禹汤文武其得赏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柱按之通知。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爱人者此为博焉;利人者此为厚焉。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以业万世子孙为善,非赞成君主世袭而何?梁氏于是乎疏矣。
要之,近人之事,颇似商贾趋时,好以外国学说,皮传古书;往时人喜谈卢梭,故以卢梭说传会之;今人喜谈劳农政府等,故又以劳农政府等传会之。此乃近世学者之长技也。其学术之能耸动听闻者在此,其短处亦正在于此。
至于《墨经校释》,长在文字明晰,能引人入胜;依鲁胜之例,引说入经,各附其章;又以校与释分而为二;均极便学者研究。至其疏失,亦可得而言。
一、拘守《经说》必牒举经文首一字以为标题之说。故多妄加妄减。而不知《经》说固多牒经文首字为题,而亦有牒举两字者,有首句《说》与《经》文有同字而遂不举者;不必拘守一律,以削趾就履也。此条胡适已论之。
二、本前人之说而不出前人之名。如《经》上云:“勇志之所以敢也。”《经说》云:“勇以其敢于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于是也害之。”张惠言云:“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者,则命之‘勇’矣。”孙诒让云:“‘名’犹‘命’也,言因敢得‘勇’名。”而梁氏则云:“‘命’犹‘名’也。言因敢得‘勇’名。人有敢,亦有不敢;就其敢于此即命曰‘勇’;虽不敢于彼,仍不害其为‘勇’也”,其说全本张孙。又句下校释之语,亦多此类。如《经说》下云:‘极胜重也’,孙注云:“《说文·木部》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极。”《梁》注云:“《说文》云:‘极栋也。’屋栋为横木,引申之凡横木通谓之极。”梁氏此注亦全本孙氏。如是之类,未免有攘美之讥。
三、援引多讹。如《经说》上云:“不若金声玉服。”梁云:“‘不若’之‘不’,孙云疑衍”,然今考孙书本云“不”疑当作“必。”而无“疑衍”之文。如《经》上云:“间虚也。”梁本改“”作“栌。”云:“‘栌’字从孙校。”然考此条孙注引王引之云:“‘’乃‘栌’之借字。”是当云从王校而不当云从孙校也。又梁氏引张惠言云:“但就虚处则谓之栌。”今考张原本作从糸之“”,不作从木之“栌”;而梁氏既改经文“”为“栌”,并改张注之“”为“栌”,误矣。凡此皆著书不小心,或削趾就履之过。
四、改字太多之病。如《经》上云:“同异而俱于之一也。”说云:“侗二人而俱见是楹也,若事君。”梁校云:“侗”疑当作“同。”“楹”字当为“相盈”二字分写之讹。“人字”涉上“人”旁而衍。“见”字涉上文“是”字形近而衍。“事君”二字不可解。是《说》文十二字,而梁氏疑改者几过半数。如此解释古书,其意虽美,恐非古人之意也。不知此文本无一误。“侗”与“同”同,犹“侒”与“安”同。墨子之意,谓当立一以为法仪。“于”依也。“之”此也。谓人人虽异而俱依此一以为法仪也。《说》云:“二人而俱见是楹”,则譬此“一”为“楹”;以此“楹”为标准,虽二人之不同,而“俱见是楹”,以是“楹”为标准则同。“若事君”者,谓若万民之事君,而志无不同也。举“二人”为言,即仁从二人之意,多数之称也。此即《法仪》、《尚同》、《天志》之恉,不须改字而本文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