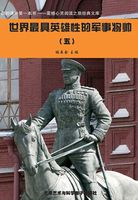星期天,11月6日来到了。这一天我准备到教母那儿去祝贺她的命名日。我跟她往来并不密切,只有在节日里才去探望她。今天她家里想必有许多客人,我指望借此排解一下这几天来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抑郁情绪。教母住得很远,在阿拉尔钦桥附近,因而我准备在天黑以前动身。我差人去叫马车,自己则坐下来弹钢琴,乐声使我听不清门铃响。一个男人的脚步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回头一望,又惊又喜,我看到进来的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显得怯生生的,好像感到难为情似的。我迎着他走去。
“您可知道,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变成什么样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这几天我一直感到很寂寞,今天一早就犹豫不定,到您家来,还是不来?来是否合适?我来得这么勤,您和您的母亲会不会觉得奇怪:星期四刚来过,星期天又来了!我下过决心不来,可您瞧,还是来了!”
“您这是哪儿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妈妈和我随时都欢迎您到我们家来!”
尽管我对他作了保证,我们的谈话还是进行得不顺利。我不能克服自己惶惑不安的情绪,只是回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问题,自己却什么也没问。另外还有使我难堪的外在原因。我们坐在没有来得及生火的大厅里,感到很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觉了这一点。
“你们这儿可真冷,您本人今天也是冷冰冰的!”他说,发觉我今天穿了件淡灰色的绸衣服,就问我准备到哪儿去。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知道我马上要去教母家,就说他不愿意耽搁我的时间,提出要用他的雪橇顺便把我送去。我表示同意,于是我们便上路了。雪橇驶到某个转弯的地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想要扶住我的腰。但是我却跟六十年代的姑娘们那样,对诸如吻女士们的手、扶住她们腰这一类关心的表示抱有成见,我说:“请别担心,我不会跌下去的!”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委屈,说:
“哦,我真希望您马上就从雪橇上摔下去!”
我哈哈大笑,于是我们便言归于好:在途中余下的时间里,我们愉快地闲聊着,我的愁绪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和我告别的时候紧紧握了握我的手,我答应过一天到他家去商量有关《罪与罚》的写作问题。
十
1866年11月8日是我一生中有重要意义的一天:这一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我说,他爱我,请求我做他的妻子。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那一天的详情细节在我的记忆中是如此清晰,仿佛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月以前似的。
这是一个晴朗、严寒的日子。我步行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家,因此,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半小时。显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等了我很久。他听到我的声音,就马上走到前室来。
“您终于来了!”他高兴地说,动手帮我解开风雪帽上的带子,脱掉大衣。我们一起走进书房。这一天,书房里十分明亮,我惊异地发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知为什么情绪激动。他脸上现出兴奋的、几乎喜气洋洋的神情,这使他显得年轻多了。
“您来了,我多么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口说,“我真担心您会忘记自己的诺言。”
“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我答应的事,总是会办到的。”
“请原谅,我知道您总是信守诺言的。又见到您了,我是多么高兴!”
“我也高兴见到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而且是在您心情这么欢快的时候。您是否碰到了什么喜事?”
“是的,有喜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个美梦!”
“就这么件事!”我笑了起来。
“请您别笑。我认为梦有重大意义。我的梦总是预兆。如果我梦见米沙哥哥米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的爱称。——译者注,特别是我父亲,我就知道我要遭难了。”
“谈谈您昨天做的梦吧!”
“您看到那只大的红木箱吗?这是在西伯利亚的朋友乔坎·瓦利汉诺夫[18]送给我的,我非常珍视它。那里面存放着我的文稿、书信和珍贵的纪念物。我梦见我就坐在这只箱子前面整理文稿。突然间,有颗明亮的小星星在文稿中间一闪。我翻阅着文稿,小星星时隐时现。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开始慢慢地把文稿一张张地翻过来,终于在它们中间找到了一颗极小的然而十分明亮、闪闪发光的钻石。”
“您拿它怎么办呢?”
“真糟糕,我记不得了!接着做了其他的梦,我就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但那是个美梦!”
“梦通常是从反面来解释的,”我说,但马上又对自己的话感到后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面色立即变了,仿佛脸上罩了一层阴云。
“那么,您认为我不会碰到什么幸福的事?这只是妄想?”他伤心地大声说道。
“我不会解梦,而且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一套,”我回答。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饱满的情绪消失了,我感到十分遗憾,竭力想使他高兴起来。他问我平日梦见什么,我便用滑稽的口吻回答。
“我梦见次数最多的是我过去中学里的女校长,一位庄重的太太,太阳穴上有一撮老式的鬈发,经常为什么事训斥我。我还经常梦见一只棕黄色的雄猫,它有一次从我们园子的篱笆上跳下来,把我给吓坏了。”
“啊,您真是个孩子,孩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笑着重复说,同时温存地望了望我,“连您做的梦也那么孩子气!那么,您教母命名日的那一天,您挺开心吧?”他问我。
“很开心。吃过晚饭后,长辈们坐下来玩牌,而我们年轻人聚集在主人的书房里,高高兴兴地闲聊了一晚上。那儿有两位可爱、有趣的大学生。”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闷闷不乐了。这一回,他的情绪变化得如此之快,使我感到惊讶。我不知道癫痫病的性质,心想,这种情绪的迅速变化是不是病将发作的预兆,我感到害怕……
我们早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当我来速记的当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告诉我,在我们分离的那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去过哪些地方。我赶紧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最近几天在干什么。
“我在考虑新的长篇小说,”他回答。
“真的吗?一部有趣的长篇小说?”
“我觉得很有趣,只是小说的结尾处理不好。这儿牵涉到一个年轻姑娘的心理。如果我在莫斯科,我就去问我的外甥女索涅奇卡[19],现在我只能求您帮助了。”
我怀着自豪的心情欣然同意“帮助”这位天才的作家。
“您那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什么人?”
“是个艺术家,这人年纪已经不轻了,一句话,跟我差不多年纪。”
“请您谈谈小说的内容,您谈谈吧,”我请求道,对那部新的长篇小说很感兴趣。
于是,应我的请求,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滔滔不绝地谈出了他那引人入胜的即兴之作。无论在这之前或以后,我都没有听到过他谈得像这一次那样热情洋溢,他越往下谈,我越清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谈的是自己的身世,只是改变了人物和环境罢了。这些事他过去曾经粗略地、零零星星讲给我听过。如今,他那详细而连贯的叙述使我知道了很多他与已故的妻子和亲属之间发生的事情。
在这篇新的小说中也讲到艰苦的童年,幼年丧父,又遭厄运(重病),疾病使艺术家脱离生活和他心爱的艺术达十年之久。后来他重新投入生活(艺术家病愈),与他所爱的女人相逢,接着是这种爱情给他带来的痛苦,妻子和亲人(心爱的姐姐)的亡故,贫穷,债务……
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他的孤独,对亲人们的失望,对新生活的憧憬,对爱情的需求,对重新获得幸福的渴望,——这一切被描绘得如此生动和完美,很明显,这是作者亲身的体验,而不只是他的艺术想象的成果。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描绘他的主人公的时候,不惜运用阴暗的色调。按照他的说法,主人公是个未老先衰的人,害上了不治之症(手麻痹症),老是郁郁不乐,猜疑心很重;虽然心肠很软,但不善于表现自己的感情;他可能是个有才能的艺术家,但却屡遭失败,一生中从未以他所想望的那些形式来体现他的思想,为此,他常常感到苦恼。
我发觉小说的主人公就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于是我便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我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为什么这样委屈您的主人公?”
“我看出,您不喜欢他。”
“相反,我十分喜欢他。他心地很好。您想想,他遭到多少不幸,却全都毫无怨言地忍受了下来!如果换了别人,生活中经受了这么多的苦难,肯定会变得冷酷无情,可是您的主人公却仍然爱人们,而且还帮助他们。不,您对他完全不公正。”
“是的,我同意,他确实有一颗善良、爱人的心。您了解他,我是多么高兴啊!”
“就这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讲他的故事,“在艺术家生活中的这个决定性的时期,他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年纪跟您相仿,或者大一两岁。如果我们不把她称作女主人公,那么,就叫她安尼娅吧。这是个可爱的名字……”
这些话使我更加确信,他所说的女主人公就是指他过去的未婚妻安娜·瓦西利耶芙娜·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我也叫安娜——我几乎没想到,这个故事跟我有关系。最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曾对我说起,他不久前收到安娜·瓦西利耶芙娜从国外寄来的一封信,新小说的题材可能是在这封信的影响下产生的。[20]
女主人公的形象与男主人公的形象不同,是以另一种色调描绘的。按照作者的说法,安尼娅温柔,聪颖,善良,乐观,待人接物很有分寸。我在那时候很看重女性的美,就忍不住问:“您的女主人公漂亮吗?”
“当然,算不上是个美人儿,但是长得挺不错。我喜欢她的脸。”
我感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泄漏了秘密,我的心发紧了。我胸中充满了对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的敌意,便说:“不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太美化您的‘安尼娅’了。难道她是这样的吗?”
“就是这样的!我深深地了解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继续讲他的故事,“艺术家经常在一些艺术团体里碰到她,他越经常看到她,就越喜欢她,就越相信,他跟她在一起会得到幸福。然而,他感到自己的梦想几乎不可能实现。事实上,他,一个衰老的病人,再加上负债累累,又有什么可以给予这位健康、年轻、乐观的姑娘呢?从年轻姑娘这方面来说,对艺术家的爱情是不是极大的牺牲,过后她是否会痛悔自己把命运跟他联系在一起?况且,一般说来,一个年轻姑娘,性格和年龄都与艺术家相去很远,是否可能爱上我的艺术家呢?从心理学方面来说,这是不真实的吧?正是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
“为什么不可能?既然您说,您的安尼娅不是个头脑空虚、卖弄风情的女人,而有着一颗善良、美好、同情别人的心,那么,她为什么不能爱上您的艺术家呢?他有病,又穷,这有什么呢?难道爱一个人只是为了他的外貌和财富吗?从她这方面来说,又谈得上什么牺牲呢?如果她爱他的话,她本人就会感到幸福,她永远也不会后悔的!”
我讲得很热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激动地望着我。
“您真的相信她会衷心爱他,终生不渝?”
他沉默了一会儿,好像迟疑不决似的。
“假如您现在处在她的地位,”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请您设想,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爱情,请求您做我的妻子。您说说,您怎么回答我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脸上现出如此惶惑不安和真诚的痛苦表情,使我终于明白,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谈话;如果我给予支吾搪塞的回答,那就会严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我朝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激动不安、使我感到如此可爱的脸瞥了一眼,说:“那我就回答您,我爱您,而且终生不渝!”
我不想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那令人难忘的时刻里所说的那些温柔的、充满爱恋的话语再重复一遍:它们对我来说是神圣的……
这巨大的幸福使我震惊,差点儿把我压倒了,我很久不能相信,这是真的。我记得,差不多过了一小时,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们未来的计划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回答他:“我此刻哪能讨论什么事!我太幸福了!!”
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有什么变化,什么时候才能举行婚礼,所以决定暂时不告诉别人,除了我的母亲。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第二天到我们家来待整个晚上,并且说,他将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我们的会面。
他送我到前室,小心地替我戴上风雪帽。我刚要走出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把我叫住,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现在才知道那钻石在哪儿。”
“奠非您记起了那个梦?”
“不,我没有记起来。但我终于找到了它,而且决心终身把它保藏好。”
“您错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笑着说,“您找到的不是钻石,而是一块普通的小石子。”
“不,我相信,这一次我错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跟我告别的时候严肃地说。
十一
我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儿回来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喜悦。我记得一路上我几乎都在大声呼叫着,忘记了过路的行人:“天啊,我多么幸福!难道这是真的?莫非这不是梦?难道他会做我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