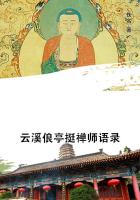街上喧闹的人声使我慢慢清醒过来,我忆起,我曾被邀请去亲戚家参加庆祝我堂弟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斯尼特金,儿科医生。命名日的午宴。我上面包铺(那时候糖果点心店很少)买了庆祝命名日的大馅饼。我喜不自胜,觉得所有的人都善良、可爱,老是想说些使人高兴的话。我控制不住自己,看到那个卖馅饼的德国姑娘,便说:“您的脸色多好啊,您的发型又那么美!”
我在亲戚家碰到许多人,但是我母亲却不在那儿,虽然她答应去赴宴的。这使我感到不快:我渴望快点把自己的喜事告诉她。
宴会上大家都很高兴,但是我的举止十分古怪:一会儿跟大家说笑,一会儿独自沉思,没听到别人对我说的话;一会儿又答非所问,甚至把一位先生称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大家开始取笑我,我推托说,偏头痛又犯了。
我的妈妈终于来了。我跑到前室去找她,搂住她,在她耳边小声说:“祝贺我吧,我要做新娘了!”
我只能说到这儿,因为主人们急着来迎接我妈妈了。我记得妈妈那天晚上不时用探究的目光朝我望,大概吃不准当时在场的我的爱慕者中间,我究竟准备嫁给哪一个。直到回到家里,我才告诉她,我要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妈妈听到这个消息是否感到高兴;我认为,她并不高兴。作为一个久经世故的人,她不可能不预见到,这件婚事将使我经受许多痛苦和磨难,这不仅由于我未来的丈夫患有可怕的疾病,而且也由于他经济拮据。但是她并没有试图劝阻我(像别人后来所做的那样),我为此很感激她。不过,又有谁能说服我放弃我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幸福,它对我们俩来说是实在的、真正的幸福,尽管在我们以后的共同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艰难和困苦。
翌日,11月9日那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什么事也做不进,老是回想着昨天我们谈话的详情细节,甚至把它记在自己的速记本里。
晚上六点半,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家,他一开始就表示歉意,说他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半小时。
“我实在等不及了,渴望尽快见到您!”
“Nous sommes logéesála même enseigne,”法语:我们俩都经受着同样的苦恼。——译者注我笑着回答说,“我整整一天什么事也没干,老是想到您,您来了,我太幸福啦!”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立刻注意到,我穿着一套颜色鲜亮的衣服。
“我上您家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您脱掉了丧服[21],还是现在仍旧穿着黑裙子。瞧您,穿上玫瑰色的衣服啦!”
“我心里那么高兴,怎能不穿这样的衣服呢!自然,在我们没有宣布结婚以前,我在公开场合还是穿丧服,而在家里,为了您,我要穿得鲜亮一点。”
“玫瑰色和您挺相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您穿着这衣服显得更年轻了,就像个小姑娘。”
看来,我那年轻的模样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感到不安。我就笑着向他断言,我马上就会变老的,虽然这是说着玩的,但是在我的生活中,由于种种情况,这句预言终于应验了。说得更确切些,我不是变老,而是竭力使我的穿着和谈吐显得那么老成持重,以致我和我丈夫年龄之间的差距很快就不易被人察觉了。
我的母亲走了进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吻了吻她的手,说:“您想必已经知道,我向您的女儿求了婚。她答应做我的妻子,这使我感到万分幸福。我希望您能同意她的选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说了您那么多好话,使我一直对您怀有敬意。我向您保证,我一定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同时,我要做您的最忠实、最热诚的亲属。”
应该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句公道话,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十四年间,他对我的母亲一直很孝敬、亲热,真诚地爱她,尊敬她。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这短短的几句话时,态度庄重,但有点慌乱,他后来自己也发觉了这一点。妈妈深受感动,拥抱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求他爱我、保护我,她甚至放声大哭起来。
我赶紧插话,使这个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可能有点尴尬的场面不再继续下去,我说:“亲爱的妈妈,请您快点给我们准备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冻坏了!”
仆人端来了茶,我们手中捧着杯子,舒舒服服地坐在柔软的老式圈椅里,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起天来。
过了将近一个钟头,传来了门铃声,女仆通报说,来了两个年轻人——我们家的常客。此刻,这两个不速之客的来临使我十分恼怒,我请求我的母亲:“妈妈,请您去对他们说,我很抱歉,此刻在头痛。”
“请让他们来吧,安娜·尼古拉耶芙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断了我的话,转过身来对我轻声说,“我想看到您和年轻人相处。直到现在为止,我只看到您和我们这些老头儿在一起。”
我微微一笑,要女仆招呼客人们进来。我向他们介绍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且道出了他的姓名。年轻人出乎意外地碰上了一位名作家,心里有点儿发憷。他们看到我们这儿有点节日的气氛,为了说明原委,我就对客人们说,他们恰巧赶上我们在庆祝我们共同的工作——一部新小说的完成。我很想引大家说话,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参加进去。一个年轻人问我,昨天我害偏头痛,现在是否好了,我就抓住这个话题,说:“我头痛,这都怪您,因为您老是吸烟,吸得太多了。不应该多吸烟,您说对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这我没法儿评判,因为我自己吸烟就多。”
“可这对健康不是有害吗?”
“自然有害,但这是一种习惯,很难去掉。”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单单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没法儿引他再谈下去了。他吸着烟,不时探究地朝我和客人们望望。两个年轻人有点发窘了,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使他们敬畏。客人们说,昨天我离开亲戚家后,大家作出决定,打算去看谢罗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罗夫(1820—1871),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友好关系。的《犹滴》,委托他们来打听一下,我哪天有空,以便去订包厢。
我很客气地,但又坚决地表示,我不准备去看歌剧,因为我眼前得加紧学习速记,以便追上同学们。
“那么,11月15日那天的音乐会是否准备去呢?您可是答应过我们的!”两个年轻人不痛快地说。
“由于同样的原因,音乐会我也不准备去。”
“可是您去年在这样的音乐会上却显得兴致勃勃。”
“还提去年的事!从那时候起,多少日子过去啦,”我用教训的口气说道。
两个年轻人感到待在这儿是多余的,就站起身来要走了。我没有挽留他们。
“好啦,您对我满意了吧?”客人们走了以后,我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您叽叽喳喳,就像小鸟儿似的。只可惜您断然放弃您过去感到兴趣的一切,就此把爱慕您的人给得罪了。”
“去他们的!我现在才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呢!我只需要一个人:我珍贵的、心爱的、卓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我对您来说是这么珍贵、这么可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道,于是亲切的谈话重又开始,持续了整个晚上。
那是何等幸福的时光,当我忆起它的时候,我是多么深切地感谢命运之神啊!
十二
我们决定把我们订婚的事向亲友们保密,但是这个决定只维持了不过一星期。我们的秘密非常意外地被揭露了。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家的时候,他所乘的出租马车是按钟点租用的,从七点到十点。马车往返的路程比较长,在这段时间里,对普通老百姓抱有好感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常总是跟马车夫聊天。他渴望向人诉说自己的幸福,就把自己的喜事讲给车夫听。有一次,他从我们那儿回到了家,在口袋里找不到零钱,便对车夫说,他马上派人把钱送去。女仆拿着钱出来了。大门口站着三个马车夫,她不知道该把钱付给哪一个,就问,刚才是谁把“老爷”送来的?
“您说的是快要当新郎的那位先生吗?是我送来的。”
“什么新郎?是我们老爷,不是新郎。”
“是新郎!他亲口告诉我,他快要当新郎了。我连新娘都见过啦,那是在她打开大门的时候。她把他送出来,高兴得什么似的,老是在笑!”
“你是从哪儿把老爷送来的?”
“从斯莫尔尼宫附近。”
费多西娅知道我的地址,猜到了她老爷的新娘是谁,便赶紧把这消息告诉了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
第二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我述说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况(他详细地询问了费多西娅),而且说得那么有声有色,使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我问,他的继子对我们订婚的消息有什么想法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面有难色,看样子,他不希望我详细打听。我却坚持要他谈清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哈哈大笑起来,向我讲述,这天早晨帕沙帕沙是帕维尔的爱称。——译者注来到他的书房里,身上穿一套礼服,鼻子上架着一副蓝色的眼镜,通常只有在隆重的场合,他才会这样穿戴。他告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听说继父即将结婚;这个决定对他有着切身的关系,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竟然不同自己的“儿子”商量一下,征求他的意见,这使他感到震惊,诧异而且愤慨。“儿子”请“父亲”想一想,他已经是个“老头儿”,不论按年龄或精力来说,他已无法建立新的生活;“儿子”还提醒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有着别的义务,等等,等等。
据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讲话的口气“傲慢,夸张,带着教训人的味道”。继子的这种口吻气得他失去了自制力,他叫嚷起来,把继子赶出了书房。
过了两天,我得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病,来到他家里,他的继子没有出来见我。他在餐室里移动着什么东西,弄出很大的声响,还怒气冲冲地骂女仆,为的是要我知道,他在家。到下一次我去(过了一星期)的时候,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大概遵照继父的吩咐,走进书房来,向我冷淡而生硬地祝贺,过后,约莫有十分钟,一声也不吭,现出委屈和愁闷的样子。可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一天的情绪却特别好,我也很愉快,我们俩感到那么幸福,压根儿就不去注意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那严肃而矜持的神情。后来,他发觉他那冷冰冰的样子不能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而只能惹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便开始对我客气、殷勤起来,虽然也不放过机会对我说几句挖苦的话。
十三
对我们来说,订婚以后那段幸福的时光一转眼就过去了。从表面上来看,日子过得挺单调:我借口速记工作紧张,随便哪家都不去,也不请任何人来做客,既不参加音乐会,也不上剧院。只有一个晚上是例外,那一晚上演阿列克赛·托尔斯泰阿列克赛·康斯坦京诺维奇·托尔斯泰(1817—1875),俄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伯爵的剧本《伊凡雷帝之死》,我去看了戏。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推崇这个剧本[22],想跟我一起去看戏。他订了包厢,除了我,还邀请了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和她的子女们以及帕维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无论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交流观感使我多么愉快,但是有这些对我不友好的人在场,我总觉得苦恼。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公开表现出自己的反感,到头来,我终于感到十分沮丧,这立即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发觉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推托说,头痛得难受。
然而,这个不愉快的夜晚并不能破坏我幸福的情绪。我的心里总是感到无上的幸福。我过去老是自己找活儿做,现在却什么事也不干。我整天思念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忆前一天跟他的谈话,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今天再来。他通常七点钟到我家,有时候是六点半。他来时,桌上的茶炊总是滚开的。冬天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我们这儿路远,我担心他会受凉。他一走进房间,我就赶紧递给他一杯热茶。
我认为他每天来看我是一种很大的牺牲,我怜惜他,就违反自己的意愿,劝他有时候隔天来。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向我断言,到我们家来在他是一种乐趣,他待在我这儿感到精神愉快,内心平静;他要每天来看我,除非我认为这样做对我是一种负担。他这话是说着玩的,因为他知道我看到他总是乐得什么似的。
喝过茶,我们就在古老的圈椅里坐下来,而在我们中间的小桌上放着各式各样的点心和糖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每晚总带来从“芭蕾”(他喜爱的一家糖果店)买来的糖果。我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手头拮据,劝他不要带糖果来,但是他认为未婚夫送礼物给未婚妻是一种古老的良好习俗,他不应该违反它。
我也经常准备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所喜爱的梨子、葡萄干、海枣、杏干、软果糕,数量不多,但总是又新鲜,又好吃。我特意亲自跑商店,寻找一些不常见的东西,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尝新。他觉得惊奇,肯定地说,只有像我这样的美食家才能觅到如此的美味。我却硬说他是个大美食家,临了,我们还是不能断定,我们之中到底哪一个在这方面更应受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