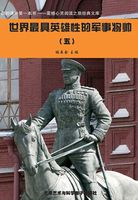11月1日——把长篇小说送交斯捷洛夫斯基的日子快到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担心这个家伙会忽然玩起花招来,找借口拒绝接受原稿,以达到取得违约金的目的。我竭力安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打听一下,如果他的猜想成为事实的话,他应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晚上,我请求母亲去找一位熟悉的律师。他建议把原稿交给公证人或者斯捷洛夫斯基所居住的那个行政区的警察分局长,不过,当然必须获得官方人士的签字证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向他同学的哥哥,调解法官弗列伊曼求教,后者给他出了同样的主意。
七
10月29日,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口述和笔录。长篇小说《赌徒》完成了。从10月4日起到29日,即在二十六天的时间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写了一部七印张、每面两栏、大开本的长篇小说,篇幅相当于通常的十印张。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此非常满意,告诉我,如果原稿能顺利地送交斯捷洛夫斯基,他打算在饭馆里请朋友们(迈科夫、米柳科夫等)吃饭,并且预先邀我参加这次宴会。
“你上过馆子吗?”他问我。
“不,从来没有。”
“那么,我请客吃饭,您来吗?我要为我亲爱的合作者的健康干杯!要是没有您的帮助,我就不可能按时写完这篇小说。您说,您肯来吗?”
我回答说,我得征求母亲的意见,而心里却决定不去。由于腼腆、怕生,我就会显得落落寡合,这将影响大家的欢乐情绪。
第二天,10月30日,我给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来了整理好的昨天的速记稿。不知怎的,他见到我的时候显得特别亲切,甚至我一进屋,他的脸就涨得通红。我们照例计算了一下写好的页数,发现完成的数字不少,比我们预料的要多,这使我们高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他准备当天把小说重读一遍,作某些修改,第二天早晨送交斯捷洛夫斯基。就在这时候,他把说定的五十卢布酬金付给我,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同时为了我与他合作而热烈地向我道谢。
我知道,10月30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生日,因此,我换下日常穿的那件黑呢子衣服,穿上一件紫色的绸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到我平时总穿着丧服,今天却换了装,以示对他的关怀,他心中十分欢喜,而且觉得紫色和我很相配。我穿了长的连衣裙显得个子高了一些,身材也更匀称了。我听到他的赞扬感到欣喜万分,但是这种喜悦的心情却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哥哥的遗孀——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本姓季特马尔;1822—1879),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来到破坏了。她是来祝贺他的生日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介绍我和她认识,并且告诉自己的嫂子:多亏我的帮助,他才能按时写完小说,从而摆脱可能遭到的灾难。尽管他说了这些话,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对我的态度却冷淡而傲慢,这使我感到惊异和委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喜欢他嫂子那种不友善的语调,因而对我格外亲切和殷勤。他建议我翻阅一下刚出版的某本书,然后把他的嫂子领到一边,给她看某些文件。
阿波隆·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走了进来。他向我点头致意,但显然没有认出我来。于是迈科夫转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及他的小说的进展情况。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正在和嫂子谈话,大概没有听清他的问题,因而没有作答。这时候,我就决定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说,小说昨天就已完成,我刚把整理好的结尾一章带来。迈科夫很快走到我跟前,伸出手来,对他没有立即认出我来,表示歉意。他解释说,这是由于他眼睛近视,也由于他觉得上次我穿着黑衣服,个子显得比此刻矮的缘故。
他开始详细打听有关小说的情况,并且询问我对它的看法。我热烈地谈论这个新的、我所珍爱的作品,说其中有几个异常生动、塑造得很成功的典型(老祖母、阿斯特列伊先生和在恋爱中的将军)。我们谈了二十分钟左右,我觉得跟这个亲切、善良的人谈话极其轻松愉快。迈科夫对我的殷勤态度使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感到诧异,甚至有点难堪,但是她那冷淡的语调却没有改变,大概她觉得对一个……速记员如此殷勤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
迈科夫很快就走了。接着我也起身要走,不愿再忍受埃米莉娅·费奥多罗芙娜对我的傲慢态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竭力劝我留下来,尽可能缓和他嫂子对我的生硬态度。他送我到前室,并且提醒我,不要忘记请他到我家去的诺言。我再次表示欢迎他去。
“那么,什么时候我能来呢?明天?”
“不,明天我不在家,一个中学里的女同学请我到她家去。”
“后天呢?”
“后天我要去上速记课。”
“那就得11月2号啦?”
“2号,星期三,我要去看戏。”
“天哪!您所有的日子都没空!听我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认为您是故意这样说的。您只是不要我去罢了。请对我说实话!”
“不是这么回事,我向您保证!欢迎您到我们家去。请您11月3号,星期四晚上七点左右来。”
“要到星期四?还得等那么久!没有您在身边,我会感到多么寂寞!”
我自然把这些话当作友好的玩笑。
八
就这样,我那无上幸福的时光过去了,寂寞无聊的日子接着来到。在这一个月里,我惯于喜滋滋地赶去工作,轻松愉快地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会面,兴致勃勃地跟他交谈,这已经成了我的需要。我对原先日常所做的事失去了兴趣,觉得它们微不足道和不必要了。就连约定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访这件事也不能使我高兴,相反,却令我苦恼。我明白,对一个聪明睿智、天才横溢的人来说,不论我那好心的妈妈还是我,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有趣的谈伴。如果说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谈话迄今一直进行得很热烈,我认为那只是由于这些谈话始终围绕着我们俩都感兴趣的事业这个中心。而现在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将作为客人来到我们这儿,对客人一定得“招待”,引起他的兴趣。我开始考虑我们未来的话题,想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赶到我们郊区已经十分疲劳,再加上乏味地度过一个晚上,这一切给他这个特别敏感的人留下的印象将会冲淡他对我们过去相交的回忆,他会觉得自己不该要求这种乏味的结交,——想到这儿,我就感到难受。我很想见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然而又希望他忘记要来访问我们的约言。
作为一个乐观的人,我想方设法给自己解闷儿,排遣自己的忧郁情绪,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打消不安的心理:我访问女友,第二天晚上则去听速记课。奥利欣一看到我,就祝贺我胜利完成工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给奥利欣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并且感谢后者介绍了速记员,说他借助于速记员才得以顺利地写完自己的长篇小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谈到,这种新的工作方法对他来说挺合适,他打算今后还要运用它。
星期四,11月3日,我一早就开始做招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准备工作:采购他喜爱的那种梨和他曾请我吃过的各种糖果点心。我整天觉得心神不定,快到七点的时候,我激动不安到了极点。可是钟打过了七点半,八点,他还是没有来,我已经断定,他改变了主意,或者忘记了自己的约言。到了八点半,急盼的铃声终于响了。我赶忙去迎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问他:“您是怎么找到我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啊,终于找到啦,”他和蔼可亲地说,“听您说话的口气,好像我找到了您,您还感到不满意呢。要知道,我从七点起就开始找您,我走遍了郊区,向所有的人打听。大家都知道这儿有一条科斯特罗姆街,可是怎样走法就说不清楚了。科斯特罗姆街在尼古拉耶夫医院后面,穿过医院的大门上这条街是最近的路。晚上医院的大门上了锁,那就只能从斯隆诺夫街(现名苏沃洛夫大街)或小沼泽街进入这条街。——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谢天谢地,总算碰到了一个好心人,他坐上赶车人的座位,指点车夫怎样走。”
我的母亲进来了,我就急忙向她介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彬彬有礼地吻了吻她的手,说他十分感谢我对他工作的帮助。妈妈动手倒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便告诉我,他向斯捷洛夫斯基送交原稿时是多么提心吊胆。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斯捷洛夫斯基耍了花招:他到外省去了,仆人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那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上斯捷洛夫斯基的出版办事处去,打算把原稿交给办事处主任,但是后者断然拒绝接受,说他的主人没有授权他办这件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找公证人,但去晚了,而在警察分局,白天又见不到领导,那儿的人要他晚上去。这整整一天他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直到晚上十点钟,他才得以把原稿交给N区的警察分局,从警长手里拿到一张收据。
我们开始喝茶,谈得像平日那样愉快和从容。我先前想好的话题不得不放到一边,——引人入胜的新话题太多了。我的母亲起初对一位“著名”作家的来访有点发窘,此刻却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完全吸引住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具有令人心醉神往的本领,后来我经常注意到人们,甚至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们,怎样被他的魅力所制服。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还顺便对我说,他想休息一个星期,然后着手写《罪与罚》的最后一部。
“我想请求您的帮助,善良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我跟您在一起工作十分愉快。我以后也想口述,让您速记下来,希望您不要拒绝做我的合作者。”
“我很乐意帮助您,”我回答,“可是不知道奥利欣的看法怎么样。也许他准备让别的男同学或女同学去干您那儿的新工作。”
“可是我对您的工作方法已经习惯,对它特别满意。如果奥利欣忽然想要给我介绍另外一个可能跟我合不来的速记员,那就叫人奇怪了。不过,也许你不想再在我那儿工作?要是这样,我自然不勉强……”
他似乎感到不痛快。我竭力安慰他说,奥利欣大概不会反对我干这项新工作,但这件事还得问一下奥利欣。
将近十一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准备走了,他在告别时,我答应他第一次去上课时就和奥利欣交换一下意见,然后写信告诉他。我们极友好地分别了,由于我们刚才谈得十分热烈,我回到餐室的时候,满心喜悦。可是没过十分钟,女仆进来了,告诉我,有人在黑暗中把那辆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的雪橇的脚垫偷走了。车夫发急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答应给他赔偿,他才安下心来。
我当时还很年轻,这个插曲使我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样的事件会影响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不愿意再到这种荒僻的地方来,像他的马车夫那样遭人抢劫。想到这个晚上过得如此美好,而美好的印象却被令人遗憾的偶然事件所破坏,我难过得掉下泪来。
九
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访问我家的翌日,我到我姐姐玛丽娅·格里戈利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家去待了一整天,把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姐姐和姐夫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我白天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那儿工作,晚上又得誊写记录稿,只能偶尔和姐姐玛莎玛莎是玛丽娅的爱称。——译者注见面,因而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跟她讲。姐姐听得挺专心,常常打断我的话,仔细地询问一切,她看到我精神特别振奋,便在我临走时对我说:“纽托奇卡,你这样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什么好处。要知道,你的幻想不可能实现。他是一个身体有病、家庭负担很重、债台高筑的人,不能实现倒是一件幸事!”
我热烈地反驳说,我根本没有“钟情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什么“幻想”,只是喜欢跟这个聪明睿智、才气横溢的人谈天,感激他经常对我关心和爱护。
然而,姐姐的话使我惶惑不安,回到家里,我就问自己:难道姐姐说得对,我真的“钟情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吗?难道这是我至今未曾体验过的爱情的开始?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多么狂妄的幻想啊!难道这可能吗?如果这真是爱情的开始,我该怎么办呢?我是否婉言谢绝他提供给我的工作,今后不再和他见面,不再想到他,埋头于工作,设法逐渐把他忘掉,从而使自己的心灵恢复昔日的宁静,而这种心灵的宁静是我一直珍视的?不过,也可能玛莎错了,我的心并未受到骚扰。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有什么理由放弃我所极其想望的速记工作,放弃伴随工作而来的那些亲切和有趣的谈话呢?
而且,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已经习惯于以他口授、我速记的方法写作,现在却要让他失去速记术的帮助,那太令人遗憾了;何况据我所知,在奥利欣的男女学生中间(除了两个已经有固定工作的人以外),不论就记录的速度还是如期交出文字稿来说,没有人能完全代替我。
所有这些思想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使我感到惊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