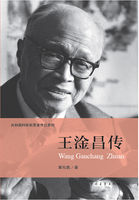[22]符·谢·索洛维约夫的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881年第3、4期的《历史导报》上,后来又于1881年在彼得堡出单行本,由阿·谢·苏沃林出版。有关符·索洛维约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会的情况,亦可参阅符·谢·索洛维约夫的《日记》,《未发表的同时代人书信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者:Л。Р。兰斯基,《文学遗产》,第86卷,页423—426。
[23]此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留下空白,准备援引伊·伊·扬茹尔的回忆录,但是忘记填写了。莫斯科大学教授伊·伊·扬茹尔在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他的语调之所以如此不友好,其原因在于:伊·伊·扬茹尔和莫斯科大学的多数教授一样,属于自由主义的西欧派,他们尖锐地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0年5月28或29日,在举行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的前几天,从莫斯科写给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中说:“主要的是,我所需要的不只是俄罗斯语文的爱好者,而是整个我们这个派,整个我们已经为之奋斗三十年的思想,因为敌对的那一派(屠格涅夫、科瓦列夫斯基以及差不多整个大学)显然想否定人民性本身,降低普希金作为俄国人民性的表达者的意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通信集》,页328)所谓莫斯科大学里“敌对的那一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可能不止是该校的社会学和历史学教授М。М。科瓦列夫斯基,而且还有伊·伊·扬茹尔。顺便说说,科瓦列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演说亦持否定意见。(参阅《К。Α。季米里亚泽夫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7年,页538—558)
[24]新闻记者、民族志学者和旅行家格·亚·德沃朗的回忆录载于《昔日之声》杂志,1914年,第4期,页122—135,标题为《往事随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格·伊·乌斯宾斯基……)。
[25]这篇题为《与陀思妥耶夫基斯的三次会面》的回忆录出自后来的教会历史学家亚·阿·泽列涅茨基的手笔。这篇回忆录的片断现保存于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亚·阿·泽列涅茨基回忆道:“我当时还是个圣彼得堡神学院的十分年轻的学生。
“那是在受难节。我忽然想起去大修道院参加晚祷。需要指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的礼仪特别隆重:教徒们不是抬着圣像巡游,而是把圣像从一个教堂(圣灵教堂)送往另一个教堂(圣三一教堂)。举行此项仪式时,由主教亲自抬圣像,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唱诗。圣诗唱得那么动听,以致有许多人老远跑来听。自然,要从头至尾看到仪式的全过程,得去圣像从那里抬出的圣灵教堂,然后跟人们一起把它送往圣三一教堂。但是我有个习惯,总要先进大修道院去,吻一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圣骨,因为过后人山人海,我就难以如愿以偿了。
“我走进大修道院,吻了圣骨,已经向门口走去,蓦地看到了一个穿皮大衣的人,他显然在等待什么,焦急不安地环视着四周,他那尖锐、迅速转动的眼睛正在东张西望。我觉得他有点面熟。看到他在等待或寻找着什么,我就向他走去。
“要是您在找圣骨,那么,它在那儿,在唱诗班席位的右首,”我说,用手指了指。
“不,”他说,我在等待抬圣像的仪式;但是很奇怪,已经两点钟了,连一个人也没有。不像在做准备工作的样子。
圣像不是从这个教堂抬出去,而是从另一个教堂抬到这儿,抬着圣像巡游的仪式在晚祷以后举行,全部准备工作将在晚祷的时候完成。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是从哪个教堂抬出来呢?这里教堂不止一个啊。
您跟我一起走吧;我领您去,反正我们是同路。
“非常感谢您,”这个陌生人高兴地说,我们走吧,走吧。
“我们就举步走,很快便走到圣灵修道院。我把大门指给他看。
“多谢您啦!我不知道怎样酬谢您才好。如果您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的话,我愿意帮助您。这是我的名片。欢迎您来找我,不用客气。”
卡片上印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急忙跟着他走进了教堂。
这时候,圣像从祭台上抬出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柱子旁边,望着圣像,不停地在自己胸前画十字,泪如雨下。他脸上表现出深受感动的神情随后,人流把我卷走,我就看不见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了下面是我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三次,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况:那期间,我已开始写点东西。当时,我的诗作发表在科罗普切夫斯基出版的《言语》杂志上。但是我觉得光发表短诗是不够的,我还打算写长诗。这是一篇不高明的、粗糙的作品,但从头至尾充满了对人民和青年学生的爱。我在写这首长诗的时候,好像觉得它会成为一篇杰作,但是当我写完以后,我自己发现长诗写得不好。于是我对自己是否有才能,产生了疑问。
这个问题使我忐忑不安。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使我同样感到不安(也许,使我不安的程度超过前者),那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真实性、灵魂的不朽以及精神生活的必要性问题。
我在童年时笃信正教,但是过了十六岁,当时一般年轻人迷恋达尔文、斯宾塞和进化论,这种迷恋也影响了我,于是我就成了个怀疑主义者,虽然我仍按照习惯去教堂望弥撒。我不否认道德,虽然我觉得没有宗教,只讲道德是不行的。据我了解,即使在无神论的体系中,也有很多漏洞。除此以外,我对民粹主义这个问题也感兴趣。
于是我就决定带着自己的疑问去求教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乐意接待当时那些专门带着各种问题去请他解决的青年们。
他当时住在库茨涅茨胡同。
我登上楼,打了铃。
“一个女仆出来开门。
“您找谁?”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贵姓?”
“就说有个大学生来访。”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
“请进。”
我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房。我记得,我起初没有去注意房内的陈设,到后来才看到窗子旁边的一张宽阔的写字台,一个放书的格子柜,桌子上的一大堆书和角落里托架上的一个普希金的胸像。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间书房的主人身上。高个子,白皮肤,未戴帽子,脑门上端微秃,俄罗斯人的脸,浅红褐色、十分稀疏的胡子,中间杂有几茎白须。右面脸颊上有个痣。一双聪慧、敏锐的灰色眼睛。
“您好,您有什么事啊?”他看到我慌了神,不知说什么好,便用亲切的语调问。
“请坐。”
我马上把手伸进自己常礼服的侧面口袋里,从那儿取出一首长诗和几首小诗。
“您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如果您没有困难的话,是不是费神把它们看一下,告诉我,我有没有才能。”
“想发表吗?”
我作了回答。
他把几首小诗很快地浏览了一遍。
“短诗您可以继续写,以后您会逐渐有所提高……可这是什么?长诗?如今没有人写这种东西了。”
他匆匆地把长诗翻阅了一下,看了看开头、中间和结尾。
“嗯,这首诗写得不好。看来,您不了解生活,您完全是个阅历很浅的孩子。我建议您放弃长诗,写些短诗,而小说呢,到您真正了解生活之后再写。显然,您有表达能力,但是您对生活还根本不熟悉。即使熟悉生活以后,您最好还是写您亲自经历过的事,而不写那些听来的传闻:您有所谓主观的才能。我再重复一遍:您暂缓写小说,先得观察生活,深入考虑它的各种现象,更要倾听自己的心声……再过五年或十年,您就可以动手写小说了。”
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道了谢。
“您要跟我说的就是这件事吗?”他问。
“不,我还没有跟您谈我来求教的最主要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于是我就详细地向他作了自白,谈了自己的信仰。
我说完以后就不再作声,惊慌不安地望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他沉默着,忧郁地、带着责备的意味摇摇头。
“您是哪个学校的?”
我告诉了他。
天哪!甚至在那里也会产生无神论的想法?
于是他重又忧郁地摇摇头
“1881年1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了。我和一个同学前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所。这一次接待我们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她擦去满脸的泪水,把我们领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其中长眠的灵柩边他的安魂祈祷仪式是在我命中注定初次与他相见的那个教堂里举行的;也就在那儿,我最后吻别了他。”(《历史导报》,1901年,第3期,页1021—1022,1025—1026,1028—1029)
[26]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政论家尼·尼·菲尔索夫用笔名“Л。鲁斯金”发表的回忆录的篇名为《在〈俄国言论〉杂志编辑部(回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的进步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