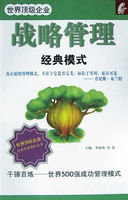像这样发人深省的文章,当然不能见容于蒋介石对于“民主”的认知与度量之上。雷震逐步迈向所谓的“叛乱”而入狱,对于了解当时政治环境的人士而言,丝毫不足为奇。
再从现实层面来说,雷震主要是因筹组新党而入狱,因为他的动作很明显会威胁到蒋氏父子的江山。
明显的是,雷震在筹组反对党的最后阶段,已被情治单位牢牢盯住了。据说,雷震等人在当时台北市衡阳路附近的新蓬莱饭店聚谈时,其谈话内容立即就被情治单位完全知悉,并上报最高当局。当局得悉新党即将成立时,乃不得不先下手为强。可是,国民党方面却否认是因雷震要组党而抓他入狱,然几乎没有人相信国民党的这种说法。
于是,在雷震、傅正两人被捕之后,参与筹组新党的李万居、高玉树曾发表声明:“……我们对雷震、傅正两先生之被捕,深感惊异,虽当局一再声明彼二人之被捕,系由于《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叛乱,而与筹组新党无关,但衡以下列事实,我们对当局此项声明实难置信:
(1)台湾警备总部逮捕雷震所引起之文字多系《自由中国》早经发表者,是项言论如有罪嫌,当局何不早依出版法予以处理,而必须于新党成立前夕采取行动?
(2)雷震、傅正若只因《自由中国》言论涉嫌,在逮捕彼等时,何以将存于自由中国社及傅正处之有关新党成立宣言及其他文件亦一并搜索而去?雷震为筹组新党主要负责人之一,傅正为筹组新党之秘书,今竟同时被捕而犹谓与筹组新党无关,其谁能信?……”从这段声明之中,就更能道出雷震被罗织罪名而入狱的主要原因了。
雷震究竟是否被罗织罪名,只要从军事法庭不准他和诬攀他的刘子英对质一事,便可获得充分的证明。同时,又拒绝雷震辩护律师梁肃戎一再要求与刘子英谈话,显示出当局的“心虚”。仅此一端,便可使真相大白,其他均已无关重要了!
至于蒋介石是否直接介入雷震案,从目前的相关史料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监察主管部门的调查小组要见雷震竟由于未获蒋介石同意而功败垂成。
前《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被捕入狱的整整四十二年后,台湾有关机构公布了当年情治单位处理雷震等人涉嫌叛乱案的机密文件和传闻中已被烧毁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相关档案证实了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已如上述,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相同。
多项文件显示,情治单位自1958年起即组成“田雨”及“支流”项目,研究《自由中国》的每一篇文章可能涉及的罪名与法条,结果多半只能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主要起诉理由,警总于是建议“应在法律制裁途径之外另先觅适当对策”。等于在尚未逮捕雷震之前,在仿真作业过程中,警备总部进行多项假想作业,警备总司令黄杰在1960年5月21日的会议中明确表示“上级已有对策与处理办法”,6月2日警总进一步拟定起诉雷震等人的假想作业。
警总拟定出甲、乙两案均以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为由,甲案计划以殷海光与雷震为起诉对象,乙案则扩大至夏道平与张益弘,这份假想作业的最后一条意见点出,“田雨(雷震)为本案主要目标,不能使其逃脱责任……防止将来被告互相串供狡辩,利用空隙使田雨脱免刑事责任”。
为了顺利定罪,警总于6月7日制定了《对雷震案处理工作要领》,由中六组、王师凯办公室、“总政治部”、情报局、调查局、警备总部、安全局抽调人员组成专业幕僚小组,在策略上分化胡适与雷震之关系,对岛内外友党及其他异见分子,采取拉拢或逼迫等诸般手段,使在本案处理时不致对雷震等发生声援情事,并以岛内为优先。
这份《要领》明确要求应透过各种关系切断雷震与当局的既有关系,并设法予以隔绝;善后处置部分则指出,处理时迅即公布起诉书或发表声明以释群疑;对各友党与国际方面斟酌情形,作个别的非正式说明,强调是法律事件而非政治事件;严防反党反台湾当局的教授、学生借机滋事;国民党及当局对此一事件应表明依法办理,避免公开答辩,如有借机叫嚣或引起国际误解,以秘密说服民、青两党或党外知名之士代为答辩为宜;如封闭《自由中国》须于事前对胡适、毛子水等予以纾解,使不致另生枝节。
7月2日,由安全局出面主持联席会议,确定由警总军法处负责“法律研究”。7月7日,军法处定出日程,“以三个月为期,自1960年7月至9月底为止”,并要求保安处评估安排杂志社内部人员揭发犯罪行为搜集罪证的事宜。一直到9月4日,以“涉嫌叛乱”为由,分别逮捕雷震、马之骕、傅正、刘子英四人。9月5日,警总声称经长时间说服恳谈,刘子英伪心承认受共产党之命来台担任间谍的所谓“实情”。于是雷震多了一项罪名,即“包庇叛徒”。一个月后,也即10月8日,军事法庭判决雷震以“知‘谍’不检举及连续以文字为有利叛徒之宣传罪”处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
雷震系狱整整十年。十年间,雷震撰写了多达400万字的文稿,却在刑满出狱前夕,被新店军人监狱没收,下落不明。1988年4月14日雷震的妻子、“监委”宋英于“监院”提案,要求重新调查雷震案并公布当年调查报告附件,没想到在4月30日却传出,除了日记外,雷震的其余文稿全遭烧毁。
今日探讨蒋介石整肃雷震的缘由,在时机上是十分合宜的,主要是当年许多当事人目前仍然健在。如果有所不实,他们自可引经据典地加以澄清,让后世子孙能够真正明白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处的政治环境而引以为鉴。
7翻案失败与时机解读
解严后给雷震翻案的呼声频起,但也遭到保守派的反扑。曾任“司法院”副院长的保皇派汪道渊,就对新闻界表示,当年雷震案发生时,他正好是覆判局局长,自认与雷震初审案关联不大。汪道渊对于外界的某些传言力加澄清,特别谈到了近日一连串的翻案风,大家几乎都将箭头指向蒋介石。他很不以为然地认为,蒋介石日理万机,不可能事事处理。如果都将不当的处理结果推给最高当局,未免太不“厚道”。
然而事实证明,翻案矛头不得不指向蒋介石!
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汪道渊不但有权利发表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许多人都十分欢迎他以当事人或以接近权力核心人士的身份澄清事实真相。不过,汪道渊绝不能仅要求大家去看当年的起诉书、判决书及调查报告,以了解所谓的事实真相,因为目前已有太多的事实证明那些东西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除了汪道渊认为一连串的翻案风对蒋介石父子不太厚道之外,也有人担心如此发展下去,将有动摇台湾根本之虞,则非许多有识之士所能苟同,其理由如下:
(1)在几十年来政治强人的领导下,任何敏感事件,莫不在蒋介石父子的直接控制与指挥之下进行,非其他任何人所能作主,有关的党、政大员充其量只不过是许多冤案、错案的“帮凶”而已,怎能不让翻案的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父子?
(2)明明已知许多冤案诸如孙立人案、雷震案都是蒋介石父子的“杰作”,但社会广大民众只是希望了解事实真相,并还当事人清白而已,并无追究蒋介石父子责任的意思。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包括最激烈的政治反对人土在内,都还没有提出迁走中正纪念堂以让出台北市最精华地段的主张,可见广大民众对蒋介石仍然极为“厚道”。当然,蒋经国晚年的表现,尚称良好,也是大家“厚道”的原因之一。
(3)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初,确曾冤杀与错杀了不少无辜而善良的人士,主要是对当时的间谍估计得实在太多了,难免会有“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心理。办案人员长期在这种观念的熏陶下,碰上孙立人案、雷震案等,也就难免比照办理。
一连串翻案风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对当事人而言,固然在还其清白;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主要是想了解事实真相以满足其好奇心理;然而,关心未来政局发展的有识人士,则另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在于检讨过去,警醒目前的当政者,千万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将来必遭谴责。因为连“政治强人”都逃不过社会大众批评的命运,遑论其他?所以,雷震案的意义在希望当今有权的人士,不要企望当什么“政治强人”,真正能够发挥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服务人生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如此一来,这一连串的翻案风,自将别具意义。
另外,对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整肃雷震,有一些声音认为:“因为当权派对民主有不同的辩解。”
蒋介石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并矢志推行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似大异其趣。有人指出,军人及情治系统人员在这位国民革命之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每当办案时遇到有读书人指责其不符民主程序时,他们会说,民主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其中竟然有人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主’,你们一般民众就是‘民’,两者合组成一个社会时,你们这些民众必须听从主人的指挥与命令行事,便称之为‘民主’;如果稍有违抗,便是‘反民主’,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看来,即使果真出自情治人员之口,也绝不可能是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熏陶所致。但是,一位了解蒋氏家族成员平日行事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正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心态,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是否合法,均在所不计,只要他们高兴,即使违法,大家也要毫无异议地支持与拥戴,否则便是反民主,也就是“叛乱”,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宋美龄都搞“小组织”,雷震追随蒋介石多年,居然没有能够了解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竟胆敢批评蒋氏家族成员的“非法”行为,特别是雷震在《自由中国》为文抨击“救国团”的成立,将矛头对准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如此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被打成反民主与叛乱的分子,可谓“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由此可知,在蒋介石父子的心目中,只有他们家族成员可以搞小组织,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甚至连批评他们搞非法组织的权利都没有,否则就是反民主与“叛乱”。
蒋经国搞一个“救国团”来培植班底,凡出身“救国团”的“从龙之臣”,近几十年来,莫不飞黄腾达;而蒋夫人则搞一个“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作为地盘,并担任主任委员就将近四十年,成为“万年主委”,比起“万年国会”,毫不逊色,而且在过去不容任何人批评,否则就是“叛乱”。雷震居然敢公然主张撤销“救国团”,怎么还能说没有涉嫌“叛乱”!
其实如果单就学理来说,雷震的民主理论素质远远优于蒋介石,雷震不但积极倡导民主观念,而且还结合一群知识分子,诸如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毛子水、戴杜衡、聂华苓、罗鸿诏等共同努力,这自然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惧。
雷震的友人、前台北市长高玉树的回忆录中指出,今日台湾乱局,蒋介石难辞其咎。他说,如果当时不将雷震逮捕入狱而让“中国民主党”成立,至少一个健全忠诚的反对党早已出现,台湾的民主政治或许已是步入正轨。
高玉树对雷震实在深感敬重、佩服,对他的热情、他的行事风格,非常敬佩。雷震一旦开讲,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高则很少讲话,都是在陪着他。
高玉树回忆,虽然雷震只会说台湾式的普通话,但是台湾人民对政治有兴趣者都会来听,也都听得懂。演讲的会场都是利用户外的空地,如果想要借用礼堂的话,恐怕学校也不敢借。每场演讲会的听众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有些政治气氛比较浓的地方,像彰化,听众就比较多;其他像板桥、桃园等地,听众就比较少。他们到台北市以外地区举办演讲会的第一站,高玉树记得是板桥。1960年时,板桥的人口虽然不多,不过若是要跨出台北市,板桥却是第一个立足点,板桥在台北县算是相当重要的地区。
雷震在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台热情,真是了不起,话语也很有力量,大家对他印象都很深刻,都真切地感受过他的热情。高玉树个人虽有民主思想,但却不具备雷震那么强的推动力。当时听讲演的人,在高印象中好像本地人比较多。雷震演讲的主要内容,还是希望在台湾实现胡适所倡导的两党政治的理想,成立在野党,负责监督执政党。胡适的理想与建议,大多是关于两党政治,但是蒋介石并不采纳。
在高玉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雷震说过他对“反攻大陆”政策的建议,也没听过他骂共产党,或是说过共产党的坏处。其实,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在做事的,国民党讲了一大堆的空话,却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当然会被逐出大陆。国民党在台湾也专讲空话,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做,以致选举会失败。所以,台湾的选举,抓住民心者一定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