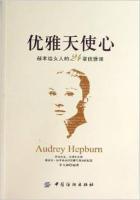组党的经费是由高玉树负责筹措的,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党部,也没有分设什么组织,只有到各处演讲,举办座谈会,所以开支不多,几万元就够用了。有一部分经费是靠募捐得来的,高自己也出钱,但为数不多。雷震并没有多考虑钱的问题,他的重点是去拼命抓住民心,组织新党。但雷震被捕后组党就停止了。
高玉树回忆,刚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阳明山别墅开会,由胡适主持会议,当时他只是提到一些大原则而已,并没有做具体的指示。雷震是奉行胡适的理想而来台湾推动民主自由的。但是雷震热情过度,经由他的领导与努力奔走后,他们已经可以组织全省性的反对党来对抗国民党。
因此,国民党开始担心、害怕。当时除了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以及国民党党员之外,全台湾的人民应该都会赞成成立反对党的,况且那时台湾人加入国民党的还是少数。此举已经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使得国民党无法容忍。因此,从1960年6月宣布组党,到同年9月雷震突然遭到逮捕,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在雷震倡议筹组新党前后,国民党的强权政治在台湾已经造成人民的反感。在台湾,敢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很有勇气的。当时不论是台北市、台北县,或是台中县、嘉义县等地,落选者都愤愤不平,纷纷痛斥国民党在选举中运用种种令人厌恶的不正当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非常灵光的雷震,敏锐地察觉出当时已经具备适合的条件,实在是组党的理想时机,所以组党运动能够很顺利地推展开来。然而,也就是因为太顺利了,以致直接触犯了国民党的大忌。
高玉树说,雷震仍有一些没有考虑周全之处。国民党、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台湾有一项秘密的大原则,即个别的台湾人出风头无所谓,但台湾人民一定不能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等组织的总干事,都须经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筛选过滤后,才能就任。其用意在于,防止任何台湾人借用人民团体作为根据地,来发展组织的力量。因此,所有的人民团体都必须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调查,这一点是雷震没有考虑到的,可能连胡适也没有料到。
因此,“中国民主党”组党失败,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因素,而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秘密原则,亦即台湾人民倘若是个人出头则无妨,但是绝对不能产生组织的力量。如果台湾人以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为基盘,来推动组织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恐怕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会没有立足之地。
当时他们没有设立召集人等职位,只有雷震、李万居和高玉树三个发言人共同负责推动组党的筹备工作。那时李万居的健康情况已经有问题,所以,实际上只有雷震和高两人到处宣传、推动组党工作。当时高心里想,如果继续这样努力做下去的话,这个政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任何受到强权统治的国家,人民一定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个道理,国民党的大员们大概不太明了。
雷案的法律诉讼案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幕丑剧、闹剧,演得十分荒腔走板。
当年以军法审判雷案已属不当,加以过程草率荒唐,雷震与假“间谍”刘子英,竟未能对质,如此重大案件竟在7个小时内审理完,难怪胡适在1960年的双十节不敢去参加庆祝酒会,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见人。
雷震的大女儿雷德全谈起父亲案件的法律诉讼,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回忆说:宣判的那天她在现场,只见外籍记者纷纷从法庭内奔向电话,有的仅对着电话说了一声“照原判”,因为宣判的前夕,记者们都纷纷得到可靠的讯息,“雷震的刑期已由最高当局核定为十年”。事实上,2002年9月4日《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布会由陈水扁亲临主持,第一册《“国防部”档案选辑》内所收录的档案资料已证明了“雷案”是未审先判。
蒋介石父子的智慧与容人的雅量,尚远不及当前某些要员,否则,雷震民主政治的理论与行动,或许早已成功,现在也用不着在台湾担心什么“统”、“独”之争了。就民主政治这一点而言,雷震无疑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雷震入狱的十年当中,台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尼克松准备访问祖国大陆,钓鱼岛事件发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次”不保,等等。外交处境的变化更大。1971年,雷震服满十年刑期出狱时,怀里藏着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的回忆录却被搜出而遭没收,后来这部回忆录被军人监狱焚毁,令研究者十分痛心。
出狱后的雷震,对台湾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政治的期待丝毫不减,他看到台湾面临外交上的艰难处境,出狱不久就写了数万字的《救亡图存献议》,提出十点改革建议,如请蒋任满引退;国民党要放弃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减少军费支出,建全军事制度;彻底实行法治,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治安机关应彻底改变作风,并严加整饬工作人员,以免扰民、误民、害民;解除报禁,以达真正的言论自由;简化机构,废除省或省级虚级化;大赦政治犯,放弃“反攻大陆”等。
这十点建议,有些在今天还未能做到,而有些则已经做到了,他的高瞻远瞩令人佩服。
回顾往事,很多人说:“雷震办的《自由中国》影响力太大才惹的祸。”此话的确不假。
1978年,中国台湾与美国断绝交往,就在这一年,雷震过世了,台湾的处境更加孤立了,我们痛感历史的无奈,也突显出这位悲剧性人物的高瞻远瞩,并看出他对台湾的贡献。透过这段历史来回顾这样的一个人物以及台湾这一段民主运动的历程,我们有无限的感慨。相信从这一段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这群来自祖国大陆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台湾地区的清流为了提早实现民主化而结合,不但很多动乱可以避免,而且“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这次民主化运动的结合将会取得十分圆满的结果。可惜,这个美好的结合却被自私的统治者所破坏,以至于后来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外省人就比较少。
名律师、原“立法委员”、“院长”梁肃戎先生,在当时形格势禁的环境下,遭遇到国民党内的攻讦,受了不少委屈,在碍手碍脚的情况下,他全力为雷震辩护,并提出延期辩论之要求,忠诚地扮演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角色,雷震及其家人都很尊敬他。
雷德全说:“父亲出狱后,一直受到监视,当时我们住在木栅,对面有一间小房子,情治人员要那里的住户搬家,还在我家附近装了3个大型的照明灯,可以就近清楚地监视所有人员的进出。这对我家也有好处,小偷就绝不敢来。”此外,“父亲常去外面散步,有时不小心掉了帽子、围巾之类的小东西,那些跟监的情治人员还会帮忙捡回来,放在门口”;“施明德和艾琳达结婚是由我父亲证婚的,当时父亲和情治人员大玩捉迷藏游戏,才得以赶到会场。”
她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姐姐、妹妹陪伴父母亲一同去日月潭游玩,跟监的情治人员开了三部车子尾随在后,真是糟蹋人力。我们在哪里吃饭,他们就在哪里吃饭。父亲在医院过世时,他们还不知道,还跑来家里问:‘雷先生在哪里?’因为父亲去世前,在医院住了三个月,他们不必整天在医院守着,所以父亲去世时,他们不知道。”
“父亲与民主运动人士的交往一直不断,父亲出狱后,常来我家的人,我记得的有陈鼓应、施明德、张俊宏、陈菊、康宁祥、江春男、孟祥轲等人。许信良可能来过,但不常来,我不太记得了。余登发还未坐牢前,他的女儿余绣鸾、媳妇余陈月瑛等人曾来我家,问母亲有关父亲在监狱里的情形。1979年,余登发入狱,那年5月我回来台湾,而父亲在该年3月去世。”
“齐世英、陶百川等人也常来我家,成舍我和齐世英都是父亲的挚友。父亲曾告诉我,世新的第一栋大楼,就是他帮忙募款盖的。当时有许多人捐地出钱要父亲办学校,父亲也曾在浙江长兴的老家办过学校,但他的兴趣还是在政治方面。高玉树正在台湾当局中任职,我想他大概不大方便来我家;我不记得吴三连有没有来过。”雷德全出示当年雷震与来访宾客的合照,另有陈少廷、林正杰、张富忠、许荣淑、胡学古等人。
雷震案对家庭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雷德全表示:“我没有父亲的勇气与胆识,无法实践像他那样崇高的理想与志业。父亲一直坚持去做他最想做的事,实现他的理想,很值得我佩服。但对我们家庭却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添了许多麻烦。”例如她的父亲刚出狱时,她常自美国回来探望他,每次都被检查行李,怕她夹带文件。即使她带鸦片,可能他们都不会管,但就是要搜查文件。
雷德全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要回美国,父亲为她送机,她买了几卷录音带,还没开封,情治人员要求听内容,她说飞机即将起飞,他们却坚持要听,而且教她放心,飞机不会飞走的。他们真的每卷都从头到尾听完。后来她都求父亲不要送机,免得徒惹麻烦。
雷德全没有注意到家里是否被监听,她说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监听的,因为父亲出狱时年事已高,没什么好做、好谈的。然而她们家的帮佣,一定有人被情治单位买通,他们也是没有办法,不做都不行,被迫定期打小报告,陈述父亲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雷德全无奈地说:“我们也不怪他们,因为当时还是独裁社会,警总的力量非常大,老百姓不敢不听命行事。”
她的父亲过世没几天,监视她家的情治人员就统统撤走了。但是她从国外入境时,还是有专人跟着她,检查行李。实际上对她来说并没什么阻碍,只是觉得麻烦,耽误时间。
雷震的案子发生时,雷德全在美国,但不在城内,还是一位外国同学通知她才知道的。她随后从电视新闻报导得知台湾有位发行人被捕,问是不是她的父亲。她打电话向《纽约时报》查询,《纽约时报》证实是真的。
该案发生不久,雷德全就向《纽约时报》等媒体投书抗议,也到过华盛顿去找美国国务院官员以及批评台湾的美参议员、众议员等,寻求他们的协助。
雷震的另一位女儿雷美琳也回忆了父亲的点点滴滴。她首先谈到父亲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那是在抗战前后,国家用人孔亟,尤其是需要负责任、肯做事、有能力的人,她父亲勇于任事,获高层信任而襄赞中枢,与他同时期的友好如王世杰、胡适、傅斯年、吴铁城等都是君子之交,她父亲最诟病的是结党营私。
雷美琳说,客观地说,当时的大环境是生存于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情况下,父亲行事风格一向是求好心切,蒋介石当然信任有加,多次委以重任,在那一段非常时期是没有矛盾存在的。
从大陆败退来台,蒋介石复行视事。自朝鲜战争发生后,台湾局势趋于稳定,蒋介石之后就忘记了大陆失败的教训,故态复萌,积极培植私人干部,保送小蒋继承其大位;而她父亲一心办理刊物,督促台湾当局改造,依然直话直说,与蒋父子扞格日深,渐行渐远,再也没有回头过。
至于她的父亲与非国民党人士的交往情形,她回忆说,《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伊始,即获海内外各方好评,她的父亲曾建议当局重用本省籍人才,并检举国民党选举舞弊事端,杂志社经常有人来拜会、来鼓励、来建议、来发牢骚,不一而足,每届选举,更是忙上加忙,电话不停。
国民党的老朋友避讳与他往来,因此旧友新交皆属民、青两党人士,或为无党无派者。1960年他们常相聚会,并已讨论组党,到处开会,所到之处,均有地方人士捐助,记得唐荣铁工厂也捐过10万元,但随后遭到报复,差点关闭。
雷美琳也谈到获知父亲被捕时的心境。她表示,事实上她的父亲被捕前不久,她刚踏入社会,第一天去大龙峒台北市立启聪学校教书,就是她的父亲陪她去见陈校长的。后来她换工作到彰银上班,她的父亲总是利用中午来看她,当时他们谈的都是有关《自由中国》刊物种种,以及新党筹组情形,那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雷美琳说:“我担忧父亲劳累过度,每次碰到傅正,我总是拜托他多看顾父亲一点。父亲和我的聊天中,我们早已达成共识,他迟早要去坐牢,只是没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除了他整整坐满十年黑牢外,出狱后依然受到严密监控,直到他去世为止。”她认为父亲被捕主要的原因是蒋介石要扶植蒋经国,要为蒋经国扫除一切异己,而阻止新党成立,扼杀《自由中国》等刊物所有的改造言论和建议,就成为威权体制当时唯一的手段。
8雷震案阴影之下的雷家
雷震狱中时期(1960—1970)的生活,是其子女们永难忘怀的记忆。
十年牢狱,让雷震错过了见证子女的成长,使他无法在她们身边指点人生道路,敦促她们努力向上,只能透过一封封家书,传递他对妻儿的关切与情感。《雷震家书》包含雷震狱中家书和雷震的家居照片,呈现了他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画面及其作为人夫、人父的生命景观。
女儿们回忆,父亲狱中生活非常有规律,读书、写作之外,有时还通过养鱼来自我消遣,在他有限的空间里散步或做其他运动,可说是十年如一日。记忆中,他头一年自看守所移送至新店军人监狱后,由于不习惯,有一短暂时期的情绪不稳定;再者于1970年出狱前夕,因他写的回忆录原稿遭狱方强行收去,他曾强烈抗议、不欲出狱外,以他急性子和好动的个性来说,均可说是相当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