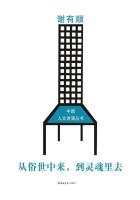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2)殷海光执笔的《“反攻大陆”问题》,说“反攻大陆”必须从公算,透过知识来检验,根据推论公算有“国际形势”和“现代战争的必要条件”两个考虑,以这两个考虑来看,短期内似乎不可能“反攻大陆”。因此,他建议当局不要把该做的事以“等‘反攻大陆’以后再说”推拖,必须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否则台湾将会累积很多问题。这篇社论被国民党诬蔑为“散布‘反攻’无望论”,而成为后来雷震被捕的重要理由。
(3)检讨军队非党私有化、军队里的党务等问题。
(4)财政问题。
(5)经济问题。
(6)美援的运用问题,对美援的浪费提出批判。
(7)小地盘大机构问题,主张台湾当局所属各个机构应缩减裁并。
(8)台湾政制问题,呼吁要根据有关规定,建立台湾政治制度,发挥责任政治。
(9)地方政制问题,主张彻底实行地方自治。
(10)“立法院”问题,批评“立法院”成为行政部门的橡皮图章,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出全面改选。
(11)新闻自由问题,要求废除出版法,保障新闻自由。
(12)青年救国团问题,认为救国团是非法的体制,破坏教育的正常运作。
(13)教育问题,要求学术自由,主张党化教育应该停止。
(14)对政风的败坏提出不客气的批评。
(15)呼吁台湾必须要有强而有力,能够制衡的真正反对党,才能解决以上的问题。
《自由中国》第15卷第9期“祝寿专号”出版后,一共再版了11次,是《自由中国》发行七年多来最大的销售量。但也因此激怒了蒋介石父子,认为“非整垮雷震不可”,否则不足以泄愤。于是下令所有官办的党、政、军方报刊,共同围剿《自由中国》,主题定为“防止共产党思想走私”或攻击“共产党同路人”。只要是提倡“自由民主”者,就会被戴上一顶“红帽子”。尤其是身为自由中国社社长的雷震自然成为官方的众矢之的。
3“孙元锦之死”案
在此危难之际,却出了一个关于“孙元锦之死”的案子,让事情变得雪上加霜。
1957年9月16日出版的第17卷第6期《自由中国》,刊登两篇被官方认为“不妥”的文章。其一是题名为《关于孙元锦之死》的读者投书,主旨是在揭穿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私设公堂,并私刑求供,把“台湾毛绒厂”经理孙元锦逼得自杀之事。其二是该期社论《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主要是谈有关阻碍华侨来台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发行到街头各处书报摊之后,台北市警察局立即勒令所有报摊均不得出售,并听候命令行事。隔日早晨警察局长刘国宪亲自来自由中国社拜访雷社长。当时雷先生尚未上班,故由担任自由中国社经理的马之骕出面代为接待。
刘局长很客气地说:“我是奉命前来的,听说贵刊这一期的内容有些不妥,上级指示我一定要来看看,千万不要发出去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想办法解决的嘛!”刘局长留下一张名片给雷社长,并再三叮嘱“没有发出去卖的,千万不要再发了”,说完就走了。
刘局长走后,情治单位的便衣人员也来查看,同样嘱咐他们“千万不要再发了,一切听候上级指示处理”等话。这次军、警、特方面,对于处理《自由中国》杂志所登载的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采取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至于上级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国民党当局仍然采用既定模式,亦即透过高层干部,直接与雷先生进行沟通,不过这次换了人选,改由“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出面,请雷先生在其寓所吃饭,而雷先生当时仍然担任“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还请了另外两位陪客:老“立委”周兆棠和杨管北,都是雷先生的好朋友。
总之,他们出面的目的,是要求把原来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另外换上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雷先生以“这是经由编辑委员会开会通过的事,个人不能擅自做主,必须再召集编委们开会决定”为由,暂时搪塞过去再做计较。雷先生回到办公室后,刚打算召开编辑委员会紧急会议,没想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正好来访,自然也是为了要求抽换两篇文章,重新印刷发行的事而来的。
据雷先生回忆当时情形:“王超凡允拿出改版的费用,我亦加以拒绝,我说如要改版,绝不接受对方的补助。王超凡见我态度坚决,竟屈膝向我下跪,盖恐自由中国社不能改版,他可能要受处分,而且饭碗砸破。我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心中实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之能屈能伸也。不料王超凡走出后,情报局科长刘瑞符亦来请求改版发行。由于各方面说情,事实上又不能发出去,只有登报迟两日发行,而抽出有问题的文章了。
由以上叙述可知,雷先生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这两篇“内容不妥”的文章抽掉,换上另外两篇文章,重新改版发行。
4陈怀琪控告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元锦案未完,又发生了读者陈怀琪控告雷震案,让事件更加恶化。
1959年1月16日出刊的第20卷第2期《自由中国》,刊登了一篇颇具趣味性的读者投书,标题是《革命军人何以要以“狗”自居?》,这是署名“陈怀琪”的一位现役军官,叙述他在“三民主义讲习班”受训的心得。大意是说:每一位教官不管上什么课,总要先将《自由中国》痛斥一顿,好像那一年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就是专门为了要驳斥《自由中国》的“毒素思想”而开办的。文中提到:有一天我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我们讲话,他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圣人”居然变成咬人的“狗”!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
这篇文章发表后,军方很快就查出了陈怀琪的身份。以当时的情况,陈怀琪可能受到的处分不难想象,于是他抵死不承认,并写了一篇“更正函”,转而痛骂《自由中国》宣传“反攻无望论”的论调,以及“杜撰假投书,以军人诋毁军人”,等等。
《自由中国》的编辑认为,既然是更正函,为何又节外生枝地批评:“诋毁台湾当局一把手,动摇‘反共抗俄’领导中心,污蔑革命军人,简直就是我们的敌人。”因此,编者并未将“更正函”全文照刊,仅在1959年2月16日出版的第20卷第4期《自由中国》的“给读者的报告”栏里,做了摘要处理。
此一疏失,却违反了《出版法》第15条的规定:“新闻报纸或杂志登载事项涉及之人或机关要求更正或登载辩驳书者……在非日刊之新闻报纸或杂志,应于接到要求时之次期为之。”
因为背后强大的压力,陈怀琪具状控告《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伪造文书”、“诽谤”及做“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三项罪名。在国民党高层决心“非把雷震整垮不可”的情况下,随即由台北地方法院签发传票,传雷震到案,开始侦讯。此时媒体随着国民党当局起舞,大肆宣传,认为雷震一定会败诉。
但是一些真正关心台湾事务的清流,如胡适、成舍我、胡秋原,甚至包括王世杰等名士,都认为这场官司无论国民党或台湾当局都应适可而止。因为尽管雷震败诉,甚至因此而坐牢,都不重要,但台湾当局一定会为此名誉扫地,也会为世界民主国家所不耻!所以他们试着透过私人渠道,谋求解决方法。
胡适先生认为“坦白”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既然是政治问题,就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于是根据大家的建议,胡适以编辑委员的身份,写一封《致〈自由中国〉编委会》的公开信,并登载在1959年4月1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0卷第7期。该函的主要内容是指责《自由中国》的编辑有许多不当之处,并提出三项建议:“本刊以后最好能不发表不署真姓名的文章。以后最好能不用不记名的‘社论’……以后停止‘短评’。”
这封信发表后,雷震请王云五先生拿着该期杂志,亲自向蒋介石面报,大家认为这件事若再宣扬下去,无论对台湾人民还是对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声誉,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希望蒋能考虑这些后果。果然此后就不再“开庭”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可知当年的法律,也要听蒋介石的。
5“今日问题”系列案
屋漏偏逢连夜雨。陈案刚有眉目,雷震推出的“今日的问题”系列又闯出更大的祸。
雷震因为主编《自由中国》,提倡民主自由,并批评时政,却遭蒋氏父子谴责,诬为共产党“同路人”、“寡廉鲜耻”、“与‘间谍’及‘汉奸’无异”等,心里已感不快,国民党当局却决定“非整垮雷震不可”。这种做法,反而将自由中国杂志社中的一群爱国的知识分子逼得“视死如归”。“今日的问题”系列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为了达成知识分子回报台湾的使命,从1957年8月1日出版的第17卷第3期起,到1958年2月16日第18卷第4期为止,《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为主题,一连串发表了17篇文章,第一篇以《是什么就说什么》为题,当作整个系列的“代序言”;第17篇则以谈《反对党问题》作为总结;另外还有两篇附录:《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和《再谈今日的司法》,总计19篇文章。
这一系列的文章,都是针对当时的内外形势,提出为台湾大事建言,可谓字字珠玑;而且秉持“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确实尽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可叹的是,这些宝贵的意见,不但不为当局接受,反而因此贾祸上身,成为雷震十年冤狱的根本原因。
上述文章分别谈论了17个大问题,尤其谈“反对党”问题,不但阐扬民主政治即“政党政治”的理论,而且还由“选举改进座谈会”,也是“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的发言人雷震、李万居、高玉树等联名,在1960年9月1日出版的第23卷第5期《自由中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向社会大众宣告,筹备已久的“中国民主党”,决定在9月底以前正式成立。此时,蒋氏父子觉得情势非常严重,遂下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将雷震等人逮捕下狱。“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同时《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了。
6雷震案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23卷第5期发表了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表示组织政党的民主潮流就像大江东流,是任何政党所抵挡不住的。三天之后,《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组党运动第一发言人雷震以“知‘匪’不报”和“为‘匪’宣传”的罪名被逮捕,判处十年徒刑,《自由中国》只好解散了。
《自由中国》庞大的发行量,的确是雷震案爆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当时《自由中国》的发行数量,每期已高达8000本,影响力相当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阅读《自由中国》者,为数极为可观,几乎已到令最高当局寝食难安的地步。
每期8000本的数量,在现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三十年前,却已十分惊人。有人指出,现在号称每日发行百万份的两大报,当时的影响力,可能尚在《自由中国》之下。
《中国时报》的前身《征信新闻》在三十多年前创刊时,是以油印发行,据说创刊号只卖出4份。而《联合报》在创刊三年时,每天才卖出10000份。至于杂志的传读率,远较报纸为高。所以,《自由中国》每期销售8000份,实已较当时许多报纸的影响力更大。对于这样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政论性刊物,当局或许只有去之而后快了。
几年前,前“立委”林正杰在办《前进》周刊时,经常遭到查禁的命运。有人询其缘由之所在,林正杰曾经回答说,《前进》每期可以销售12000本以上,这已超过了国民党可以容忍的极限,因而经常加以查禁,期能阻止其生存下去。如果林正杰所言属实,那么,雷震被“整肃”,也就其来有自了。
当然,雷震被控“叛乱”的近因,毫无疑问是积极筹组“中国民主党”,特别是他不断与本省籍政治人物来往,共同组党,犯了当时政治上的最大禁忌。
同时,雷震竟胆敢反对蒋介石连任,他不但敢批评蒋经国成立“救国团”的不当,而且还敢反对蒋介石违规连任,使得蒋介石有“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感,自然不能不着手“整肃”雷震的行动了。
1959年11月16日出版的《自由中国》第21卷第10期,刊登了一篇唐德刚所著《罗斯福总统究不敢毁宪》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岛内争论领导人应否违规继任、连任的问题而发。那篇文章在叙述美国总统罗斯福企图毁宪而招致没趣的一段史实之后,写出了下列两点感想:首先,它说明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领袖,都不太喜欢权力分立的民主宪政体制,不仅袁世凯要毁宪,就是号称一代民主宗师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也有狗急跳墙之时;其次,这个故事同时明白告诉大家,民主宪政的推行,不能靠当权者皇恩浩荡的“赐予”,而是它要建筑在全体人民以及人民的“代表”或“委员”们对宪政的认识之上。如果当时的民主党人,也是一批只知攀龙附凤,只知不择手段打击政敌,而对民主宪政一无所知的饭桶和党棍,则罗斯福恐怕早已变成千古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