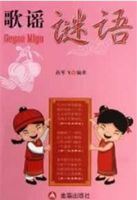这时我好像知道一点后果了。我马上记起,那个大院里的其他部门曾经也有过一个右派,由于一点小的过错,被那些左派人士吊在树上抽打……我开始害怕起来……但是,听天由命了……
恰在这时候,人事员办公室的门呀地推开。韩总编走了进来。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显然他听见了这边的吵闹。
韩总编进门一看,先是沉默不言,让屋里暴烈的气氛冷滞下来。然后他才慢慢地说话。他首先是对我说:“某某某,我不是给你说过,让你有事来找我的吗?”
我想起我来出版社的第一天他接待我时的情景了。他的确说过那句话。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他出于礼貌而说的一句客气话,我没把它当真过。因此在后来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去麻烦他。那天从乡下押送我回来批斗时,他解救了我,并用他的车送我去医院,我心里感激他,但也没有想到他第一天说的那句话。但是他对我很友善,这我知道。于是,他一出现,我就垂下了头,我原是准备不顾一切和那个人事员拼了的,现在我一声不响。
韩总编对我说:“你去。回宿舍去。过一个小时,再叫你来。”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但是凭经验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就回宿舍去等着了。一小时以后,真的有人来叫我。我又来到人事员的办公室。总编已经不在那里。人事员黑着脸,一言不发,甩给我一张他重新写过的证明:“某某某系右派分子,因身体有病,我社同意他离职去上海治病,病好后由当地政府安排途径,继续改造。”
我拿下这份证明,第二天便挤上去上海的火车。
我和一位从伊犁去上海的女同志坐一个双人座位,她带一个刚满月的婴儿。我把位子让给她们母子,自己睡在他们的椅子底下,身上裹着一件两年前下乡时父亲给我的破皮袄。就这样躺了三天三夜。这位善良的年轻妈妈,不时地把一些饼干屑和孩子奶瓶里剩下的乳汁递到椅子下面给我吃。她让我捏她儿子柔软的小手,还给我讲她儿子刚出生时,被维族保姆放在伊犁河中洗澡的事,据说,这样孩子长大后身体健康。
我到达上海。父亲和哥哥来车站接我。我们潸然相见,但随即破涕为笑。父亲说:“儿子,你拣回一条命来咯!”
就这样,我来到上海。
报户口的经过
但是,我仍然没有真正进入大上海。因为还必须报进户口才能算是一个上海人,而我报不进。
我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派出所的户籍警便上门拜访。他所管辖的区域里来了一个五类分子,他当然是要立刻前来查问的。对于一个无职无业的人来说,居住地的户籍警就是顶头上司,他是可以决定我的命运的,就像我刚刚逃离的那个室主任。我思想上准备着面对又一个张牙舞爪的人。但是出乎我的想象,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三十来岁,姓陈。
陈同志耐心地听我陈述自己的情况。我说了一个多钟头,他自己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边听我讲,一边把我带来的证明书反复地看了又看。我说完了,他问几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划上右派的?”“你的人事档案现在在哪里?”“你除了上海的哥嫂父母,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家属和亲人?”问完,他就走了,拿走了我的证明书。并不跟我谈报户口的事,只说:“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他能准许我报进户口吗?全家人都在提心吊胆,都认为希望渺茫。上海的户口早已严格控制,何况是在全国大精简和大疏散的时期,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人。陈同志一言不发,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打算怎样处理我?那张证明有用吗?如果报不进户口,他会不会马上赶我离开上海?那我到哪里去?即便他同意我在上海治病,那我病好后,又到哪里去?……一连几天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睡,儿子刚见到爸爸,跟我亲得很,贴在我怀里,睡得好香,小手还紧紧捏住我的衣角,好像是怕我重又飞掉。我又想起不在身边的女儿……我怎样才能把他们养大成人啊!……
几天以后,陈同志又来了。他向我和全家人宣布,上级不同意我报进户口。上海的户口已经冻结。他并没有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有自知之明。一家人也都明白。陈同志又说,我可以留在上海治病。
“那病好以后呢?我到哪里去呢?”我急切地问他。
“病好以后……你到哪里去……你可以还回你来的地方去嘛。”他说。
“我回不去了。我已经离开那里,他们已经不要我了。”我说。
“我们可以帮你跟那边联系,病好以后,还回去工作。那边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人才。”
我惨白的脸色大约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紧紧抱住我的腰、两只小眼睛盯住他看的儿子,大约也让他感动。他伸手抚摸我儿子的头顶,问我母亲:“这孩子几岁?”母亲告诉他,“四岁。”他又问:“你们送到北京给她娘的女孩几岁?”母亲说,“七岁。”母亲忍不住地哭起来,对他说:“孩子可怜呀!我们老了,不能帮他带一辈子,从今往后,他不论去那里,都得把他的孩子带走……”
我感到母亲说得多余了,便制止她。而陈同志却反而制止我。他说:“老人家说的是。让老人家把话说完。”
而母亲已经只顾哭泣,说不下去了。陈同志临走前对母亲说:“我们再想想办法。”
两天以后,他再次来到我们家。他再次和我仔细地谈话,进一步了解我各方面的情况,问及我离开那个地方的详细经过,我的老家,我的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乃至我原先的婚姻和离婚的过程。这时他对我说:“我给你摊个底吧: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有一条基本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有户口。好人坏人都得有户口。你这个人也必须有个地方落下户口。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根本无处可去的人,我们就得给你解决户口问题,就说你是个右派吧,也得给你解决。可是,你带来的证明不能说明你无处可去。你病好以后,应该可以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听他这样说,我不禁紧张起来。他察觉到我的心情,又对我说:“我知道,话是这么说,而你实际上是不可能回去,也决不愿意回去了。他们大概是也不再欢迎你。你刚才说,走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是吗?”
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好像是一句早已准备好的话:“这样吧:如果你能给我们证明你已经和那里的单位完全脱离关系,根本不可能再回去,那么,把你的户口落在上海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话中流露出对我的同情和理解,我能听出来。他在尽可能地为我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我立刻问他:“我带来的证明书不能证明我和那边已经完全脱离关系吗?”
“不能。那上面没有这样一句话。根据这份证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你病好以后,让你再回到那里去继续改造,或者把你送到一个什么别的地方去。这都是我们可以给你安排的‘途径’嘛。反正是,你还有路可走,不一定非把户口落在上海不可。”
这时,他给我明确指示应该怎么办:“你可以向那个单位,那个你离开的单位,再要一份证明,叫他们再说一句话,说你已经与他们完全脱离关系。问题就有可能解决。”
我实在不愿意再找那个单位的人,那位人事员,那位室主任……陈同志见我不说话,他再提醒我:“不要不好意思嘛,更不要意气用事。你就硬着头皮写封信过去,哪怕试试看呢。从道理上说,他们也不应该不给你说这句话。你实际上是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
他给我指出了道路,更重要的是,他的善意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一封信去。但是,怎样写?写给谁?……我反复考虑。只怕一不小心,把事情搞糟。两天后,陈同志又来,问我信写了没有。他的真诚关心让我很感动。见我犹豫不决,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又指点我:“把信写给那个总编。那个那天晚上叫人事员给你重新写证明的总编。”
我是想过,可是我不敢。我听他的话写了那封信。真是硬着头皮写的。心里也为自己给人家添麻烦而不安。再说,人家会怎样对待,我毫无把握。
同时收到两个证明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邮递员在楼下叫我的名字。我儿子把信拿上来时对我说:“爸爸,两封一模一样的信。都是挂号。”
两封挂号信用的是同样的信封和同样的邮票。只是笔迹不同。其中一封我认出是那个人事员写的。我立刻拆开。是一份新写的证明。我还来不及读它,马上又拆开另一封。奇怪,还是一份证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给我寄了证明又忘记,所以再寄一份?或是事情由两个人在经办,他们各自给我寄了一份来?……
我急着看证明的内容。我把这两份证明摊在桌上,对照着看。它们的内容是不同的。
人事员写的一份是这样:“某某某,系右派分子。本人要求离职去上海治病。我们同意。他已经与我社断绝关系。病好以后,由当地政府送往适当地点,继续改造。”
另一份是这样:“某某某同志,因身患重病,医生证明不宜在本地区居留。我们同意他离职赴上海由家属帮助治病。他已与我社断绝关系。在他治病期间和病好以后,均请当地政府妥为照顾和安排。”
我真是不懂了。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我凭常规的理性,把人事员的证明丢开,把那另一份给陈同志送去。虽然我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不配被称作“同志”。但是我很清楚的是,人事员对我仍是存心不良,他故意给我拖一条将来会有麻烦的尾巴。
几天以后,陈同志来家中通知我,我的户口已批准报进。我算是一个上海人了。
陈同志来通知我的那天,说完正事,他继续和我谈话。他说:“那个单位对你还算不错的。人家还称你为‘同志’呢。”
我真怕他会从这一点上生出什么怀疑来,使事情节外生枝。我一声也不敢响。我当然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天,陈同志兴致很好。他和我聊起天来。我记得,他深表关心地对我说过这番话:“这往后,你还得要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户口这一关算是过了。可是接下去,总得把病治好吧,总得把头上的帽子摘掉吧,总得有份工作吧,总得有个自己的住处吧,还有,总得再讨个老婆成个家吧……”
临走时他说:“上海这地方,也好,也不好。日子久了,你自己会有体会的。反正,你去拼搏吧。我能帮你时,就帮你一把。”
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过后很久,母亲告诉我,她那时找了个瞎子,偷偷给我算过一个命,说我命里有多次劫难,但关键时刻,会“有贵人相助”。母亲说,陈同志就是一位“贵人”。
我算是一个上海人了。但是,那两份证明是怎么回事?我写一封信去问小李,也告诉他我已经报上户口。
小李的回信过一个月才来。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我了解到实情,他是趁一次和韩总编两人在菜地里劳动时悄悄问明情况的。
那份称我为“同志”的证明是韩总编写的。他收到我的信后,让人事员办理,而人事员给我写了那份故意刁难的证明。他不便与人事员为我的事再有矛盾,就自己另写一份,盖上公章寄给了我。韩总编说他以前知道我这个人。原来,他本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室主任,1957年后“明升暗降”地调到那个偏远地区当总编。在北京时,他的编辑室曾经约我翻译一本书,我把这个宝贵的选题主动让给别人,这件事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我“发配”到那个省后,他一见名单,便向省委把我要到他的出版社来。小李并且向我转达了韩总编的问好和希望我今后努力的话。而总编自己呢,这时正在接受“反右倾”运动的思想审查。
韩总编是我这次人生劫难中帮我化险为夷的另一位“贵人”。
我回想起他说到的事:
1956年,我接到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函。要我译一本当时在国际上很红的书,是一位法国美学家的著作。他们给我送来书的英文和俄文译本。我花三个月时间译出两个本子里几万字的学术性序文,正要开始翻译正文时,偶然在图书馆里遇见外语系某法国文学教授的妻子。闲谈中她告诉我,教授先生正在家里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翻译那本我已经得到约稿的书。而他完全是因为看中书的价值,拿起来就译的,并没有联系好出版的事。当时我就决定,应该把这个选题的约稿关系转给他。他肯定比我译得好,他是教授,我当时只是个讲师;他是从原作的原文翻译,而我只能从英、俄文转译。我不应该因为自己拿到有合同效力的约稿而占有这个选题。回到家里,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们和教授先生联系,同时给教授先生写信,并把我已经译出的两篇序文也送给他。这件工作在我就算结束了,我从此不再想起这件事。
谁能想到,当时负责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室主任,就是现在这位韩总编。
“做人要凭良心。”母亲生前老是对我说的这句话,真是有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