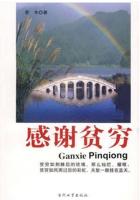这时我只感到麻木,不知自己有什么反应。只呆呆地听他往下说:“有三位同志,对,三位同志,是回自己老家,从事农业劳动。就是说,从此当农民。这也是一种工作嘛。但是就不需要国家再负担他了。还有一位同志,就是社里收发室的老马,他五十几的人了,就请他提前退休。再就是你了。你嘛,跟他们情况不一样。这你自己明白。”
我仍然麻木地听他往下说。只感到有一盆凉水在浇到头上。
“你嘛,身体不好,政治上有大问题没有解决,又没有个老家可以回去落户,而且是单身一人。这样,组织上就有责任帮你安排。”
怎样安排?我正要开口问,他就说了:“有一个去本省西边少数民族地区落户的名额。我们决定就给了你。”
“少数民族,落户,给我……?我是汉族呀……?”我喃喃地说。
“对,你去那里落户,永远做个那里人,将来在那里成家立业,也很好嘛。汉族,也很好嘛,民族大团结嘛……那里空气新鲜,有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你大有作为嘛。当然啦,首先是利用那里的有利条件,努力改造,争取摘掉头上的帽子嘛。”
我不知该说什么。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继续说:“那里是艰苦点,这不用我说。是我们全省,也可以说是全国最后进的地区。这两年再遇上自然灾害,情况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嘛。再说,你是去改造,又不是去享清福。这一点也是要对你讲清楚的嘛。”
“那我以后……?”我茫然地问。
“以后你就是那里的一个普通的,也是光荣的劳动者啦。当然啦,还不能说是劳动人民。不过,经过你自己的努力,还是有希望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的嘛。”
“……”
他不等我再问什么,就立起身来,最后再对我说:“那就这样了。等你出院了,我们开个会嘛,先把你这回在乡下出的事解决一下,你就可以动身去那里了。”
“我在乡下出的事?……”
“我是指你犯下的新罪行!不要装糊涂!”他态度突然严厉了。言语中连那个表示他宽宏大度和胸有成竹的“嘛”字也不见了。
“你是要走的人,我们可以不对你做进一步的处理,但是批判会总是要开的。治病救人嘛!”
这时他的那个“嘛”字又出来为他的思想表达服务了。说完这话,他不再理睬我,转身就走出病房。
去少数民族地区落户,永远不再是一个国家干部了。那是个什么地方?我的帽子怎么办?我的病?我以后怎样养活我的父母子女?……
命运之神下一步将怎样宰割我,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独独对我一个人如此地残忍,世界上有那么许多人,难道就我一个人是万恶不赦?这时的我,除了让自己不去思索,保持麻木不仁,听凭人家摆布之外,别无选择。
整个下午,我躺在病床上,两目直视,形同活尸,即使哭,也没有眼泪了。更何况,我还不是一个遇事便哭的人。
傍晚,同宿舍住的美术编辑小李来看望我。他是那个编辑室里经常来看望我的几个人之一。他是个很单纯的年轻人,对我一向友善。但他不是昨天刚刚来过吗?为什么今天又来,一定是有事情对我说。
是的,他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他也知道了要把我送去少数民族地区的事。他特为来告诉我:千万不能去。从他这里我知道,那边的情况比我下去帮助春耕的地区还要糟。而我这次下去,是取消了干部身份,没有工资,必须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我的一条腿还不能灵便活动,身体十分虚弱,怎样能劳动挣钱呢?而且,那是一个非常不开化的地区……而且,我的右派身份还会给我招来许多歧视和想象不到的待遇……而且,我哪天才能再见到我的父母儿女?他们还要靠我供养,以后怎么办?让他们也去那里是绝对不能想象的……小李最后说:“你去那里,是死路一条。”
我这时明白了,的确是死路一条。立刻从心底里害怕起来。但是我怎么办呢?我眼前一片绝望的茫然这时,小李给我指出一条生路。“你应该知道,中央关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中有一条:可以脱离公职,自谋生活。”
“自谋生活?”
“对,脱离这个单位呀,他们要你去那里落户,也是要你脱离公职,你自己要求脱离公职,去自谋生活,就可以不去那个地区。这是你有权选择的。”
“脱离了公职,那我怎么办?”
“现在这个你有公职的单位不正是要取消你的公职身份吗?他们给你安排的是怎么一种前途和命运,你还看不清吗?”
“那我去哪里呢?”
“去上海呀,去你父母和儿子那里。你不是有哥哥嫂嫂在上海吗?去那里自谋生活,怎么也比让他们把你送上死路强呀?”
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小李继续开导我:“去上海,你不会没路可走的。你要对我们国家,对共产党有信心!你不会没有前途的。他们这些人不讲政策,不顾人的死活,但是总有讲道理的人,讲道理的地方。你要相信这一点!”
他接着说:“再说,目前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总会过去的,你这样的人总会有用的。你也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党和人民不会这样浪费人才的。把你扔到那里去,不顾你的死活,是绝对不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的。你要相信这一点!”
他并且运用辩证法来说服我:“你现在脱离干部身份,脱离公职,是为了保存自己,将来有一天更好地回来当干部,来履行公职。”
单纯热情的小李非常同情我的处境,他极力劝说我听他的话。这天,他在我的病房里待了很久,他扶我下床,和我走到医院后院护士们种的菜地边坐下,反复地跟我谈。我和他在一间宿舍里同住了几个月,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的身世。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孤儿,是新社会把他养大成人,从小学到中学,到美术学院,他相信真正的共产党不会是像我们室主任这样的,我们的国家一定是有希望的。他说,眼前这个时刻对我的一生来说,是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要我坚决顶住。他说我一定能熬过眼前的艰难阶段,在将来对祖国人民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一再反复说这些话,要我千万不能受那些人的无理摆布,要我在关键时刻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说,到上海去自谋生活,是我眼前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路,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有任何的前途。
我终于被他说服了。
哥嫂给我一条生路
我立刻和上海的哥嫂联系。他们同意接纳我。在我人生的这个关键性时刻,是我的亲人给了我一条生路。
我躺在病床上给出版社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不去他们要我去的地方,提出离职,自谋生活,到上海治病,并和我的父母孩子和哥嫂在一起,他们可以照顾我。我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有人照顾。我的理由是充足的。党中央有明文规定的政策,我而且身体有病,正躺在医院里。我想,这条路我是一定可以走的。
然而,我对那些“左派”人物的估计太低。收到我报告的第二天,那位室主任便带上他的两个亲信到医院来,他们强行为我办理出院手续,把我拖回办公室,立刻组织一批人开会,进行批斗。
他们安排好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我的罪名除了在乡下破坏生产、破坏党的威信之外,还有装病赖在医院里,拒绝服从分配,拒绝分担国家困难等等,等等。那位室主任立场坚定地宣布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知道吧?不要给你活路你不走,要自寻死路!给你说,我们今天把你拉出去枪毙,都有充分的理由!像你这样的死不悔改的反动分子,死一个少一个!你说,你表个态,啥时候离开,到组织上叫你去的地方去?”
“我不去那里。我不能去。我有病。我要求自谋生活。”我已经铁了一条心。
“什么?你竟敢顽抗?”室主任看我坚持我的要求,他们的一番批斗毫无作用,气得呼地一下站起来,一只脚踩在他坐的椅子上,咬牙切齿、指手画脚地大声对我说:“你死了到上海去的心吧!上海那种地方是你能去的?你不尿泡尿照照你自己。要说上海,我们都想去!连我们都去不了,你想去?告诉你,现在全国大城市的户口早就冻结啦,你这种人,更是哪里也不会接受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他稍停一停,大约是看在座的人对他的高论有何反应。大家鸦雀无声。他大约认为自己的讲演非常的成功。于是再提高嗓门,发表了下面这番十分奇妙的言论:“我再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这里是什么地方。有句我们中国的格言,你知道吗?叫做: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到了我们这里,你还想走?哼……真是白日做梦!”
原来他把我比作肉包子,把他自己比作狗。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想笑,但是怕引起更多的麻烦,便把嘴闭紧。在座的他的喽啰里边,已经有人在吃吃发笑了。
这时我鼓足勇气说:“我有选择自谋生活的权利。这是党中央的文件里规定的。”
“党中央?党中央在哪里?在这里吗?这里执行政策的是谁?是我们,是我!这里谁说了算?我们说了算!我说了算!”
他的喽啰们应声虫似的连忙跟着说:“我们说了算!”
有一个跟他最紧的家伙,在别人话音落地以后,又特别钻出来说:“主任说了算!”
“不对,党说了算!”我坚决抗争,因为这关系到我的死活。“我要去找上级党委。我要去找省委宣传部的刘部长,我在北京见过他,是他把我从北京调来的!”
“不准你去!”主任大发雷霆,拍起桌子说。“你不配!你没资格进省委的大门!”
我决心和他顶到底。因为他的确没有道理。也因为我从来就心里看不起他。
“是你没有资格不许我去见省委!是省委大还是你大?”
在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的那几秒钟里,我从我的座位上立起,拖着我的一条病腿,向门外走去。在场的人,连同那位主任,见我居然如此大胆,一时间都呆住了。他们大概从没见过敢这样和他们顶撞的人。其实在我眼里,他们都算得了什么?
我已经走出门外,那位主任追出来问我:“你到哪里去?”
“我到省委去。我现在就去!”我当真马上就去了省委。我是在大门口花一块钱叫一辆三轮车去的。
“那你就走吧!”
省委的大门并不难进。从门房间到大楼里的工作人员都很有礼貌。刘部长在开会,他让人事处的处长接见我。处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她态度温和,给我一种可信任感,她耐心听取我的陈述,并且相信我所说的话。她劝我留下,说她可以建议出版社改变一下现有的决定,不把我送到那个少数民族地区去。她说:“我们这里需要干部,尤其需要知识分子。”但是,我已经被在省城和我支援春耕时在乡下所见的景象,以及那位主任的“肉包子打狗”的“格言”和他一贯对我的态度吓怕了。我仍然坚决要求“自谋生活”。处长最后接受了我的要求,她长叹一口气说:“那你就走吧!”
我回到出版社,她的电话已经打来。这些人在上级面前是驯服的。我可以去上海了。我立即开始准备动身。
我领到的“离职费”在购买火车票和托运一小部分行李以后,已几乎一文不剩。他们不肯再多给我。好在我还有些书,我把它们摆在马路边上卖,一部三十册的俄文原版《高尔基全集》才卖三块钱……但我总算有了动身的路费。
我还要带一张离职证明书。临行前的晚上,我奉命到人事员的办公室里领取他为我准备好的证明。他早已写好,盖好公章,我一进门就给了我。
幸亏我当场看一看。他给我的证明书上这样写:“某某某,系右派分子,本人坚决要求脱离革命,我们同意他去上海治病,病好后由当地政府押送原籍继续改造。”这实在是太恶毒了。他这是和那位室主任商量好,存心堵死我的生路。我本来脾气不好,长时间的忍气吞声,把我压抑得十分憋闷,现在,已经被逼到这种地步,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是一个死!我在刹那间失去了控制,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会对这位掌管我命运大权的人事干部做出这样的举动!
我把他写的那张证明压在手掌下,往他的办公桌上猛力地一拍,愤怒地大声吼叫说:“他妈的,老子不走了!你这是不叫我活嘛!”
我完全忘乎所以了。根本没有考虑任何的后果。在那个年代,人事干部从来高人一等。我竟敢骂他,还在他面前称老子,拍桌子。这还了得!他气得满脸涨红,两手发着抖,一边拿起电话,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你反了,反了,你个反革命分子要造反了!……”他在用电话通知保卫科,叫他们来捉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