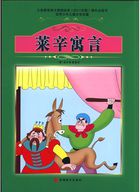摘帽大会上
1960年冬,我从一个离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蜷曲着身子,裹一件破皮袄,卧在火车座位底下三天三夜,来到上海。
我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我终于离开了,捡回了一条命。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后怕。我是怎样离开那里的?怎样居然能让我,一个除了头上的右派帽子和身上的疾病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在上海这块宝地落脚?这是一个你或许会感兴趣的故事。
还是从我怎样会去到那个地方,来开始讲起吧。
我当上右派分子以后,曾被送到河北农村几个地方去劳动改造过。我的劳动表现一直是很好的,曾多次受到表扬。一个我落户的村子在我走时,还给我送过一块玻璃匾,是一幅西湖风景画,两边贴上红纸条,写着:“王智量同志留念,感谢你忘我的劳动对我队农业生产的宝贵支援。”我的确真心诚意在改造。虽然改造什么,我始终并不明确地知道。我下定决心去改造。叫我改造什么我就改造什么,只要能让我“回到人民的队伍里”。
到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文件。我和其他几个人回到北京的原单位,等待对我们的决定。我觉得自己绝对有把握第一个摘掉那顶沉重的帽子。
那天,领导宣布开会。大家安静地坐定。还没有开始发言,会议室的门轻轻推开,进来一位同志。一位女同志。我一看,是我的妻子。
她来干什么?……我感到惊愕。我不停地用眼神询问她,但是她却躲开我的视线。
她来是有重要的公事要干的。
领导讲完一套应景的话,开始正式的议题,他宣读今天要讨论通过“摘帽”的几个人的名单,第一个是我。我激动得心都要跳出胸腔外。
这时,我的妻子举手,要求发言。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我也盯住她看。她开口了:“同志们!今天要讨论某某某的摘帽问题。我抱着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负责的态度,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来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份材料,供大家在讨论某某某的问题时参考。”
她要提供一份什么材料?我的表现很好,并不需要她再来为我说话。
她开始大声而缓慢地朗读她所提供的材料了。那是我在农村写给她的一封信。
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的:一天夜里,矿石收音机里,一家外国电台用汉语、英语、俄语反复攻击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运动,我听得厌烦,关掉收音机,又不能入眠,便起身给妻子写信。给自己的妻子写信,当然是毫无顾忌的。我向她叙说我刚才的厌烦情绪,这些话是绝对进步而且正确的,我甚至还咒骂了那个攻击我们国家的电台。接着我便谈到我的思想和心情:“……那些胡说八道我当然不会相信,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现在仍然有着许多我所不能理解的东西,我所看不惯的东西,我所不喜欢的东西,让我想不通的东西,明明白白是夸大的、虚假的、歪曲的、不公正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也是非常讨人厌的……”
她在读完我的信以后,把上面这段话里从“但是”两字以后开始的这几句,再反复加重地朗读了三遍,然后她提醒在场的人们说:“请大家看看,一个有着这种思想的人,对党和政府抱这种看法的人,能不能算是一个改造好了的人呢?够不够资格摘掉右派帽子呢?”
立刻全场哗然。我不仅不能获得“摘帽”,而且被立即逐出会场。
领导认定,像我这样顽固的人(当时流行的用语是“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应该送到一个更为艰苦的地方去加强改造。于是,我在和妻子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奉调去到那个远在天边的地方。
“这里只有你一个是右派”
当地省委宣传部根据我的情况,把我分配给省里的出版社。我去报到时,接待我的是社里的总编。他态度亲切和蔼,对我很是客气,甚至让我在会客室里的沙发上坐下,给我倒一杯热茶。他对我表示欢迎。当我想向他汇报我的情况时,他摇一摇手说:“不必了。你的情况我知道。好好干吧。以后有什么问题,你来找我好了。我姓韩。”
我怀着见总编时所感受到的愉快心情到一个编辑室去报到。我走进那间办公室,高昂着头,面带笑容,径直来到编辑室主任的写字台前,心想,这下子,我可以在这里为祖国人民做些贡献了,也争取把头上的帽子早日摘掉。
那位主任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我头脑清醒了。他说:“你就是那个北京下来的,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是吗?”
他这一当头棒喝,令我只敢立正站在他桌子前面,一动也不敢动。
“不错,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哪一个有你的学问大、学历高。你是个已经评上高级知识分子的人,是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们室里,个个都是革命的左派,只有你一个是右派。所以说嘛,你要是想在我们这里翘尾巴,那是做不到的!”
屋子里有七八个人,这时都停止了工作,注视着我。我不敢说话。他继续说:“工作嘛,我考虑好了。你没有资格处理文稿。我们编辑室的稿子都是供给工农群众阅读的。原想让你帮助小苏(他指一指他邻座那个梳小辫子的中年妇女)搞收发,我们每天出出进进的东西是很多的,可是她不愿意跟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成天在一起。没办法,总得安排你呀。你就给我们倒倒开水,扫扫地,擦擦桌子吧。”
他环顾一下四周,对大家笑笑,也有个别人跟他一起笑。我仍然站立不动。他觉得自己还没说过瘾,再继续说几句:“让你也尝尝伺候人的味道嘛。你在北京的大办公室里,让别人伺候惯了。现在让咱们这些大老粗,”他再环顾一次屋里所有的人,才继续说,“也享受一下让大知识分子伺候的味道嘛。”
于是我开始了我在那个城市里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中,以这种方式,继续改造。
对立面和勤杂工
我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从后边宿舍区跑到办公室,把房间和门外四周打扫干净,再去茶炉上冲二十瓶开水,给办公室里每个桌子前放两瓶,然后开始清理写字台。八张桌子我足足要干一个多钟头,稍一不慎就会闯祸,比如,清理烟灰缸时在桌上留下烟灰,洗茶杯时洒下一滴水沾湿了桌上的纸张,整理桌上的书本杂志时,把原是打开的某一页合拢让人家再找不到,主任同志都会怒目申斥我,而且“上纲上线”,说我是在搞破坏。大家是八点半上班,他们一来,我首先是给每一位同志沏茶,按照各人不同的要求去买早点,然后从那位唯一的女士苏同志手中接过当天要发出的一大捆邮件,把邮票一一贴好,骑上一辆破自行车,送到十几里路以外邮局去寄掉,回来赶上为他们大家排队买午饭。下午或是为他们抄稿子,倒开水,或是去编辑部包干的菜地里干活。菜地在河的那一边,来回一趟要走两个多小时,有时还要拖上一车肥料去……回来天黑了,匆匆吃过晚饭,又开始工作,回到宿舍总是十一点以后。第二天照样重复。每天如此。星期天也不休息。
我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在他们的政治学习会上充当“对立面”。每次他们学习时,总是要我交代我的右派言论和行动,然后大家结合我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批判。据说是,学习革命理论必须“树立对立面”。在这一点上,我是编辑室里最不可缺少的成员。不过,这项工作我还是很愿意承担的,因为至少我不需要劳动。每周两次的这种批斗,对我是最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名正言顺的体力休息。
而我对我的另一项工作就十分地害怕,但又无法逃脱。我必须代表编辑室承担所有上级分派下来的体力劳动。比如上山“绿化”,为食堂修建炉灶,给印刷厂从卡车上往下卸成捆的印报用纸等等。有时是通宵干,第二天照常上班,因为“一天应该等于二十年”……
我是一个多年来坐在书斋里的人,当右派以前,曾多次因肝炎住过医院,医生确诊我为“早期肝硬化”,我并且有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病史。在河北农村一年多的劳动,已经让我筋疲力尽,在乡下也曾经住过医院。现在这样的紧张生活我实在是吃不消了。这种对待我的方式并不能让我的思想意识得到改造,反而让我陷入一种茫然的绝望之中。
支援春耕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边。1960年的春天已经来到很久,天气相当炎热,这时,上级突然动员干部紧急下乡帮助春耕。说是否则今年夏天将颗粒无收,全省的人将会没有饭吃。这个光荣的任务当然地降临到我的头上。那位主任手捧一杯龙井茶,把他的两条高贵的腿放在面前的办公桌上,轻松愉快地告诉我说,这是我深入基层、培养自己对祖国美好大地的感情、直接向勤劳的劳动人民和基层干部学习、大力改造思想和立场的绝好机会。是他们大家,他指编辑部所有的工作人员,出于对我政治前途的关怀,把机会让给我的。
五月初,我被送到一个山村里。当我亲眼看见那里的饿死、吃人、逃荒……的可怕景象,看见那里树是死的,地是光的,山是秃的……勤劳的劳动人民一个个奄奄一息,祖国美好的大地上连野草都被挖光了,在那个村里领导生产的一个干部还在奸污妇女……我惊呆了。这真是给了我一个绝好的了解我们国家真实情况的机会。我在那个山村里待了一个多月,几十年后,我把当时留下的、已经残缺不全的记忆写成一本书(编者注:指《饥饿的山村》,漓江出版社),读者和文艺评论家们还说我的记述是“残酷的、震撼灵魂的真实”。关于那一个多月里我的体验,这里不详细叙说了……我在那里又病倒了,而我生病不能下地劳动,却被说成是“故意装病,破坏生产,抗拒改造”。我见村里一户农民全家五口只有一条裤子和一条破被,五口人个个全身浮肿,因为没有钱买盐吃,我给了他们几角硬币,结果被说成是“用小恩小惠收买落后群众”,“破坏党的威信”,“用心恶毒”……于是我被押送回省城了。也必须是“押送”,因为我的一条左腿这时已经不会走路了。
押送回省城以后
我回到省城出版社的那个编辑室里。押送的人把我放在地板上,交代给单位,就走了。我身边围着十几个人,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如何来处理我。我听见多数人是在怜惜我,想着怎样给我一个妥善的安排,但是其中一个人却大声地说,应该首先开个批斗会,因为我是坏人又犯错误,被押送回来的。别的人不愿同意他,但也不愿公开出来反对他这种立场坚定的人。
他们正因此沉默着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我见他们在纷纷让路,让那个人走到我身边。这人弯下腰来查看我的情况,这时我才看出,他是韩总编。自从我第一天来时他接见我,对我表示欢迎以后,我没有机会跟他再讲话。
总编一来,这一群人都等他表态,然后好按照他的态度来表态,这是那个时代我们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本规则。
韩总编独自沉吟着,低声地说:“怎么办呢……”
那位坚定的“左派”以为他看准了这是一个表现自己立场的机会,便挺身而出地来回答韩总编的问题,然而他没有看准的是,总编这句话并不是要别人来回答的。当韩总编仍在低头考虑的时候,这位左派吼叫似的恶狠狠地说:“拖出去斗他!这种坏蛋,死一个少一个!”
他没有料到总编对他的话非常反感,当即训斥他说:“这是什么话!就是判死刑的人,没枪毙以前,有病也要给治的!”
左派同志闭上了嘴,不敢再发狠了。我听见围观人群中有了嘁嘁嚓嚓的议论声,有一个女同志的声音:“救人要紧。赶快送医院吧!”大家立刻同意她的话。韩总编做出决定:“送医院去!”
总编吩咐用他的轿车把我往医院送。在我被扶上车时,我听见,还是那位革命左派在高声地发牢骚(这时总编已经走开了):“好个狗日的,跟咱社那头约克夏一个级别啦!坐总编的车!老子我也没坐过!”
约克夏是社里养的种公猪,当时每个单位都要搞生产,出版社买来这头良种公猪,作繁殖幼崽用。它的身价和地位非常高。上次它生病,就是用总编的车送去兽医院的。
我躺在当地人民医院里,回想着到这个地方以来的种种遭遇。这样下去怎么办?我不知道。渺茫前途令我忧思深沉,日不能食,夜不能眠。
躺了两个月以后,我的腿可以一瘸一瘸地走路了。一想起又要回到那个编辑室去,我真是不寒而栗。
而这时,恰逢全国因为自然灾害而有的大规模的干部精简,一天中午,那位室主任来医院“看望”我。我住院两个月,他从没有看过我,他必定是有目的而来。果然。
他先是告诉我干部大精简的消息,然后向我传达对我下一步的安排。他摆出一副领导架势,不紧不慢、不冷不热、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现在,我们国家面临巨大的自然灾害,全国都在大精简。每一个对党忠诚的,有爱国心的人,都要主动为国家分担困难。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更是一个表现自己有没有改造决心的好机会。”
我不知道他接下去要说什么,已经开始在心惊肉跳了。我屏住呼吸等他说下去。
“精简机构和遣散冗员的工作,在我们单位已经开始了。初步决定有五位同志,啊,不,五个人,要遣散,脱离干部编制。”
我屏住气息听下去。
“对,是五个人,不能都叫同志,要遣散。其中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