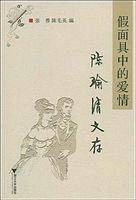母亲的好帮手
她是一枝青翠、嫩绿的,美丽的幼竹,亭亭玉立,默默无声地生长在太行山下。
她的名字叫青竹。她的确就是一枝青翠嫩绿的幼竹,那年我和她在一起时,她刚满十五岁。那天,我一到羊角岙村,王良大伯就带我回家,他把我的行李往驴圈旁小屋里那张大炕上一放,喊一声:“大竹,青竹,小竹,你们都过来!见你们王大哥!”
马上,院子里出现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男孩大竹十六岁,最小的女孩小竹四岁,中间那个女孩就是青竹。她身材不高,皮肤白皙,苗条而挺拔,她仰起脸来,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盯住你看,让你想躲也躲不开。端正的鼻梁下是一张带两个小酒窝的、笑眯眯的嘴,嘴唇薄薄的,一口洁白的牙齿露出来。她一只手把妹妹小竹搂在身边,另一只手在匆匆清理着自己乌黑的长发,把卡在头顶上的一根草剔掉。头发理顺了,又在自己清秀的脸庞上抹一把,虽然她脸上除了漂亮的红晕什么也没有。我看出来,她想让我这个新来的人对她有个好印象,我这时也正用眼睛盯住她。
哥哥大竹对两个妹妹吼叫似的说:“你们走开!”青竹便乖乖地带上妹妹退到厨房门口去。妹妹在她的手臂下挣扎,想要脱身,她就是不让,妹妹大声地叫“娘!”,不停地撒娇,她也不理睬,反正不让妹妹往我身边跑,自己则一声不响,只用两只乌黑的大眼睛牢牢盯住我。
父亲对他们三个说:“咋不喊人呀,没规矩!”于是大竹和小竹乖乖地喊我一声“王大哥!”而她却仍是一声不响。只用两只大眼睛继续盯住我。
我和大竹睡一间屋。他帮我把行李解开铺在炕上,把我的衣服在炕头放好。我偶一回头,发现青竹独自偎依着门框站在那儿,两只大眼睛还是好奇地盯住我。脸上带着笑容,她是在对我表示欢迎。但她仍是默默无声。
我的皮鞋上满是烂泥,我刚把带来的布鞋换上,她就一步窜进屋里,把脏鞋拿走了。我正要阻止,她哥哥大竹说:“叫她给你洗。”我不好不同意,便任她拿走。她把一头美丽的长发往后一甩,回头对我露齿一笑,笑得真甜,让我感到她很高兴为我做事情。
她把我的鞋洗干净,爬上一架木梯去放在房顶上,让它晒干。那里的房屋都是平顶的,屋顶承担着一部分庭院的功能。我见她迅速地爬上爬下,灵活得像一只山猫。吃饭时候,她也是捧着她的碗,哧溜一下就上了房,坐在房顶上吃。妹妹小竹也要学她的样往上爬,被大娘喊住。她太小,还爬不稳。
我的一碗豆角(她家称作“饭”的,就是白水煮豆角,另外还有玉米面贴饼,叫做“干的”)刚吃完,她的手已经从我身后伸过来,把碗接过去,给我又满满地盛上。把碗递到我手中时,她又对我甜甜地一笑。似乎她平时不大有这样的笑容,因为我发现,家里的人对她的兴奋和快乐,有些觉得奇怪,都用眼睛注视她。她是什么时候从屋顶上下来,立在身后等着给我盛饭的,我不知道。一眨眼间,她又坐在屋顶上吃她自己的豆角了。
我觉得不应该让她这样为我做事情。我正想说话,大伯却宣布说,以后我的饭就由青竹盛。我的衣裳脏了也由她洗。我立刻谢绝,但却不被他们一家人接受。我发现,男人的饭由女人盛,这似乎是他们家的规矩。我见大伯的饭是大娘盛,大竹的饭也是青竹盛,就不再说话,心想,还是“入乡随俗”吧。
坐在房顶上的她,听见大伯这样宣布,又对我笑笑,表示很得意,好像她从我这得到一种什么荣誉似的。让我更是不安。
我快吃完第二碗豆角时,青竹又已经立在我的身后了。我连忙对她说谢谢,告诉她我吃饱了。她瞪着一双大眼睛,把头一歪,表示不相信,后来相信了,再对我甜甜地一笑,去厨房拿一只贴饼给我。我吃不下,但是出于对她的感谢,我掰下一小块,余下的还给她。她把那大半块饼子自己吃了,吃得好开心,让我觉得,她是因为能和我分吃一块饼才特别地高兴。但是她仍是不说一句话。饭后,由她清理桌子、收拾厨房和洗碗。她很快就都做完了。真是她母亲的一个好帮手。
她不会说话?!
第二天下午,我从外边回来,发现我行李里的衣服全被取出来,整齐地叠好放在炕头上。再仔细一看,原来全都洗过。即使干净的也被重洗了一遍。一定是青竹做的,我去门外找到她,向她说谢谢。
她和大伯两人正在门口给牲口铡草。大伯代队里养两头驴,每年能得八十个工分。青竹见我向她走来,一声不响,只对我露齿一笑,又低下头只顾往铡刀下送草。每当铡刀咔嚓一声落下时,我的心会猛地一缩,生怕会铡到她那一双幼嫩的小手,但是不会的,她的两只小手干得非常熟练,和大伯两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我见她满头是汗,阵阵凉风吹来,便把她脱下放在一旁的上衣给她披在肩头上。她很感动,抬起眼睛盯住我,再给我一次甜甜的笑,仍是一声不响。
我让她去休息,由我来给铡刀喂草,大伯点头同意了,她才起来让位子给我。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她不停地指导我该怎样做,她一次两次地给我示范,直到我完全会做了,才去立在一旁。但是她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只是用手势给我比划,时而还拿起我的手,叫我学她的样子做。我到羊角岙村里,第一个把着手教我干农活的,是青竹妹妹。
第三天,我开始去上工,和几个老乡在地里锄苗,青竹跟几个和她同龄的小姑娘远远走来,不知是去做什么。一群女孩在一起,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但是我发现唯独青竹一个人一声不响,她好像也不很合群,老是一个人走在大伙的后边。她从我们干活的地头走过时,见我把衣服脱下扔在潮湿的田坎上,就给我拾起来,挂在树梢上。她并不喊我,只用手指一指,再朝树梢撅撅嘴,让我不要找不到。
已经三天了,我还没听见过她说话的声音。
下工回来,我累得一头倒在炕上。忽然好像觉得屋子里有些异样,原来是闻到一股清新的幽香。我抬头看见炕边土台上多了一只瓦罐,里面插满一种白色的小花,不知叫什么花,那香味真是太浓、太诱人了,不仅充满了整个屋子,而且立刻浸透我的肺腑。当然是青竹采来的。
大竹回来,我指给他看,他也很爱闻这种香味。他说,青竹是采给我的。
青竹给我和大竹打来洗脸水,我谢谢她的花,说我很喜欢。她笑得合不拢嘴,但还是不说话。晚饭时,她给我盛饭盛汤,还非要我把整个一只饼子吃掉。饭后又给我把洗脚水送到炕前。我实在过意不去,请大伯大妈叫她不要这样做,而他们却说她应该做,让我心里更是不安。我又在炕上对大竹说,叫他告诉青竹,以后不要再这样照顾我。而大竹竟然也认为青竹伺候我和他是理所当然。他说:“她不干这个还能干啥?”
“她也应该跟你一样上学才是。”我说。
“她上过学,七年多以前,生一场大病,就不能再上了。”
“为什么?”
“自那以后,她就不会说话了。成了个哑巴。”
“哑巴?!青竹是哑巴?”我震惊了,呆坐在炕上,身子好像不会移动。
“她是个哑巴。七年前那场病以后,她就不会说话了。”
“什么病?”我急忙问。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以后她就哑巴了。只上了一年多小学就停下来。好在还听得见。就是不能说。”
是的,她的听觉没有坏,而且很灵敏。所以我几天来都没想到,她默不作声是因为不能说话。
这实在太残酷了!多好的一个小姑娘!
我心里难过。尤其让我难过的是,大竹还告诉我,一家人都不喜欢她,嫌她是哑巴,将来不会有出息,一辈子都是个累赘。
这一夜我都没有安睡。
“明天我交你各草……”
青竹已经习惯于命运强加于她的沉默。她会用各种灵巧的手势,辅以眼神和表情,表达她所要表达的意思。和她周围的人沟通,在她并没有任何困难。我也很快就能和她沟通。她还有另一个与别人交流的渠道:她会把她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她上学时,曾经是班级第一名,现在还能写大约三四百个字。
自我来以后,她不像从前那样老是独自蹲在角落里。她变得活泼了。一有空就帮我做事,还向我问这问那。她使我更迅速也更愉快地融入这个家庭。家里人好像也因为她的变化,不再那么讨厌她。
我的农活技术还很差,队里往往只能分配我上山去割喂牲口的青草。干这个不需要技术,割四十斤记一个工分,而我拼命干一整天最多只能割二十几斤,中间还夹着许多牲口不能吃的杂草。我为此很是苦恼。一天晚饭时,大伯和大竹边吃饭边教我怎样割草。
大伯说:“你要挑那些长长的,比如山茅草和狗尾巴草那样的草割,容易找见,分量也重;不要割那些趴在地上的,割半天也割不到一斤。”
大竹说:“不要把酸枣枝子割进来,那上边有刺,要扎牲口嘴的。”
大娘也说:“有些草牲口不吃的,不要割回来。”
我分不清什么是山茅草,狗尾巴草,和酸枣枝子。更不知道哪些草牲口不能吃。一家人为我的笨拙和无知哈哈大笑。
青竹坐在房顶上,她停下不吃饭,歪着个头,静静地,一声不响,仔细听我们说话。
晚饭后,我回到屋里,在我的枕旁看见一张纸条:“明天我交你各草。不要给别人说。”
是一笔一画写的,笔迹很认真,虽然写得大大小小地,还有错别字。一定是青竹写的。我心里暖暖的,把这纸条小心藏起来才睡觉。这张纸条我后来收藏了几十年。
第二天早晨,我爬上村后的山坡,远远就看见青竹站在一棵大树下等着。她带来两根捆草用的绳和两把磨利的镰刀,我也带来一根绳和一把镰刀。她用手指在我的镰刃上试一试,对我皱一皱眉头,瘪一瘪嘴,意思是我没有把镰刀磨利。又把我的绳子两头缠在她两只细小的手臂上,用力一扯,就扯成了两截。然后对我瞪一瞪眼睛,指着我的绳子和镰刀,再瘪瘪嘴。脸上一股顽皮的笑容。我知道她是在批评我没有把准备工作做好。她继续做着手势和表情,指指我的绳和镰,再指指坡上的草,把两手一摊,耸耸肩头。这时我完全懂得,她要说的话,翻译成知识分子的语言,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是她表达得似乎简洁得多,而且使用的只是几个身体的姿势。
我们马上开始。我跟在她身后,首先是找一片好地方。我们翻过一个坡,来到一个野草又厚又高又密的山洼。怎么我原先就找不到这种地方?她一弯腰,镰刀便在她手下飞快地舞动起来,只听见嚓嚓嚓的响声。我紧跟在她身后,她怎样割,我就怎样割。不一会工夫,两人已经割下高高的一堆,比我一天割的还要多。她像个小蚂蚱,只往草厚的地方蹦,我紧跟着她,累得满头大汗。
她大约是听见了我的喘息声,她示意休息。我们走到一块大石头前,我坐下,她把我割的草抱来一小堆,放在我面前。自己盘腿坐在我对面的泥地上。
她开始给我上课了。原来我割下的草里,有许多种是牲口不吃的。她把那些一一挑出来,排成一行,放在我脚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和半截铅笔来。她是早有准备的。
她开始写了,写以前,先抬起头,用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对我不好意思地瞧瞧,我懂,她是说自己写得不好,让我不要笑话她。她指一种,写一个名字:刺头,硬叶子,苦芽子,毛瘌子,狗屎苗苗,臭杆杆……我就一个个地认,读给她听,再牢记在心里。
有的字她不会写,“瘌”字,她写成“拉”,我想应该是瘌,因为那种草的叶片上尽是扎手的硬毛。“狗屎”她写成“狗十”,“臭”字她也不会写,就把那苗草递到我鼻子底下叫我闻,嘴巴做出发“臭”字声音的口型叫我看。
我把她不会的字给她写出来,她趁势就来坐在我身边。她又在纸上写了“交你各草”几个字,脸上做出询问的表情。我懂她的意思了。马上给她写了“教”和“割”两个字。她立刻就照样每个字写三遍。
这时我想到问她:“为什么你教我割草,不叫我给别人说?”
她用手势告诉我:“他们不喜欢我。爸,妈,哥,妹妹。”
“你喜欢他们吗?你爸妈,你哥和你妹妹?”
她认真地点头。
“你听我说:你是个好姑娘。我们都喜欢你。我还会让大家都喜欢你。好不好?”我这样安慰她说。
她笑得咧开嘴,不住地点头,说明她是真希望这样。
中午我们背着两大捆草回来,称一称,一共七十五斤。下午我们又割了七十斤,两人得了三个半工分。我请狗不理(他是记工员)给我记一个工,余下的给青竹。当然应该这样。狗不理却偏向我,给我记了两个工,给她记一个半。
采粽叶的那一天
端午节头一天正好是我们下放人员的休息日,上午,我奉大娘命,跟青竹去村对面河滩边的芦苇丛里采粽叶。我们提一只篮子,兴高采烈地往河滩里奔,她像只小燕子,一声不响,轻盈地往前飞,我紧跟着她,感到愉快极了,好像天更蓝了,跟随我们身后飞来的几只乌鸦,也不讨人嫌,那哇哇的叫声比平时好听多了。
河滩上空气好新鲜,芦苇丛里更是一阵阵的清香。钻进那遮天盖地的绿色丛林,好似沉入一片无边无际的汪洋,而你却呼吸得更加自在而舒畅,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奇妙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