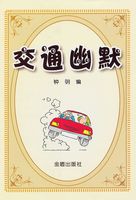童话中的乞丐
1940年,我十二岁,在离家七十多里的陕西省城固县上初中一年级。
学校设在汉江边一座破庙里,庙旁一片乱葬坟地上造几间草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宿舍。草房前面是操场,没有围墙,操场外是一条公路,路外就是江堤。一眼望去,只有堤下滚滚东流的江水,和几十里以外隐隐的山峦,四周空旷得很。
初冬时分,寒风劲吹,残叶在操场上飞舞。
一天下午,第一节课后,同学们都在教室前晒太阳。一个人影出现在操场边,正沿着红色的庙墙一步步向教室走来。远远望去,能看出是个中年妇女,她身体佝偻,步履蹒跚,头上包着一块咖啡色方巾,穿一件藏青色束着腰带的大衣,一只手上提一个白布小包袱,另一只手杵着一根长长的木棍。
我一看见她的身影便开始心跳,觉得她和我有关系。但是我看不出她是谁。远远望去,她很像是童话故事中一个饥饿的乞丐。我还刚刚看到她的身影,就好像已经知道,她左边面颊有一块褐斑,她的头巾很破,她的大衣上有许多补丁,她的鞋……
突然,就在这一瞬间,我认出她是谁了。她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她那块已经用了许多年的咖啡色头巾,上面有许多的破洞;那件呢大衣,就是日本人大屠杀时,我们一家人从南京城里逃出来,刚逃到徐州那天,她穿的那件大衣。那天,为了赶上最后一列逃离的火车,我们从停在轨道上的一列又一列车厢下爬过,母亲一只手自己爬,一只手还要牵着我,大衣因此被钩破好几处。逃到大后方以后,她用几块布料补过这件大衣,呢料上补几块布疤,而且颜色不完全相同。尽管母亲已经费尽心思,也的确补得很不错,但是我总觉得这件衣服很难看。我最不喜欢看她穿这件衣服了,而她冬天又只有这一件外衣可穿。她的鞋,一定是那双南京穿来的皮鞋,早就不成样子,而这是她最好的鞋……
我再睁大眼睛注意看,的确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我脑海中是童话里那个包着破头巾、穿着破大衣、杵着木棍的乞丐。而我眼前看见的,却正是我自己的母亲。
母亲越走越近了。她快要认出我了。这时同学们在各自玩耍,并没有人留意她。但是如果他们留意了,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乞丐样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那我怎么办呢?而她正包着那块破头巾,穿着那件补了布疤的破呢大衣,杵着一根木棍,向我和我的同学们走来。
我该怎么办呢?母亲,乞丐,破头巾,破大衣……
我立刻向母亲奔去。我要去拦住她,不让她走到我的同学们跟前来。
姆妈,你为什么要来啊!
这时母亲也认出了我,她开口在叫我了。我的心跳得更猛烈,我在想,同学们一定都在身后注视我,他们一定已经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知道这个衣衫破烂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一定在嘲笑,一定在说我的母亲是个乞丐……
迎着母亲慈爱的笑容,我心头涌起的却是一股对她的埋怨:姆妈,你为什么要来啊!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一副打扮,出现在我的同学们面前……
恰在这时,上课铃响了。铃声解救了我。同学们涌进教室去,不会再有人留意到我和我的母亲了。我悬着的心落了地。我走到母亲跟前,望着她含笑的、慈爱的、憔悴的脸。片刻以后,我才说话:“姆妈,你怎么来啦?”
我话音里传达出心头对母亲的埋怨,母亲却没听出来,她只听见她心爱的儿子在叫她“姆妈”。她伸出双手搂抱我,给我把衣服拉挺,拍去我身上的灰尘,又理顺我纷乱的头发,还问我为什么不戴帽子。我没有回答她,只顾回过头去,看有没有同学瞧见我们。已经开始下一堂课了,教室外一个人也没有,我有些放心了,但还是拖着母亲往校外走,同学们如果从窗子里边往外瞧,就会看见我们的。
走到操场边,转到庙门前,回头看不见教室了,我才再问母亲:“你为什么来呀?这么远,你怎么来的?”
“你来信说生病,我担心,就来看你。”母亲说。
母亲这年是四十五岁,她原本是小学教师,逃难到后方,找不到工作,只能种地。她种了一亩多地的蔬菜,养几只猪,维持我和她的生活。她每天都很忙很累。其实我只是一星期前有点不舒服,想家了,就随便地写了封信给她。这时早没事了。
母亲告诉我,她把园子里的大白菜全卖给菜贩子,凑了几块钱,就动身来了。她半夜两点钟出门,整整走了十二个钟头,为了省钱,一路上连杯水也没舍得喝。
我真不该写那封信!
“多亏这根棍子啊!要不我走不到这里。”母亲提起她手中那根难看的木棍对我说。而我当时恨不得她赶快把那根木棍丢掉,在我看来,她杵着它,实在太像那个童话中的乞丐了。
母亲一边走,一边打开她手里的包袱,拿出一小块糖糕叫我吃,我不要吃,我这时只想让她离开学校,越快越好,别让老师同学看见她。
我拖着母亲向县城的方向走。学校在城的东郊,我拖着她穿过大街,一直走到城西,离学校远远的,我才放心,同学们不会看见她了。我们找一家小客店住下,母亲向店家要来一盆热水泡她肿胀的脚,再用一根针把脚上的几个大泡挑破。她让我去街上买来几个叫做“锭子馍”的很硬的烧饼当两人的晚饭。吃完那几个馍,她仔仔细细地把我全身上下都查看过,知道我确实是没有病了,这才放心。
天黑了,我们躺在床上,母亲把我搂在怀里,问我学校的功课和成绩,我一边回答她的问话,一边就睡着了。我睡得好香,好甜。我一觉睡醒,发现那盏桐油灯还亮着,母亲还没有睡,她斜靠在床头的土墙上,一只手搂着我,一只手压在她自己的胸前,好像她心里不舒服。我第二觉睡醒,母亲还是没有睡,她在缝补我衣服上脱线的裂口。
马上天就亮了,母亲打来热水,给我洗脸、洗手,又给我洗了脚。太阳一出来,我们就离开小客店,我送她往回家的路上走,这时,她说:“本来我想给你把被子衣服洗一洗,还想看看你们的学校,跟你的级任老师谈一谈……”
说到这里,她没有说下去,只看了我一眼,轻轻地叹一口气。我心里有鬼,很怕她再往下说。
我送她走到大路口,她杵着那根木棍要迈步时,又嘱咐我:“天冷了,夜里不要踢被子,当心着凉。”
想想再说:“马上放寒假了,你回来不要走路,叫一辆人力车。你口袋里有钱。”
她一步步走去。看她佝偻的背影缓慢地消失在拐弯处,我转身往学校走,手伸进衣袋,摸到一沓钞票,母亲把她身上的钱全留给我了,她怕我丢掉,用针线给我缝在衣服里。
除夕夜的忏悔
一个月以后过年了,我回到家里。母亲把一只猪送去杀掉,猪头和内脏留着吃,猪肉全都卖了,拿钱给我做新衣服,还给我压岁钱,余下的做我下学期的学费。除夕夜里,我穿着新衣和邻居家的孩子们放炮仗,玩得真开心。母亲在堂屋里点燃两支红蜡烛,带我一同供奉死去的祖父母,然后和我两人吃年夜饭。这是家里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母亲几乎没有吃,她只顾看我吃,我吃得越多,她越高兴。饭后,她烧一大锅热水,给我好好洗一个澡,然后用棉被把我裹住,让我睡在她的身边,她自己没有躺下,只靠在床头上。这时,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孩子。
我已经差不多要睡着了,母亲却叫我睁开眼睛,听她说话。她说:“一年到头了,把身上洗干净,把肮脏全都丢掉,明年,不,明天,你就是一个全新的干干净净的好孩子了。”
她说得很对。我洗过澡,一身好舒服。我把身体贴近母亲的身体。
母亲再说下去:“不光身体要洗干净,心也要洗干净啊。你说是吗?要把这一年到头你心里有过的所有不好的、不干净的东西,在这时候全都丢掉,这样你明天就进步了,一天天、一年年变成个大孩子、好孩子了。你说是吗?”
母亲说得对。我回答一声“是!”,同时身体向她贴得更紧。
这时母亲郑重地问我:“儿子,你说说看,你觉得,这一年里头,你自己做过、想过的事情,哪一件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最不好的?”
我回答不出来。我真是不知道自己这一年里,做过或想过什么不好的事情。跟同学打过架?没有;成绩不好?我是全班第一名……
母亲继续说下去,她显然是早有准备的:“你把眼睛睁开,看着我!”
我感到她的语气有些特殊了。我睁开眼睛看着她,还抬起了头。
“你知道我们中国民间流传的两句古话吗?”
“什么?我不知道……”我真是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告诉你,这两句话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听人家说过吗?你们老师教过你们吗?这可是很有意义的古训呀。”
“儿不嫌母丑”……我马上知道母亲要说的是什么事情了。立刻,我在学校操场里把母亲急忙推走的那一幕,清晰地重现在我的脑海里。顿时,一阵无法遮盖的羞愧涌起在我的胸间,我把脸埋在母亲怀里,不敢抬起头来。
“你看我们家的大花狗,它多乖、多讨人爱哟。你看,它哪天嫌弃过我们?我们喂它的吃食,比左右邻居哪家的狗都差,可是它从来对你、对我都是忠心耿耿的。它从来没想过要丢开我们,另找一个主人家。人要是都像它那样没有自私心和虚荣心,那就好啦。”母亲一边用她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顶,一边说。
这时我已经完全知道自己的过错了。我知道我错得很厉害。我用两只手抱住母亲,她也用一只手搂住我。我哭,母亲沉默着听我哭,任我继续哭下去,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用眼泪来清洗自己。但是这时,我感到,我再多的眼泪都无法洗净自己可耻的过错,这是肮脏的过错,连狗都不如的过错。我该怎么才好呢?……我想听母亲告诉我应该怎样做。可是母亲沉默着,她要让我自己认识到错在哪里,知道如何改过。而我却怎样也开不了口。我连“我错了!”这几个字也说不出来。母亲仍是沉默着。她在耐心地等待。
这时,我感到自己不配睡在母亲的怀里。我把身体转过去,用手捂住脸。我在等母亲说话,可是她不说。我爬到母亲的脚边,蜷缩成一团,我想要母亲说原谅我的话,哪怕她只说一句,哪怕她只是伸手把我拉回她的怀抱里,或者,她如果不肯原谅我,那就让她像我平时做错事那样,用那根鸡毛掸子抽我一顿也好。可是母亲就是不说话。她不打我,也不伸手拉我。这段时间拖得越长,那种羞愧和忏悔的感觉往我心里钻得越深……
忽然我想起,有一次我的舅父做错了事,他去跪在家里祖先的神位前,表示他自知错误……我好像为自己找到了出路,立刻从床上跳下,披一件衣服,跑进我家的堂屋,跪在供奉在那里的祖父祖母画像前。堂屋里亮堂堂的,母亲点的两只大蜡烛还没有熄灭,那只蒲团,我现在还记得那只圆圆、大大的蒲团,是稻草编结的,还放在供桌的前面。我跪上去,埋着头,把脸也俯在蒲团上,放声大哭起来。我好像觉得,眼泪流得越多,这件错事在自己身上留下的羞耻和污点就越少,于是我不停地哭,大声地哭……
我哭了很久。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感到母亲温暖的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她抚摸我,为我擦干泪水,把我从那只蒲团上拉起来。她抱不动我,便搂住我的肩头,把我拖回睡房去。
躺在床上,我再次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这才说出了母亲希望我说出的话:“姆妈,我错了!那天我是嫌你了。我下次不敢了!”
这时母亲说:“儿子呀,知道错了就好。你还要做一辈子人呢,要是你这么大就连娘都不认了,这以后,在世上,你还认谁呢?人活着,不能心里只有自己啊!这是关系到你的人生和你的良心的大事啊!”
我把脸在她怀里埋得更紧,我哭得更大声了。母亲继续说:“做人,衣裳破点、脏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事事、处处都要凭良心。你记住:活在世上,一直到你死,都必须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一个良心上干干净净的人。”
母亲这时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枚金子做的针,直插入我的灵魂。
我不哭了,俯在她身边,静静地听她教训。母亲这天夜晚的这顿教训,引导了我整个的一生。母亲没有说很多,她只说了那几句话。那的的确确是几句金子一样贵重的话,针一样尖锐的话,它们将永远留驻在我灵魂的深处。
后来我俯在母亲身边睡着了。母亲却一夜都没有入睡。她靠在床头上,搂住我,抚摸我,亲吻我的头发。
……
今天,我已经七十五岁,母亲那夜吻过的我的头发,已经白如霜雪。
我多么希望今生今世我还会再一次,哪怕只是一次,让我躺在母亲的怀抱里,聆听她的教训。
不会了,绝对不会了。母亲早已在二十年前安眠在南京牛首山下的泥土里。
姆妈!啊,姆妈!……
好在那个夜晚,那个草蒲团,祖父母遗像前的那一对红蜡烛,母亲那天给予我的教训,至今全都鲜活地珍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