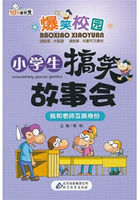段立文
高铁走了约八个小时,从早到晚。我们在窄长的车厢里坐着,冷气吹得关节疼痛。耳机塞了一整天,睡觉,醒来,睡觉。于山谷和隧道中穿行的时候,时速达三百多公里,视线中的景物悉数向后退去,前进的人像要飞起来一样,简直疯狂极了。从浙江到福建,窗外是中国南方那种湿漉漉的青山,蜿蜒纤细的盘山公路,散落在山上和平原上像火柴盒子一样呆板的三五层小楼,阳光照亮田野和树木,水田里耕种的农人皮肤黝黑。
在农田,山谷,村庄,小镇之间,速度及空间转换,仿佛永无停顿。我在背离自己的故乡,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从福州下车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大量嘈杂陌生的方言在傍晚异常潮湿的空气中不停翻涌发酵,如同当头一击。没有了家乡熟悉的味道,连呼吸都不适应。我想开口说话,发现言语一片空白。在那一瞬间我只听到了遥远的海洋的声音。
灼热的午后,阳光明晃晃地四处流动。阳光在八月的厦门更像一场暴雨。直接,激烈,让人无处可逃。扬起头来心中盲目不知所从,感觉窒息。我来的时候凤凰花开得正火红。校门道路两侧种植了高大的棕榈树,殖民地风格的建筑物上有朱红色木质百叶窗。
厦门大学,她的美暧昧不清,比想象中少一点,又比这个现实的世界多。
开学和军训的时候,事情出奇冗繁。写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连续几天半夜十二点发说说。穿着肥大却不透气的劣质化纤衣服在大太阳下一站半天,清晰地感知到汗水从皮肤上滑下来时走的路线。偶尔有夜训,却不是高中晚上训练时那样激动和新鲜。我几乎谁都不认识,可还得看起来饶有兴致地跟旁边人说话聊天套近乎。问你叫什么名字,转身忘记。下次见到不好意思再问一遍,就连这个话题都没有,只能点点头笑笑。
我并不脸盲,可能是真不走心。看到建南大礼堂青黑色的楼顶渐渐隐于背后的紫色霞光中,而东南方向月亮升起来,或许还照亮了海面。心里空空的,想起了什么。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抑或是很矫情的事情。然后我环顾四周,默默地掏出手机发一条说说。我不想家,只是跟身边站着的女孩说现在谁都不能让我回去,我觉得只要一回去我就不会想回来。
跟朋友出去喝酒,有时候只是头晕,有时喝醉。厦大白城沙滩其实不是一个适合喝酒的地方,那里能听到海浪,深夜里海水涨潮,可第二天洗衣服是一盆又一盆沙子。酒精的作用下绝望一下子如海水般涌来,把心房填充得特别满。哭泣是在试图把这些东西变成眼泪流走,但那胸腔里的巨大响动,分明是心脏在绝望的碾轧下崩塌碎裂,和这世界一起一块块化成齑粉的声音。
我在一个月以前会控制不住地拨出某个号码,并且对那个人念念不忘。而到今天也就不会了,应该再也不会了。
深夜十一点跟同学去爬情人谷,我本想的是一路走到山顶看月光。可一条木板拼接的路把思源水库环绕起来,于是我们只是绕了一个圈。经过夜色中一座漆黑的石拱桥,再往前走没有路灯。同学说你还走不走,我说你去过这里吗,他说没有,我说好那我们走。
我们就这样走,夜里地面湿滑,不时有小青蛙从右脚边的水塘里跳出来进入左脚边的草丛中。湖心亭在黑暗中显出飞檐轻盈的轮廓,我甚至觉得自己看到了它四根柱子上剥落的朱红漆。亭子里有一个人拿着荧光鱼漂垂钓。我们坐在亭子外面的石头长椅上,分完一包烟,聊天。
两个人可是说了什么吗,并没有。不过是平日里的一些极琐碎的事情,能跟别人分享的那部分曾经,能与别人交流的那一些认识。山顶的月亮在平静的水面上留下一道寒凉的影子,这面碧绿色的湖泊,微风吹过水面时平静得像是不起涟漪。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抽烟,沉默。那是一包台湾烟,入口烟雾缠绕在舌尖上,味道浓稠而辛辣。
过往的许许多多,皆在走过的路上沉淀成静默。没人可以分享,我们自然而然地无话可说。
时光中每一个能够沉思默想、浮想联翩的瞬间,都让人觉得欣慰。孤独多么难得,我竟拥有这许多。深夜中远离了一切尘世喧嚣,脚下的路,依然不曾停止。
我背着双肩包一个人走在大学校园里,感觉今年夏天非常漫长,像是再也不会有冬天一样。高跟鞋在鞋架上放着,时间久了盒子表面积了灰尘,也就忘了穿。脚上套着的这双白色阿迪,一直洗一直洗,终于发现它侧面开胶了。我不是知道珍惜的人,如果喜欢,就只会很用力地挥霍。
可还是想要一个安静的干净的人,有温暖的眼睛和手掌。这个人会是多么地难以寻觅,更可恨的是我只会等待。能找到身份,找到目标,唯独温暖和安全却很稀少。中学时代那些像花期一样的可能,那些人,竟都悉数错过。如今看来,那六年是场不自知的旅行。寻找一点点温暖并发现终不可得,得不到的东西,就应该错过。没有开始的结束,不断地不断地告别。只有旅途还在继续,我看见自己背着笨重的双肩包沿着柏油马路行走的身影。深灰色公路伸展向远方,侧过头看见无尽的金黄色大漠,戈壁中翠得发黑的孤独灌木和被夕阳燃烧起来的大片火红云霞。
我一直跟着自己的理想,独自走了好远好远。我问自己你现在能妥协吗。不,绝不。
一个人血液里的东西,真是很难抑制,就像生死一样。
低着头走路的时候,心知前方漫无边际。因为是一个人,就随时可以停留,也随时可以失踪。
又是在白城沙滩喝酒。不知道什么特殊日子,晚上有很多人放飞孔明灯。那个爱和我聊文学的文艺青年,他渐渐地醉了。我把背靠在台阶上,双腿蜷起来,一口一口地喝酒,像喝茶一样。这个时候进入嘴里的液体,没有任何味道。
孔明灯慢慢从海面升起,发出如太阳一般暗红朴拙的光。这群古老轻盈的精灵,它们在半空中分散开来,又在头顶上很高的地方聚在一处。我看着它们升空,没有声响且不知道去哪里。可它们在静默中相聚就像守着一个归期,然后一起走过广阔的孤独的夜空,然后一起死亡。
我看到这里眼含热泪。
经过黑暗的时间如果太过漫长,会让我觉得寒冷。终点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想让未来变成什么。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换言之,人又是被拘禁的,从未曾得到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我们孤独,或者漂流。更多的时候是在孤独中漂流。我读书然后远行。有时候我这样伤心,但不会表达,就如同不会去爱,从不。爱是被封闭被禁忌被拖延被搁置的。这样的爱,是我对人群的方式,是我手里唯一的救赎。我怕一旦错了,我会被自己的罪吞噬。
如果你说走吧,我会跟你走吗?我只是说我不会寻找只会等待你,可我没有告诉你我在哪里。
你这四年是什么模样,我怎么知道。去做心理测试回访,那人说因为有一两项得分情况不好。我就对着一个陌生人说了好多话,关于自己的规划,目标,活生生地把自己说成了一个有为青年。她很快就放我走了。出门的时候我一直在笑,也有可能,自己真是这个上进的样子吧。
接触到以前完全不了解的西方后现代文学,跟很多人讨论自己的文字,讨论电影、讨论书。这是我之前不曾做过的事情。生活毕竟在改变,性格的可塑期,说不定哪一天昨日的那个自己就悄悄地溜了好远。
翻看之前的旧书,看到书中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个作者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能让我们按一下按钮就瞬间消失,那么地球上的人会少一半。我曾问自己:“如果这样的按钮在你面前你会碰吗?”去年夏天我记得自己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我会。”可现在,我觉得我一定不会。自生而外,不曾考虑其他。死不是生的对立面,可生命始终有它值得敬畏的奥秘存在,不论事情变成什么样子。对痛苦的担当,就如同对喜悦的渴望,长大了的你我,需要以赤子之心坦然相对。
从八月一直到十月,这里依然裙裾飞扬。今年竟多过了三分之二个夏天。厦大的晚上总是安静而美好,潮湿的风扑到皮肤上,带来清凉的水汽。这几天天气有点凉了,天黑之后刮起的大风让人非常清醒。自白城一路到情人谷,天空中云层薄薄的。只要抬头,在哪里都能看见月亮。
所有发生过的,只是往事。而故事,还没开始。
就这样站在夜色里的时候,总有熟悉冰凉的月光透过路边高大的棕榈树叶子,洒在我脸上。
想要,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