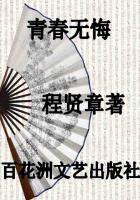/曲玮玮
接到暑假去北京参加活动的通知,匆匆关了邮箱,想着准备行囊。豆瓣电台正播放Eason的歌,他的愁肠忧伤像轻柔绸缎飘落在皮肤上,又慢慢地融化进毛孔里。他说,你会不会突然地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他说,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一双撩拨的手拨开杂草丛生一样的记忆碎片,那些完整的画面竟依然近在眼前。它们被轻轻地托起,又瞬间跌落,多了开裂的痕迹和模糊不清的脸。
叫我不得不想念。
去年暑假我跟小浅像两个冒失鬼顶着骄阳整日徘徊在首都的大街。那天一位喜欢的作家恰好在时尚廊书店举办书友会,我们当即血脉偾张冲锋而去。见了作家我们俩只顾拍照,兴奋溢于言表。放下相机我们东张西望,注意到一旁的男生只是低头提笔写字,垫着躺在腿上的黑色公文包,清淡的眉宇像安静的雪。我们的激动锐减,也安心地坐下听访谈。中途我忍不住瞥向一旁的男生,甚至直勾勾地盯着他。他似乎有所察觉,不抬头,只是嘴角隐约翘了一下,像堆在枝丫的清雪温柔落地。
恍惚间有人戳我的肩膀,那个男生竟凑在我耳边说话:“同学,我是记者,今天忘带相机了,你回去能不能把今天的照片传给我?”我说:“好。”他笑着递给我一张字条,写着他的电话和邮箱,显然是提前准备好的,捏在手里湿漉漉的。
未料走出书店,下起了大雨,我跟小浅不知所措。这时那位记者迎上来,手里拿着蓝色折叠伞:“你们没带伞?来,我帮你们拦车吧。”古灵精怪的小浅说:“你们这么快就混熟了?帅哥,那就不客气了。”到了旅店,小浅给他打电话:“你交代的任务我们一定完成,不枉费你为了拦车,衬衫都打湿了。”挂了电话小浅催我给他传照片,我伸伸懒腰,慢吞吞说:“急什么?”小浅用中指戳我脑门,“这帅哥看起来特温良,傍上他咱这几天就有好玩的了。”我笑着白了她一眼,打开电脑。
传完了照片顺势和他在邮箱里聊天。他还是学生,暑期做兼职记者。我问他怎么坐在观众席上这么淡定,面对喜欢的作家也不动心?他发来一个得意的笑脸说,见惯了大场面,波澜不惊。我戏谑,连相机也不带的记者,还谈什么场面。
转眼聊到深夜,小浅早已睡去。从窗户望去,镶嵌在城市夜空的灯光都有些疲惫了。我揉揉眼睛,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辗转很久才睡下。
第二天清晨却被腹部剧烈的疼痛惊醒。怕是肠胃炎犯了,我无奈地看着小浅。小浅踉跄地跑过来,在旅行包里一阵乱翻,终于找到了药。我皱着眉头吞下。小浅说:“必须要去医院,要不打电话给那个记者,让他过来帮忙吧。”我心想,不过一面之缘,名字还不知晓,太冒失了。不过耐不住剧痛,只好点头。小浅一连打了几次电话,又发了短信,还是没回音。我们两人只好去附近的医院挂号。夏日的骄阳要把整个人烤化了,走在街头一阵晕眩。走出医院时,昨天熟悉的身影突然又出现了。他焦急地跑过来,带来一阵热浪,额头的汗珠断了线一样往下淌。
“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刚才看到短信,就跑过来了。你没事吧?”
“嗯,她没事了。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小浅抢着问。
“这就是离你们最近的医院了呗。呵,我家也在附近。”他笑着敲小浅的头,末了又神情严肃地看着我说,“好点了吧?好好休息,明天带你们玩,将功赎罪。”
我心头一暖几近落泪,未曾想到能俘获陌生人的温暖。嘴上却说:“我们得考虑一下,最近首都拐卖人口特别猖獗。”结果小浅笑着呵斥我不知好歹。
第二天他果真在旅店门口等我们。穿一身清凉运动装,额前的刘海被风吹得四散。我跟小浅俩人又神气十足地在城市四窜,他安静地跟在我们后面,提着两个唐突的粉色女包。这天我们才知道他叫梁彬,小浅软磨硬泡追问他的私密生活,我们又得知几月前他跟女朋友分手。听到他没女朋友,小浅两眼不由自主地放光,立即扑上前摇他胳膊撒娇似的唤他“梁大哥”,梁彬只好假装向我做呼救状。我只是笑。
晚上小浅回旅店又念叨梁彬的好——温柔又殷勤,眉眼恬淡还见识广博。我打趣她:“过几天我们就回家了,难不成你想尝试一下时髦的异地恋?”小浅瞠目怒视道:“哼,倒是你苗头不对吧,别做对不起我哥的事,枉费他正在家乡对你痴心妄想呢。”我朝她扔枕头,于是两个女生又笑嘻嘻地打闹成一团。
那晚脑海中浮现的竟全是梁彬的脸。他低头疾书,温柔蹙眉,满脸汗珠,搞怪的鬼脸。暗笑自己仍逃不脱小女生情结。夜越来越深,思绪成了越加黏稠的浆子,我按捺不住,发短信给梁彬,只有两个字——失眠。他很快回复五个字——楼下咖啡馆,这竟像雷电一样击中了我的心脏,怦怦跳。我看一眼小浅,她正微鼾深睡。我蹑手蹑脚地下床,屏住呼吸,轻轻带上房门。
深夜的城市竟有些凉,梁彬早就等在那里了。他的眼睛更黑更深了,仿佛与它交汇,就能跌进去。“恰好我也睡不着,索性出来聊聊。”他温和地解释。我点点头。我们聊着北京,他的大学,我的家乡,他听说从我家就能看到大海,特别兴奋。想到他兼职做记者,我打开手机把我写的杂文给他看,他认真地读了很久,眉宇又变得像一抹快化的雪,我撑着头百无聊赖地盯着他。末了他做夸张状,拍案而起说:“文章观点犀利很有洞见,不知以后能否有幸约你的稿?”见我不言,他竟握着我的手说,“我是认真的。”我当时因这一阵温热不知所措。
第一抹微光把城市的天空擦亮了,我跟梁彬分别,又屏住呼吸赶回去。思绪像乱麻一样错综交织,我为在他乡邂逅这样的男生欢欣,又不敢靠近空气里若隐若现的暧昧,更不知如何跟小浅解释一夜的未归。颤抖着推开房门,小浅的旅行箱竟然塞得满满的,她光着脚丫在床上乱摁遥控器。
“玮玮,我要走了。”小浅淡淡地说,仍然紧盯着电视,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简直要傻眼了,手心顿时渗出汗:“你提前走?那我呢?”
“刚才妈妈打电话让我收拾东西,说口语考试提前了,今天托朋友给我买了动车票马上送来。你一人再玩几天吧。”小浅见我瞠目结舌,忙着一股脑解释。
去北京南站送别小浅,陌生的身体和无数张疲惫的脸在眼前一晃而过,周遭的离别与眼泪那么多,只是都不属于我。我找张椅子坐下,思忖剩下几天是自己悠悠然地触摸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还是再冒失地打搅梁彬。人流与我逆行,我好不容易冲到地铁站口。那个温柔的声音再次响起,梁彬说:“我来了。”他就像一朵被施了魔法的清新的云,在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荫蔽阴凉。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小浅发了短信给我呀,说你一人举目无亲颠沛流离,只剩下我做依靠了呢……”他恢复嬉皮笑脸。
我不说话,只是笑。多么温暖,人群中有一双只认准我的、清澈好看的眼睛。
那天我们去了798、后海酒吧街、南锣鼓巷……我把相机牢牢抓紧,想留下的风景太多,但一想到此后记忆无处安托,只属于渐渐泛黄的彩色纸张,决定把相机放回包里,不去惊扰时光,让今天走的每段路都是完整的细水流长。
梁彬边走边哼歌,唱的是Eason的《好久不见》,“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他说:“前几年到处旅行,去驴友网住陌生人家里,对每个城市的印象也沾惹了不同人的气息。若是第二次,见物是人非不免感慨。”“那我以后不敢再来北京了,怕触景伤情呀。”我笑着搭话。
明天我就回家了。疲惫的工人决心在这里安身立命,特立独行的艺术家飞扬跋扈,匆匆行路的白领,游荡闲适的游人,阳光在城市上空,在每个人头顶盛开。时光流得那样慢,围在我身边周旋。梁彬对我说,要坚持梦想,要给生活最好的微笑。我身边的他,因为晚上要出席活动,穿着白色条纹衬衫,笔直的西裤,刚硬的轮廓隐藏了他那部分孩童式的单纯。他突然变得那样远,那样不可企及。就像我即将挥手而别的城市。
我只身一人拖着旅行箱去车站,梁彬执意要送我,我故意告诉他错的时间。过安检的时候,我最后一眼打量这个城市,想象他的魔力会不会再一次显灵,再次出现在被泪水浸湿的视野里。
最后我留下的只有一首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今年夏天我或许要住同样的旅店,看同样的风景。路过那家咖啡店时,会不会看到去年昨日的梁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