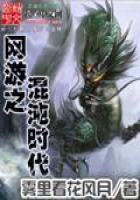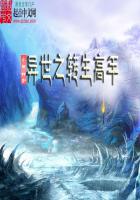再次遇见“鸭舌帽”是在三个月后的派出所。
工地上一个年轻的工人因为迟到被罚了工资,不爽骂了几句,被工头一巴掌扇碎了一颗牙,那愣头青当即报了警。作为监工,我只能来派出所备案接受调解。
工地上出事故分三个等级,第一种是赔钱,第二种是赔大钱,第三种是不赔钱。这种就是第一等级的事情。
我赶到派出所门口的时候正好和“鸭舌帽”擦了个肩,我认出了他头上的帽子。
“嗨,党小沫。”
“哦,是你啊,陈……陈大力是吧?”他一拍脑袋。
“你怎么在这儿?”话一出口便觉有些多余,小偷进派出所不是很正常的事情!
“哦。刚刚路上有人飞车抢包,我把那人逮住了,刚做完笔录。”
我有些难以置信地看了看他身旁的警察。
“党小沫同志可是个英雄啊,见义勇为。那个飞车劫匪可是个惯犯,说来我们还要好好感谢小沫同志帮我们抓到那人。”
“哎,不提不提,应该的。”他又转了一下头上的帽子,咧嘴笑得很是开心,“对了大力,你上这儿来干吗了?”
“公司的一点小纠纷……我接个电话。嗯,来了,在门口了,遇见个熟人。嗯,好。马上进来。”
“手机……”党小沫冲着我裂了屏幕的手机努了努嘴。
我诡异一笑:“还给那人了,都是开玩笑嘛。”
他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人,有意思。一会儿一起吃个饭吧。我请你。”
党小沫是个孤儿,16岁之后从福利院出来,没有资助,辍了学开始混社会。他那令人咂舌的手顺理成章地被一个小偷发掘了出来。
“算是我师傅吧,对我挺好。2008年进了监狱,被判了十年,冬天就能出狱了。”他把芹菜肉丝里的肉丝都挑了出来。
“你不吃肉?”我好奇地问,“信佛?”
“信佛会当小偷吗?”他笑笑,“还债。”
我没有继续问,谁没点故事呢?
“我也是那时候金盆洗手的,嗨,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想做这行。师傅进去了,正好干点儿正经事。”
“看得出来,你这不是还见义勇为了吗,不是个坏人坯子。”
“小偷,都没几个坏人,有坏心的人杀人越货,不比偷个钱包手机什么的来得快?”
我不置可否,呷了口啤酒。
“干什么?摆盘你知道不,后厨里忙活的。你也知道,我手快,干这个轻松又漂亮。这是我主业。”
“副业呢?”
“嘿嘿,什么零活儿都干,说不定我还在你手底下搬过砖呢。偶尔也操个旧业什么的。”
“这么辛苦啊。”
“我那师傅,老光棍一个,这次出来都60多了。我得给他养老。”
我想起第一次看魔术,是小学时候班里的老大——哈哥儿在午休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的。
我看着他的手在红布下面翻来倒去,就像看着数学课上几乎停摆的钟表指针般缓慢。然而身边人都惊呼不已。包括我偷偷暗恋的小妍,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胖子,捂着因为惊讶而微张的嘴,笑靥如花。我突然感觉一阵躁动,于是我挤上前去,揭穿了他的魔术。
哈哥儿的脸色微变,紧接着他又掏出纸牌,想要挽回失望的观众。但是又被我毫不客气地一一揭穿。
那天放学,我被哈哥儿堵在了厕所。他高出我一头,胳膊几乎有我小腿粗,我只能用手护住脸,蹲了下去,以减少挨打的部位。他愤愤地对我拳打脚踢了足足十分钟,骂声甚至盖过了我小声的抽噎。
从此我再也没有看过魔术,也不再毫无顾虑地捅破任何蒙住我双眼的纸。
“你怎么不学魔术?凭你这双手,不比什么刘谦差吧?”
“怎么没想过。你知道这行有多难入吗?那些魔术道具,贵得你不敢想。而且我学会了也没地儿给我演去,要是进什么团啊社啊,进门就问在哪儿学的,一听是自学,看都不看,管你是不是巧手如花呢。人家要的是个响当当的名字。上街头卖艺?还不如我打工呢,至少工资按月结。”
我一时无言以对。
分开的时候他要了我的电话,说是如果有什么临时的活儿可以联系他。我点点头,上了不同的公交车。
入秋的时候,工地的施工也逐渐进入尾声。我的工作量却逐渐加重,每天要上下几十层巡视最后的几道工序,施工监察的报表也是每天要撰写存档。连徐小峰几次约我出来吃饭我都没空推后了。
快到国庆节的时候,我终于先拨通了徐小峰的电话,打了两次却只是无人接听,只得作罢。
小时候我问奶奶,为什么奶奶脸上有这么多皱纹。她爱怜地抱着我说:“老了就这样。”
“人都会老吗?”
“人都会老的。”
那时候我觉得很惊恐,我觉得当我满脸皱纹的时候一定很丑,于是我每天都凑在镜子前许久,观察我什么时候会窜出一条皱纹。
等到我20岁时,第一次照镜子发现刘海下沟壑清晰的抬头纹时,我怔了一会儿。
那时我有个女朋友,我盯着她光滑的脸颊看,直到她不自在地用手在我眼前摇晃问我看什么。
我告诉她,我要把她的脸留在我的眼中,慢慢地看,这样,她就很久很久以后才会老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扭过头去继续玩手机。
当我知道小峰跳楼后的那天晚上,我一直在做梦,我梦见他从我们新建好的大楼上跳下来。我抬头正好看见他下坠的脸,离我只有十厘米。我放慢了他下落的速度,他就从我面前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下落。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看着我,直到我们的眼睑贴在一起。
然后我就醒了。
因为国庆期间车票难买,他的父母从千里之外赶过来的时候尸体已经发臭。他的葬礼极其简单,或者说没有。只有他满头白发的父母和几个大学同学,他没什么朋友,公司的同事甚至没有派个代表来。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她噙着泪和我们一起看着小峰被推进焚化炉中。而他那因为一瓶Dior香水问题而分手的前女友则是自始至终不见踪影。
小沫说:“他能听见那么多那么细,一定活得很累,下辈子希望他是个聋子。听不到那些非议和嘲讽,听不清那些是非,或许能够活得开心点。”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小峰的死一直让我感到很愧疚,我静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如果之前他找我,我能够多陪陪他,了解他在新公司里的事情,帮他疏导一些,他是不是就不会绝望地轻生?
这种想法让我陷入崩溃,我想起半年多来我们相处的时光,想起他文质彬彬的西装、眼镜、腼腆的笑容还有他酒醉之后歇斯底里的咒骂。
他说这不公的人生,现实的女友,钩心斗角的职场,冗杂腐朽的制度,又聋又瞎的社会,我知道他瘦弱的身躯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可我们谁又不是在苟延残喘?
心绪不宁让我最终犯下大错,我在报表中多写了一个0,隔天公司就损失了300万。老板很宽厚地扶起跪倒在地的我,说念在老员工为公司做了不少贡献又是初犯,只让我赔偿十分之一的损失。
其他的话我一句都没听见,我看着他厚厚的嘴唇不断嚅动,脸上的肥肉因为笑容而堆在一起,像一条肥大的蛆虫,要钻进我腐烂的身体里大快朵颐。
我只记得“赔偿十分之一”。
我如同行尸走肉般地靠着习惯走回家中,从床下拿出了我的鞋盒子。
晚上我点了一遍又一遍那些参差不齐的钞票,直到痛哭流涕。
36270元,我的全部积蓄。
国庆节的那天,举国欢庆,我在阳台上对着远处灯火辉煌的闹市区喝了一杯又一杯的酒。
那天我也是和小沫一起喝的。
“30万,我上哪儿找那么多钱。我来这里八九年了,就攒下3万多。我父母还没享到我一天清福,难道要我这个时候还要剥他们的皮抽他们的筋让他们帮我还这个债吗?”泪水和鼻涕已经糊住了我的口鼻,我的嗓子沙哑到失声。
他只是揽着我的肩,安慰我说他有办法。
我知道他说的办法是什么,但是我没有阻止他。
如果还不上这笔钱我会坐牢。
党小沫接了道上中介的活儿,去偷一件古董。结果被人发现,主人是本市有名的黑老大,于是党小沫的右手被齐根砍下,作为“学费”。
我没有去医院看他,我不敢见他。
身边的酒还剩最后一瓶,我没有开,用它压住了一张薄薄的纸。
从阳台上跃下的时候,灯红酒绿刺痛了我的双眼,我闭上了眼睛。
我想在这里生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如果活不下去,至少我还想死在这里。
我叫陈大力,1988年10月2日生。